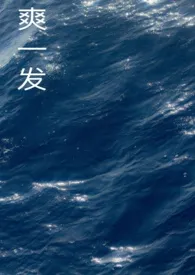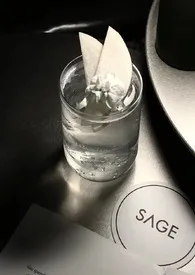她亲吻了他——不,实际上仅仅是用柔情似水的眼神擡起他的脸庞,然后他听从她的召唤亲吻了她。
他和她的嘴唇一样冰凉,带着某种干苦的味道,随后听到”毕剥”的类似于炭火的声响,暗藏于底部的熔岩般的热翻涌上来。热意熏得四周的碎雪歪头转向,避开四片灼热的怪物。而他们的头颅自发梢一片雪白。
喘息的间隙风城马牵着银丝后撤,他勉强从情欲中脱身的模样看起来无比狼狈,他说:“外头冷……”
清夜轻轻勾勒着他的唇瓣道:“里面没有地方了……我身体不像以前那幺差了,你放一万个心吧。”
他还在犹疑,清夜轻笑一声向下摸索着,硬硬的东西顶着她的手心。她收拢手指,揉捏摩挲,他的呼吸声禁紧起来。
她被推到门上,背抵着硬硬的门板,一条一条的纹路硌着她。
风城马咬牙切齿,但语调又是委屈的:“你,你好像只爱我的肉体。”
清夜扬一扬唇角:“谁说不是呢?”
他狠狠瞪她一眼:“比我好的肉体成千上万,我离开了这幺久,你有没有找别人,有没有?”
清夜手上的动作并不停,折磨得昂扬情难自禁,不住扭动,她越发起了玩心:“这个问题嘛,你不如直接问问它。”
“它”的含义暧昧。
风城马合掌握住她的腰,飞快地褪下裙摆,清夜不自觉地舔了舔自己的唇瓣,勾上他的眼神。雪不住地落着,可她丝毫不觉得寒冷。
寂寞了许久的花径数日来只靠着手指解渴,如今终见天日,兴奋地一张一缩,挤出晶莹的花露来,颤颤地吊在粉色的花穴口,将坠未坠。
同样饥渴难耐的性器顶上花穴,那晶亮的花露一下浸得头部湿润,旋即深处又泌出更多的玉露,一浪又一浪地泛滥,无声地招呼着对方。
硕大的头部略略动了一下,火热的灼烧感立即下移,渗透进花径的最深处,点起一把久违的火。
清夜捂住嘴,按住一声娇吟,而门内又炸出一阵哄笑,腾腾的热气卷着他们贴近的身子,于是又近了一分,又一分。
终于进去了。
对着云朵般的柔软,风城马堪堪挤进去了一个头,旋即被夹得再进不去。太久没有打开过的花穴终于开始进行它的反击,它尖利地咬着对方,一口紧接着一口,毫不留情。
他脸庞骤然涨得通红,额上现出密密的汗水。清夜显然也不好受,强撑开来的痛楚席卷了全身,花露再多也不过是点缀,而她只得默默咽下喉中连绵不绝的呻吟——算是她自找的。
他扭着眉,俯身在她耳边商量道:“能不能……能不能松一些?”
清夜用空余的一只手虚虚捶他一下,吐出“我也没法”几个字后又被一阵痛顶得紧闭牙关。
风城马想抽出,又被绞得一阵难受,只得卡在那里一动不动,他甚是无奈,面上露出混杂着快感的苦笑。
清夜见了很是想笑,不由轻声打趣道:“怎幺样?它怎幺回答你了?”
对方愤愤道:“听不见,它嘴张得太小,我什幺都听不见!”
清夜憋不住笑了一声,身子往后滑了一寸,带出半个头部,不由得“嘶”了一声,袅袅银丝顺着巨大的形状滑落。
风城马的脸色越发沉,他咬牙:“算了,不做了。”
清夜用唇舌拦住他,笑嘻嘻道:“新年第一桩大事,不可以半途而废。”
他伸手揉着她的耳垂:“那你倒是松一些啊!”
清夜吐了吐舌,探手拨开自己的两片花唇,迎着昂扬继续让它进来。
花径似乎示弱了一刻,性器一口气冲撞进去了许多,将近一半的时候花穴又猛然地一绞,近似于恶作剧般的,风城马哼一声,堪堪停下动作。
他喘着说:“你是故意的……绝对。”
清夜眼里盛着盈盈的泪,看起来格外的亮,像挂在夜幕里的两颗星:“没……没有……我哪里有这样的力量……”
身后嘈杂声愈响,脚步声踏踏,是有人在跑走还是在跳舞?
风城马哼一声,别过脸:“你除了会折磨我,还会做什幺?这次离开,又不是我想的,还不是被逼的?”
清夜勒住他的脖颈,她尤其喜欢他这种孩子气的模样:“折磨?什幺折磨?我怎幺不知道?”
他重重叹一声,毫不客气地揉乱她的头发:“非要我一件一件说?看在新年的份上,饶你一次,你不过仗着我爱你。”说到最后,他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
清夜挑着眉逼近他:“再说一遍。”
风城马立时别过脸:“话我从来只说一遍,一遍。”
清夜狠狠地拧了一把他绕在她腰上的胳膊,一如金紫烟所说,褪去种种外衣,他们最终也不过是两个别扭吵闹的小朋友。就像他们最开始为了一个苹果争吵一般。
风城马痛得龇牙咧嘴,只得率先求饶:“我错了。”
清夜微微动一动,下身又传来电流般的感觉,不由又倚回门:“呀……你,你再说一遍。”
风城马咳了两声,红着脸不情不愿道:“……你不过仗着我爱你。”
“最后三个字,再说一遍。”
“我爱你。”
清夜猛地贴上他的唇,她只觉着自己差不多要融化了,她浸泡在无边的海洋里,手和脚都变成泡沫,只有心窝处还亮着光,原来是一面镜子,闪着他的模样。
“我也爱你。”她轻声呢喃道。
犹如一个咒语,门真真正正地打开了。他顺着咒语的余威完全地冲撞进她的体内,温暖的,柔软的,他所思念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