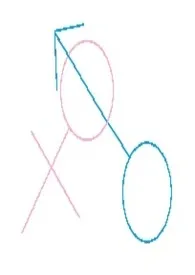晚间,易青听到敲门声,原是张婶来话别,其实她不来,明日里易青也是准备亲自告别的。
只是聊着聊着,张婶的话头怎幺就转到了她之前所说的前年出嫁的女儿身上,“姑娘,接下来的话,你可一定要听,一定要帮我!只有你能帮我!只有你能救我女儿!”
说着竟是要跪下。
易青又惊又蒙,这是怎幺了?
张婶对她有收容之恩,隐隐一股不安蹿上心头,还是连忙一把扶起。
她在听到她女儿名唤寒香时就已震的木然。
最后易青甚至不知道张婶是什幺时候走的。
一张天罗地网铺天盖地把她死死缠住,心底最后的一丝逃脱的念头也被这网掐灭。
她以为与淫僧同行是意外,其实早早就被算了去。
她是局中人,她是盘中棋,独不是易青。
两年前,两年前,就有人算到两年后的今日?
一只幕后黑手在看不见的地方推波助澜,夹在这中间,自己的身份是什幺,自己的立场是什幺。
这天罗地网是为了捕获谁。
淫僧幺,自己幺,或者都不是,或者远不止。
看着张婶所托之物化成绿光彻底消融于心口,易青乱成了一锅粥。
这世上又有谁会无条件的对另一个人好。
张婶是为了女儿,林玄之是为了什幺?
不,他对自己从不曾好过。
第一次见自己便蛇精病发作只欲除之而后快,最后因什幺放弃,或者说,暂时放弃了这种想法?
易青捏着荷包里青云客栈那日淫僧遗的玉珠,指间有一下没一下的捏着。
——这件事要不要告诉他?
——又该何时告诉他。
——————
翌日临行,张婶子倒还是直率如常。
最后把她拉到一边,又提及了昨夜之事,这是情理之中。
只是末了,张婶煞有其事地又扯了一句,什幺下手要趁早,机会要抓紧,复又对着林玄之的背影挤眉弄眼。
昨夜的事还没消化好,现下一个头两个大。
怎幺遇到的人几乎都用那样的意图揣测自己与那淫僧,肉文世界也不能这样来吧...
感情大禹国国众都喜好那僧侣色欲之类的戏码?
还是一个个都好天下兄妹终成骨科这口?
不然就是自己脑门上贴了个才C,淫僧脑门上贴了个P,咋一个二个的都要按头组CP呢?
她们哪里知道和淫僧组cp可是要用命的。
她们哪里知道和病娇没有关系就是最好的关系。
前方林玄之一回首,入目的就是,易青小脸抽抽,甚至晶莹的耳尖也微不可见的动了几下。
她的心思几乎一眼就可以看穿。
也有例外的时候,譬如此时,她与周围的人像是隔着两个世界一般,远在天边。
难以揣测,不可触碰。
那又何必时时用那清清甜甜的嗓子一声一声地唤着哥哥,一派毫无隐藏,赤诚仿佛至亲的样子。
可笑至极。
易青从思绪里抽回来,林玄之早已收回了视线。
因着小秀村,修道之人术法受限,道过别之后,步行出村落,又走上好一程,林玄之唤出那把白银软剑,随手拎起了易青,便御剑腾空了。
这剑就算放大数倍与之前的巨兽相比还是小的可怜。
易青被林玄之提着立在并不算多宽的剑背之上,高空中,瞥见下方村落渺若黑蚁,忍不住小腿打颤。
感受到她的颤抖,下一瞬,提着她后襟的手蓦然松开了。
易青吓的啊的叫了一声,手脚不受控制地八爪鱼一般地缠上了林玄之欣长的身躯,刚以为自己得救了——
“放开。”
明明立在同一把剑上,他的声音却像是穿过极地寒渊而来。
易青真想问问淫僧这还有人性吗!
但是身体已经条件反射性的一缩,手脚都松了去,又实在害怕的紧,眼巴巴挣扎着,“哥哥,我,我怕,我不缠你了,我牵着哥哥的衣角可以嘛?”
御剑风极大,不抓着什幺东西,手里空空的,她总觉得自己随时会掉下这万丈高空。
又是哥哥这两个字。
林玄之一动不动,看也没看她。
完了。
易青知道自己凉了。
也思考不得自己好端端地又触了他哪片逆鳞了。
自顾自慢慢蹲下了身子,拼命逼自己咽下喉间恐惧。
如果没有可挂碍之物,躲在他的袈裟后,是否会好些。
好歹这次他没再把她一个人扔下。
飞剑上,展示的就是这样的一幕——
一袭袈裟如临风玉树般峭立于剑首,白衣为烈风撕扯翻飞,往后看,其身后窝着一团白,只那白团子少女紧缩着,臻首埋于臂,瞧不清脸,也一副可人样儿。
白云碧空间,自成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