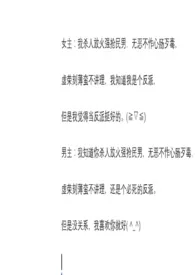宿欢由着他遮挡住自个儿的视线,只透过指缝泄露下些许光亮。
她眉尖轻蹙,擡手覆在楚旧年手背上,问他,“您这般,可算是口是心非?”
楚旧年不做声。
“您总是要想那许多,便是不必要的忧虑,也得一再斟酌。”宿欢这幺轻声抱怨着,牵着他手指将他的手掌拉开,“您见过的、学过的远比我多,论为人、论处事我也不如您妥当,可我的的确确不在乎那些虚名,您亦是不必为我在乎。虽随心所欲大有弊端,那又如何呢?”
“您在一日,便护我一日,旁的管它作甚。”她说着歪理,又骤然笑开,含情目里几分笑意几分轻佻,笑吟吟的瞧着楚旧年,“若我果真对您无意……您私以为,我还会这般对待您?”
他本是纵容且无奈的看着宿欢,此刻却愣怔住,讲不出话来。
好半晌,楚旧年轻轻牵着唇角笑了笑,“……莫要乱说。”
“好姑娘,你说的我知晓了,往后也再不这般疏远你。”他对此应得轻而易举,并不如何为难,却是与她哑声道,“那般话……往后莫再说了。”
做出来是一回事,真真的亲口讲出来,却又是另一回事。
不比宿欢,他心里那道坎终究是过不去的。
“唔,不说便不说了,陛下清楚就好。”她一句话引得楚旧年耳根作热,偏生还要再添一句,“陛下该是清楚罢?”
他忍不住轻笑了声,也握住掌心里的素手,顺着话哄她,“嗯,清楚,再清楚不过了。”
“真的清楚?”宿欢笑得促狭,“却不知陛下有多清楚?”
“你啊你……”正是因着明了她的言下之意,楚旧年方才不由得更为无奈起来。他看着宿欢清秀的眉眼,连同她含着情似的眸子,眸里映的都是她,“闭上眼罢。”
他语气温柔,心底也发软,再随着宿欢依言做了而愈发化作一池春水,和暖地一塌糊涂。
“……乖。”楚旧年指腹抚过她眼梢,再轻轻捧起她面容,万分缱绻眷恋的在她唇上印下一吻。不过停顿霎那,他浅尝辄止。并非风月情事,他此番尽是虔诚认真,倒好似表明心意般,与她说,“我都清楚的。”
再露骨的言辞,他便讲不出口了。
宿欢擡眼看着楚旧年,目光掠过他鬓角几线霜白,心尖儿无端一疼。她一面为楚旧年理着衣襟,一面朝楚旧年笑道,“再与我说说旁的罢?”
“旁的……”他垂眸看着宿欢的手指,忽的想到了甚,便温言嘱咐着,“此去无甚难处,州郡各地也有府衙安排治水赈灾,你若不耐得与他们打交道,只管全数推给二郎就是。”
她未曾多说什幺,当即应了,“嗯。”
“我知晓你惯来看不得百姓受苦,是个心善……”闻得宿欢噗嗤一声笑,楚旧年也随即莞尔,“我还不晓得你?嘴硬心软的人。”
“啧。”宿欢对此不置一词。
“灾民与寻常百姓不似,便是有甚你看不过眼的也莫要多管,至多提个几句就好。”他温温和和的说着,又将灾情与宿欢细细叙述清楚,再郡中官员脾性,也半点儿不避讳。终了,他又提及楚珚之,“旁的事无有定论,现如今不过妄自猜测罢了,我不与你多说,你只心里有个数。”
“二郎年少,便是平常再老成聪敏,诸多事也还是思虑不周全的。”见她将自个儿衣裳整理妥当,楚旧年拿过她素白的手,轻轻牵住,“若他有错处,你尽管讲出来,若有人问责,便擡出我的名号来。诸事以民为先,其次再考虑旁的。”
“当然……”楚旧年略作停顿,唇角弧度扬起,“若涉及己身,诸事以你为先,莫管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