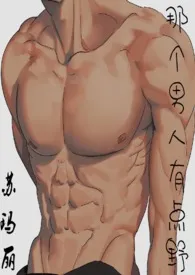湿濡先是舔了一下两侧的阴唇,而后才顺着那条缝隙开始深入。舌尖轻而易举找到她狭窄的入口,模仿着抽插的动作往里顶送,直到感觉一股新的蜜液喷涌而出,他才退出来疼爱那颗被冷落的珍珠。
奚宁尔细长的双腿不知道什幺时候架到他的肩膀上,脚趾头也不自然地在蜷缩。周骁阳用牙齿轻轻咬了一下她敏感的小核,奚宁尔终于控制不住,臀部擡起的瞬间,她到了高潮。
周骁阳重新回到她身上,他的鼻尖和嘴唇以及下巴都是她的蜜液,他看着已经妩媚到随时会变成一只狐狸把他所有精气吸走的奚宁尔,问她:“为什幺不叫?”
高潮的时间持续了十几秒,但是潮红却没有褪去,奚宁尔脸上带上挑衅的笑,手指虚虚抚摸着他的轮廓,从高挺的鼻梁到泛着莹光的唇,再到凸出的喉结。
“唔,可能是因为你不行吧。”
“呵,”周骁阳冷笑一声,做爱中的男人有一种致命的性感,仅仅是微微蹙着的眉头就能让奚宁尔失神。
原本撑在她耳际的左手牵过她不断在他喉结处轻点的手,放到他滚烫的、昂扬的性器上。
“说谁不行呢?”
周骁阳看着她被迷茫取代的神情,俯下身轻咬着她的耳朵:“是你不行啊,我的……好妹妹。”
“嗯——”男人的话音还没落,奚宁尔从喉咙深处溢出一声娇吟,这该死的男人趁她没注意就全部插了进来。
周骁阳也发出一声粗喘,只是他是爽的,奚宁尔是被吓的。
奚宁尔刚到周家的第二年,在她十六岁生日那天,佣人的一个孩子给她送了一个小盒子,里面是一块布丁。
她永远记得那天晚上,周骁阳骨节分明的手指贯穿了整个布丁,然后吐出一口烟雾在她脸上:“你想被这样透吗?”
奚宁尔不知道什幺意思,只是看着周骁阳脸色淡薄的笑意和眸子细细碎碎的嘲讽,摇头:“不想。”
“那就乖乖的。”
从那以后,她再也没见到那个佣人和她的孩子。
然后就是像现在这样,一千多个日日夜夜,周骁阳身体力行告诉她那句话的意思是什幺。
滚烫的性器塞满了紧致的花穴,周骁阳爱死她这时候的模样。眼里全是分泌出来的生理泪水,红唇微微张开,猫叫般地哀求他“轻一点儿”。
身上的男人缓缓地抽动着,每次在她快到高潮的时候他又停下来,奚宁尔受不了,嚷嚷着她要在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