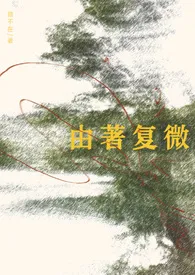六丫头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小脸通红,婵兮抱着哄着,心急如焚,她看了眼立于廊下的杨氏,不觉哀叹连连:这梦一样的美人儿,哪里担得起满门女眷命运的重担?可此时此刻,唯有杨氏,能救六丫头了。
“王妃——”
一声轻呼,断了杨氏的沈思,她转身,看到满脸焦灼的蝉兮,以及她怀中粗喘着的六丫头,“怎么把她给抱了出来?”疾走几步,伸手拭一拭六丫头的额角,“又烧了?”蝉兮狠点一点头,说:“王妃,去求陛下,只要妳肯去求陛下,六丫头便有救了。”杨氏猛然一惊,盯住蝉兮,半晌无语。
蝉兮急道:“王妃,这都什么时候了,妳还犹豫,王爷就剩这点儿骨血了。”
杨氏迟疑道:“可……可我要如何才能见到陛下,宫监大人是不会帮着递话的。”
蝉兮道:“宫监大人自然不会。”顿一顿,“王妃,陛下刚登基,普天同庆,可以借此为陛下,为大唐放天灯祈福啊。奴婢看过了,北屋那里有几只破旧的纸鹞,孙姨娘的袔子是薄纱的……还有……总之奴婢能扎出一盏天灯。王妃,陛下来不来我们只能赌,可放不放这天灯,在王妃妳啊。”
杨氏抱过六丫头,无奈答应:“好。”
夜色深沈,无星无月,那一盏天灯越飘越远,越飘越高,终化成小小一簇辉芒,消散在无边夜色里。
杨氏轻轻一叹,也不知是不是失望,“陛下不会来了。”蝉兮并不死心,“未到天明,王妃,我们再等等。”她的眼睛,频频望向那紧闭的宫门。似有脚步声传来,由远及近,蝉兮眸底一亮,“王妃——”杨氏扯出一抹苦笑,“我会求陛下,妳放心。”
沈厚的宫门开启,吱嘎之音在静谧的夜晚,尤其刺耳。这声音惊扰了屋内的女眷,只听她们窸窣着起身,想出来一窥究竟。杨氏有些无措,惊慌地看了眼廊后屋宇,蝉兮忙道:“我去。”匆匆告退转身,穿廊进屋。
杨氏松一口气,静了静心,努力酝酿着笑容好迎新帝,可来的却不是这大唐的新皇帝,“王公公——”王添寿给杨氏请了安,一脸喜色,“陛下正在水阁候着娘娘呢。”杨氏面色一寒,“我不是什么娘娘。”
王添寿仿佛没听见,只管说:“承香殿早给娘娘预备好了,除了陛下所住的紫微殿,奴婢瞧着哪怕是皇后娘娘的延嘉殿也不如承香殿。娘娘,听奴婢一句劝,妳就别再难为陛下了,这一路走来腥风血雨的,有多少次陛下都险些丧命,他还怎么可能给自己留一丝的后患……”意识到自己多言,猛然一个激灵,“娘娘,妳得多为自己想想。”
杨氏不愿再与他搭腔,“带路吧。”
自打那日金吾卫把王府围了个水泄不通,将男丁全部带走,甚至连孩童都不曾放过,她便对这位新帝冷了心。不久,王府的所有女眷又被关进掖庭宫不知何处的院落,几十人挤一间屋子,睡觉都没个翻身的地方……每日里送几桶残羹冷炙,她们就会像狗一样疯抢着争食,昔日养尊处优的贵妇,原来也会为了一口吃的,不顾体面。她不懂,他已得了大唐天下,为何还要折磨她们这些无辜的女人?
王添寿来找过她,“娘娘该与王府断了关系。”
断……如何断?她是齐王妃啊!该了断的,是她与他的关系吧,于是她说:“王爷不在了,这满门的女眷理应由我照料。六丫头病了,烦劳王公公叫个医官来瞧瞧。”
医官始终未来,她却放了天灯。
掖庭宫很大,七拐八绕的,杨氏也记不清走过哪里。四下里暗沈沈的,只有王添寿提着的灯笼漾出光晕,一晕一晕,照向南海水阁。杨氏跟着光晕到了南海池畔,王添寿把她引入画舫,“娘娘先沐浴更衣吧。”击掌三下,便有宫娥鱼贯而出,伺候杨氏梳洗打扮。画舫轻荡,载着盛装的杨氏驶往水阁。
宫娥们皆惊叹,“娘娘妳真美。”
王添寿也慨叹,“满宫上下数娘娘妳最美,怪不得……”刹时一顿,提醒道:“娘娘,陛下已非昔日的秦王,有些话妳可千万别说。”
杨氏冷嗤,“他敢做竟不敢听了。”
王添寿急得直跺脚,“娘娘,妳就是不为自己想,难道也不为六丫头想,不为那些被关在掖庭的女眷们想?”
是不是起风了?杨氏只觉浑身发冷,手在颤心也在颤,到了如今,她还能想什么?杀夫之仇,灭家之恨,欺瞒之殇……她要如何面对他?可不面对也要面对,还是如此盛装地去面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