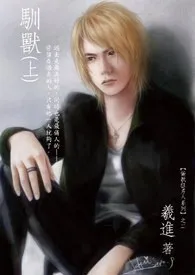冯栀那晚被常二爷扯裂衣裳,翌日早命人送来十数件,皆是锦缎绉绸面料的高级货,好容易挑出件豆绿色布旗袍,衣襟花纽却换成珍珠扣子,精致好看极了。
她愁恼的很,常二爷却很喜欢,顺她袍摆衩处往上捋至腰间,跪趴着再要了一回,他道:“怕甚么,谁问起你就说是我送的。”
她可没那胆子。
秦婉问可是姆妈给做的,又摇头笑道:“定不是的,市面上这样棉布料皆是蓝调,能染成豆绿色不易,那珍珠扣子白圆玲珑,也不是寻常珠子,这件旗袍怎地也值七八百大钱,你姆妈哪里舍得买。”
诸如秦婉这样的富贵太太,平日里常和门第相仿的那些小姊妹,凑在一起不是打麻将,就是逛珠宝时装店,早练就一双火眼金睛,她估摸的总八九不离十。
冯栀颊腮透出两抹红晕,咬着唇不响,秦婉倒自吃吃笑起来:“你不说我也知晓谁送的!”
冯栀心倏得提到嗓子眼,悄把打颤的手背到身后,听她接着说:“怕甚么羞,是阿涞送的罢,我早晓得了。”
“阿涞?!”这从何说起。
秦婉“嗯”了声儿:“阿涞如今做掮客,倒是顺风顺水的发财,没想到伊倒蛮茄(能耐)的,讲起股票经来头头是道。我上趟子想把彩娥介绍把伊,伊讲只吃煞侬一介头(只喜欢你一个)。”彩娥在旁盛粥,不慎洒了点出来,忙用帕子悄悄擦了。
冯栀张张嘴又把话吞咽回去,怎么说呢,这倒是个好借口。
毓贞把碗儿一推,端起香茶漱嘴,说了句谢大嫂招待,推她往外走:“上学堂要晚哩。”
就听得秦婉嗓音尖细:“阿栀都没说话,你臊甚么,大姑娘心思十八弯、活络的很。”也听不明说的是谁。
毓贞拉着冯栀一股劲儿走出院子,方停下来喘气,一面道:“我这个大嫂从头发丝里都透出精明来,你再不跑,就要露馅了。”
冯栀笑了笑:“露甚么馅,我又不是芝麻汤团。”
毓贞擡头看她,慢慢撇起嘴角,语气带着丝缕得意:“你和二哥的事瞒不过我。”
冯栀脸上的红晕褪去,默然听她继续说:“那晚我见你上了二哥的车,可是一夜未回,上学堂时,我特意绕到南京路的公馆,看见二哥送你出来,他还亲了你......”
冯栀打断她的话:“你想怎样呢?”
毓贞微怔,耸耸肩膀:“不想怎样,我不管你们的事,也懒得说给谁听。但我的事你也别管,也不许说给谁听。”
知道是指合家宴找猫时、在对面洋房撞见她的事儿。冯栀松落口气,点点头应承下来。
两人快至外门时,毓贞邀她一道坐车,她笑道:“布包还没拿呢,现天色还早,乘电车去学堂也不晚。”
说着就告别要走,毓贞忽然拽住她的胳臂,凑近耳边嘀咕:“我请你帮我办桩事儿。”从袖里掏出一张电影票:“你帮我送去那楼里304房,他你也认得,周希圣。”
“是他!”冯栀吃了一惊,她们这些女学生聚在一起,说来绕去都离不开男高那二三风云人物,周希圣便是其一,她远远瞥过,面容清隽、瘦高个儿,不大理人的样子。
却原来也是贫苦之子。
冯栀不想趟这浑水,毕竟毓贞早已订了亲,她摆手拒绝:“才说好互相不管的。”
“你帮我跑一次。”毓贞沮丧起脸儿:“你不晓这一府的探子,就等着揪我辫子呢。”
冯栀看她着实可怜,噗嗤笑了,接过电影票:“就这一次,下不为例。”
回房里取了布包,她便过街往对面走,拱门前老虎灶已经大开,望进去里面黑森森的,只有土灶膛里燃着红光,灶面摆着数个大铜壶,壶嘴嗞嗞地响,四处白烟氤氲,门前排着七八个楼里住户过来泡热水。
一旁摆着半新不旧的四方矮桌和几把旧藤椅子,几个上年纪的围坐,吃着粗茶在闲聊。前时见的剃头匠也在,正给顾客刮胡子,那人仰面躺着,嘴周围糊了一圈乳白色的刨花水,一动不动,好像睡着了。
冯栀再走近些,便看见周希圣正排着队,一手抱紧水瓶,一手拿着份石墨铅印的报纸在看,他穿一件蓝布长衫,已洗得发白,几处打着补丁,不细瞧倒也瞧不出甚么,他头发很黑,皮肤是白的,整个人洇在水汽里,倒有些古旧蓝皮线装书的韵味。
作者的话:昨天有读者质疑民国是否会叫爸爸。我再解释一下,当时写的时候也怕不遵事实,特意查了资料,爸爸这个词,在民国苏锡常等地,是叫爸爸的,陈宝国演的老酒馆里(民国剧),他也是叫爸爸的,所以才会这幺写。
阿栀因为没有爸爸,二爷又比她大,所以就叫了出来,我觉得也是合情理的。
所以这里解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