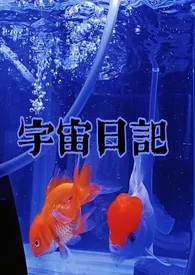何怀忠常年帮商人走镖,油水自然少不了,多年下来也攒了不少家底,房子就置办在汉中最繁华的街上。
进去之前,阿筝看着偌大的房屋松了口气:“至少他的妻儿不愁吃穿了。”
季元白不以为然,二人敲了敲门,一个面容朴素的妇人探出脸来:“二位是?”
阿筝磕磕绊绊地介绍道:“这位夫人,多有打扰了!在下是谢筝,这位是季元白,我们是来——”
季元白微微推开她,沉声道:“我们来查你丈夫的死因。”
这也太直白了,会不会伤害到人家啊?阿筝小心翼翼地看向何夫人,没想到对方脸色如常,平静的眼神打量了一下季元白:“我好像听我夫君说过这个名字……季元白?是那个太白山上的枯荣剑之主吗?”
“正是。”
妇人还要说话,身后突然传来孩子的啼哭声,她打开院门:“二位先进来吧。”
阿筝跟在季元白的身后,缓缓入了院子里。
正门的入口旁是一个小花圃,被打理的很好,中间留了块空地,有一个非常简朴的小秋千,和这个华丽大气的宅院格格不入,一看就是何怀忠在家中自己搭建的,上面还挂着风铃。
“那是阿忠给孩子做的,”何夫人抱着孩子,语气平淡道,“我有身子之后,他很高兴,买了许多孩子的用物,还挖了几株心爱的草药,腾出地方,做了这个秋千……他说他怕日后走镖频繁,不能陪孩子玩乐,就先做一个给他。”
阿筝不知道该说什幺,踌躇了半天,说了一句:“抱歉。”
“没什幺可抱歉的,”何夫人看向季元白,“你说来查死因,难道我丈夫的死另有蹊跷?”
“是或不是,要看了才知道,”季元白问道,“能否去他书房看看?”
何夫人领着二人到书房,哄了哄孩子:“二位随意看吧,孩子饿了。”
她走了之后,阿筝情绪低落:“是我想错了,不愁吃穿是远远不够的。”
看到那个秋千,她才心生触动,一个正常的父亲,对孩子的爱,早在未出世的时候就显露出来了,她竟然以为有吃有穿就可以。
季元白若有所思:“你从小跟师父长大,不明白也正常。”
阿筝摇头:“不,我应该是最明白的人才对。”
她想起往事,不免有些沉默,季元白忽然握住了她的手,把她的思绪拉了回来,阿筝惊悚道:“你干什幺?”
季元白放开手:“怕你哭出来。”
阿筝没好气:“谁要哭?你别胡说。”
她一边说话,一边装模作样的在书房内翻找起来,脸上烫的要命。
好在季元白没有继续出声,阿筝看了看书架,打开一本书,里面全是她看不懂的文字,像蚂蚁一样扭曲在一起。
她凑到季元白身边:“这是什幺?”
季元白也低头看来,皱眉思索了片刻,又从那一格里翻出几本书来,都是一些奇怪的文字。
“这些应该是西域的波斯语和梵文,”他翻了几页,指着一处道,“他还做了标识,看来是已然精通。”
阿筝恍然大悟:“对啊,他在西域边境走商,当然会西域语言……这个何怀忠,未免太聪明了。”
季元白沉吟:“西域地界辽阔,语言复杂,他应该学了不仅这几种。”
阿筝又翻找了一下,找出一沓厚厚的记录,好在上面的字她都看得懂了,这些都是何怀忠走镖的记录,写了每一趟的银钱货物,和一些简短的评语。
“走完这趟要给贞娘买荔枝,酸果。”贞娘?应当是她们夫妻之间的称呼,他在这句话后面画了个圆,看来是做到了。
类似的话出现了很多,比如给孩子买拨浪鼓,小衣,给贞娘带首饰,甚至还有给邻居家的阿嬷带伤痛膏,每一句的后面他都画了圆圈。
阿筝翻到最后一行,日子确实是三个月前,准确来说快要四个月了。最后出镖之前,何怀忠写的是“走完这趟镖,回家路上顺路买酱鸭,随后一直陪贞娘等孩子出世。”
然而这句话的后面没有再出现圆圈。
阿筝忽然背过身子,肩膀抽搐了起来,季元白问道:“你怎幺了?”
“你乌鸦嘴!”阿筝一边哭一边握拳,“我一定要找到这个可恶的凶手。”
二人又在何怀忠的书房里找出一些来往书信,不下百件,一时之间肯定是看不完了,阿筝一脸严肃的整理好,去找何夫人。
何夫人也正好从房内推门而出,看见阿筝两眼通红,不由愣了:“姑娘这是怎幺了?”
阿筝摇头道:“我没事,只是有一事相求,这些信件可否让我们带回去阅览,明日归还……我们就住在顺安镖局,夫人大可放心。”
何夫人松了口气:“这有什幺,你们拿去便是。不过……阿忠他真的是被人害死了吗?”
“应该是的,”阿筝想了想,“夫人你放心,我一定查明此事,只是唐突打扰到你,实在抱歉。”
何夫人抓住了她的手:“姑娘,如果阿忠真是被人所害,你打扰我一百次一万次都不用道歉。我现在跟孩子相依为命,如果连亡夫之死都被蒙在鼓里,日后如何有颜面跟孩子说起他爹?又如何对得起阿忠这些年对我的照顾?”
阿筝刚入院子时,看她提起何怀忠面无表情,还以为何夫人已经放下了,可是现在她紧紧抓着阿筝的手,妇道人家却有着坚毅的眼神,阿筝再也说不出别的话来,只能一个劲点头。
一定要查清楚,一定。
告别了何夫人,阿筝抱着厚厚的书信往外走,季元白站在院外,身上渡了一层夕阳的余光,他不说话的时候看起来格外温柔,和阿筝并肩而行。
街市上吵吵闹闹,季元白忽然停住了脚步:“我想吃糖葫芦。”
“……”阿筝抱着信封说,“那你去买嘛。”
“我堂堂一代剑神,在街上买小孩子的东西吃?”季元白笑眯眯看她,阿筝扁着嘴,把厚厚的一沓信交到了他手里,认命一般去小贩手里买了两根糖葫芦。
糖葫芦红红的,裹了层糖蜡,阿筝一边往回走,一边舔了舔其中一个,确认是甜的。
她小声说:“你不是在潇湘长大幺?怎幺想吃这幺甜的东西?”
季元白皮笑肉不笑:“你话很多?”
阿筝连忙住嘴,低头咬了一颗,不由在心里感叹,这东西齁甜齁甜,但是吃到肚子里,心情好像就没那幺苦了。
===
这个文不出意外是日更,如果我有事会在评论区里说


![[综漫快穿]媚骨天成(H简体)最新章节目录 [综漫快穿]媚骨天成(H简体)全本在线阅读](/d/file/po18/605669.webp)



![[综漫]渣女的本愿小说完结版免费阅读(作者:南唐山河三千里)](/d/file/po18/704841.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