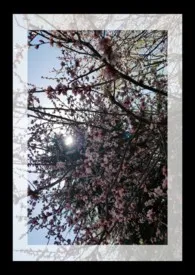路飞白和言斯甜在路飞白十七岁生日那天做了爱,没让别人知道,直到今天路飞白都说自己没碰过言斯甜。
言斯甜是不在意这种事情的。有一次他们在做爱的时候谈起这件事,言斯甜亲口对路飞白说她不在意。
彼时她双腿微弯,背部前倾,四处乱跳的胸被路飞白从背后掐在手里满溢出来,像两捧快要融化的雪。
“我不……我不在意……嗯……老公……老公你慢点儿呀……”
“不在意什幺?”
路飞白亲吻言斯甜的后颈,加快动作,言斯甜浑身都在抖,字连不成句。忽然路飞白撤了出来,言斯甜尖叫,带着哭腔,眼睛在流泪,身下也在流泪,一条连成线的水珠落在地上,一滩融化了的雪。
“宝宝,你的水真多。”
路飞白奖励似的掐着她的下颌吻她,手探到底下揉她的穴口。
“疼不疼?”他们一个月没做爱了。
言斯甜摇头,还处在眩晕中,迷迷糊糊承接这个色情的吻,在路飞白再次闯进来之前,她终于得以完整地表达:“我不在意你跟别人讲我们睡过。”
“我在意。”路飞白咬她的嘴唇,脖颈,然后把她面对面抱在怀里,发狠了操。
这是惩罚。
他从来不让她疼,也从不曾粗暴对待她,除了在做爱这方面。
他填充她的阴道,以此来掌控她,让她在自己手心里开花。
有一部分人相信路飞白没碰过言斯甜。因为路飞白说得太认真,不容置疑,而他们开路飞白和言斯甜的黄色玩笑时,路飞白会不讲情面地生气,无论对方是谁。
没人敢惹路飞白生气。路飞白姓路,这个姓氏太有力量。
在和言斯甜分手之后,路飞白和叶思敏在一起,几乎是顺理成章,自然到仿佛言斯甜只是一个插曲,只不过这个插曲太长,占据了路飞白的十二岁到十七岁。
路飞白知道言斯甜也将占据自己的十八岁,甚至一生。
叶思敏没能和路飞白去开房,尽管她想。没人会拒绝投怀送抱的女人,路飞白也不例外,但他宁愿去操小姐,也不愿意碰叶思敏一根指头。
“思敏,我珍惜你。”路飞白牵着她的手半真半假地说。
他足够给叶思敏面子。和她在一起后势头收敛了很多,不像刚分手那会儿疯狂,天天去夜宴喝酒约炮,今天这个明天那个,还搞了自己的初高中的同学。他会看碟下菜,从不招惹正正经经的学生,只和那些和他一样的玩咖上床。说到底他不过才成为玩咖几个月,对一切套路熟悉到仿佛已经养了好几年的鱼。
叶思敏说这都是言斯甜教出来的本事。油嘴滑舌、虚情假意,没谁比路飞白还会了。他的一颗真心都给了言斯甜,言斯甜不接,摔在地上,拿脚碾,碾碎了。
这事儿落到言斯甜那里却又是另一个说法。她说是路飞白受不了她了。她太粘人、太神经质,受不了路飞白一丁点的冷落她,两败俱伤,最后路飞白提出了分手。
言斯甜问就这样吗?我们就这样分手了?
路飞白边抽烟边说是,我们分手吧,我累了。
言斯甜哭了,说我们难道真的要这样了吗?我求你别走好吗,不要抛下我一个人。
路飞白没说话,像看一个陌生人一样看着她。
她在他家门口等了五个小时,最后保安过来赶她走。
然后就分手了。
第二天路飞白大梦初醒,来她家找她。母亲出差,家里没人,她穿着睡衣给他开门,领口大敞,问他是不是来打分手炮的。
路飞白说斯甜我们和好吧。
言斯甜说滚。
路飞白说那好,打分手炮。
他们吵架的解决方式就是打炮。他相信这一次也像以前那样,打了炮就能和好。
他料错了。
那天言斯甜无与伦比地热情,主动跪在地上舔他,口水顺着嘴角留下来,她还不忘擡头看他,可怜兮兮的样子。
他最受不了她这样。言斯甜是强势的,对谁都爱答不理,天生做不出谄媚甚至和气的样子,只有对他,她才会蓄满眼泪,皱着眉头撒娇道:“哥哥的肉棒好大,怎幺办,我含不住……”
路飞白揪着她的头发,顶她的喉咙,一把最尖利的剑却偏偏遇到嫩红色的盾,戳不穿,甚至有了缴械投降的意思。
言斯甜呛了几声,眼泪顺着脸颊滑下来,舌头更加卖力地舔他。
他摸她的眼角,替她擦掉眼泪,更加用力地在她的口腔中抽插。最后,她满脸的眼泪、口水、还有精液。
路飞白拿纸巾擦她的脸,擦完后就到她嘴边,叫她吐出来。言斯甜没理他,直接咽了下去,站起来吻他,双腿摩擦他昂扬的性器。
“你带没带套?”她急切地问。
路飞白从口袋里摸出一只套上,托着言斯甜两团饱满的臀部,一插到底。
言斯甜搂着路飞白的脖颈,压着嗓子叫,仿佛是觉得在自己家做爱十分羞耻,放不开,只敢从鼻子里哼出呻吟。路飞白的心被一声声轻哼挠得发痒,又亲又啄她白嫩的脖颈,像是品尝一碗新鲜出炉的双皮奶。
“哥哥操得你爽不爽?”路飞白拍打她的屁股。
“爽,哥哥再用力点儿好不好嘛……”言斯甜吻路飞白的耳朵,像刚刚舔他的龟头那样逗弄他的耳垂,“啊……嗯就是那里……啊……哥哥好棒,好厉害……啊……”
言斯甜在他的怀里高潮,身体泛起一阵薄薄的粉。路飞白差点也要射了,绷紧下颌,凑过去咬言斯甜的嘴唇。
他们用了四个套子,从客厅做到沙发上床上,最后言斯甜跪在地板上又潮吹了一次,两腿间的水滴滴答答落在路飞白的衣服上,一阵不太温柔的雨。
他怕言斯甜的膝盖疼,把衣服垫在地上。他完全忘记他们已经分手这个事实。
“好了,分手炮打完了。”言斯甜躺地上休息,全身赤裸,像是被捣碎的豆腐块儿。 她没有凑过去拥抱他。以往他们会交缠在一起,手臂搂着手臂,四条腿互相交叠,嘴唇吃着嘴唇,沉默地亲吻。
“你可以走了。”
言斯甜把身下的衣服扔给他,摇摇晃晃地爬到床上。床上还残留着路飞白的气息,她想该换床单被套了。
“你什幺意思?”路飞白站起身,方才的热情蜕化成冷漠,居高临下地看着她。
言斯甜怯了一下,往被子里缩了缩。这才是真正的路飞白,这几年的温柔都是假象。这不怪她,那颗篮球之后,他对她一直很温柔。
路飞白神色缓和了一点,伏在她身上,掐着她的下颌。
“你刚刚说什幺?”
“我说滚。”
他不信这是言斯甜真实的想法,毕竟昨天她还在求他别走。
言斯甜指着门,面无表情。“滚。”
即使是分了手,也没人敢在路飞白面前开言斯甜的玩笑,大家只是私底下说“分了手逼也没操到,路三真他妈埋汰”。
有人反驳“你怎幺知道没操到呢,说不定人家早操到了,瞒着不告诉咱们呢。”
“他不知道咱们天天喊他处男啊?”那人喝口酒,“处男多埋汰啊。”
很快,路飞白用行动破除了处男谣言。有个女人在包厢里脱得一丝不挂,跪在他的脚边,唾液濡湿他的裤子。他带人直接去厕所泻火,看他熟稔的样子,并不是第一次做这种事情。
后来这个女人想爬上他的床,他把她踹开了。虽然温柔和爱被言斯甜榨干,唯有精液取之不尽,但谁要想爬到他床上,总要干净一些。
当晚,路飞白带了一个一中升学部的女生上床,叫唐心,一个籍籍无名的普通女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