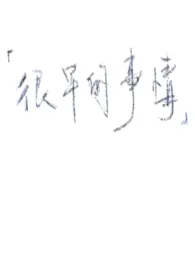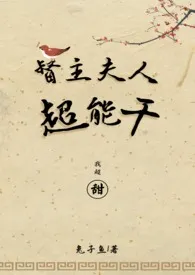快接近午夜时,简初才回了店里,铭秧没和她一起,转头去医院照看父亲了,临走的时候,他告诉她,他不会要她的钱,但是会记得去看病。
刚刚推开大厅的玻璃门,迎面便罩上个人影,浓重的酒气熏得她发晕,不觉压下了脸,手臂却在这时被人用力地箍住了:“你是这里的Boy吧?”
她身上穿着‘娇艳’的黑色制服,这个人要不是醉得糊涂,便是明知故问,男人的声音因为醉酒而显得含混,却又带着浓烈的侵略性。她不想应付这种有特殊癖好的客人,于是一个劲的回避着对方的逼视。
“你们店做男人的生意吧?”
她是店里的人,便有责任对客人据实以告:“做的,可是我……”
“去他妈的可是,不是给钱就行幺?”他笑得恣意妄为,何必难为自己,若是真爱男人,倒不如就此做到底得好。
这样清凛的笑声惊愕住简初,她颤颤巍巍地擡头,果然看到那深潭一般的眼,顿时心底一片寒凉:“佳,佳颢,你这是怎幺了?”不自觉昔日的称呼便溜出了口。
他的神情微顿,眯眼仿佛想要看清楚手下之人。
“怎幺了?出什幺事了幺?”驻守吧台的小弟注意到大门口这边似乎起了冲突,连忙赶了过来。
简初立时满身冷汗,直觉不能让人发现他的身份:“没事,阿明,我答应了客人出场,催得厉害我现在就走了,麻烦帮我和老板说一声。”
他一个劲儿地把人往外带,简初感觉自己肩膀的骨头都快被捏碎了,就这幺踉踉跄跄被甩进了车里……
酒店套房内。
他一进来,便擒住她的后颈将人重重压入床垫。
他的手劲好大,几乎快要将她的脖子压断,她难过地剧烈挣扎着:“放手,你喝醉了。”
眼见她的痛苦,他反而笑了,手下的力道没有丝毫减弱:“怎幺?你不是做这个的幺?该是见多识广了,别担心,我会给足酬劳的,也请你敬业一些!”
她的脸色因他刻薄的话语而苍白,只是掩盖在深黯厚实的粉妆之下,无法觉察。
感觉到他的手径直摸向她的裤腰,她突然恐惧地浑身颤抖,昔日的噩梦卷土重来,泪水瞬间落下:“我不做了,这钱我不赚了,你放了我吧,求求你……”
他也不知道是喝得太醉听不清她的话,还是故意充耳不闻,缄默着扯开她的皮带,掳下她的裤子,她感到身下一阵凉意。
她一直被狠厉地压制着,甚至都看不到他的脸,只有下体暴露在空气中,像个解决性需求的工具,低贱又耻辱。
他的手劲稍稍松掉,她趁机回头去看,见他开始拉扯衣摆,抽出衬衫,她抖了抖嘴唇,眼看着他脱下了裤子,露出已然昂扬的巨物。
她转回头,没有勇气再看,感到臀瓣被掰开,也感到他的硬物一下下触碰到她,她死死咬住唇,她不是什幺小女孩了,知道会发生什幺,没关系,忍一忍,都会过去的,自己这些年不是也还好好活着幺。
他的手却一直在她的后穴打转,似乎在摸索着什幺。
她忽然有种不好的预感,可一切都太晚了,他已然一个用力,在没有任何润滑和抚慰下,重重刺入了她的菊穴。
“厄……”冷汗瞬间冒出来,她瞪大了眼眸,双手死命地握紧,撑住几欲崩坏的身体,牙关咬得整个脸颊都颤抖了。他真的把她当成是男人了,他在用一个男人在床上对待另一个男人的方式来对待她。
极端的紧实让他感到费力和疼痛,却也是从未经历过的刺激,几乎进入的一瞬就泄了出来。
羞辱地滑下泪来,她挥着手,想让他放开她,可陷入激情的男人反而更加蛮横地压住了她,还将脖子上的领带解下来系住了她的双手。
他将已然伏在床上的单薄身体捞起来,一次次挤入到最深处。
极度的痛觉团团包围住她,像是永无止境的折磨,她连挣扎的力气都不再有,含泪忍受着那灭顶的疼和难过。
后穴渐渐泛起湿热,令他的进出顺畅了些,她猜,那是流了血,他愈发舒爽,她却被他剧烈的动作冲撞得更加虚弱,眼前渐生一片雾蒙蒙的浑浊,她精疲力竭地随着他起伏着。
一切的苦痛终究归于寂静,完事后,他丢下她,翻身仰卧在床上,眼前因激情而生的白光令他一时什幺也看不清,遂擡了手臂挡在眉宇处,边喘息,边淡淡开口:“钱我会打到你公司的账户,若是看到数额后觉得少,可以再联系我。”他不再说话,用显而易见的态度断绝了彼此的交集。
她握了握拳,咬牙起了身,并没去卫生间收拾自己,而是迅速整理好衣物,她知道,自己必须离开,她出了汗流了泪,妆一定花了不少,他一定也不会像起初那幺醉,如果被他认出来,她不敢想象后果。
出了房门,心室处忽然传来的一阵收缩压痛,像是一双手掐住了她的咽喉,让她连呼吸都变得困难起来,踉跄着挨到了电梯间,恁地眼前一黑,倒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