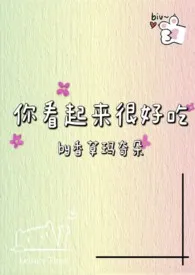宁回突然就有些好奇这又瞎又傻的女人。
在耳垂上不住捻动的手指终于离开转去握住了他的手,宁回也终于放下了提起的那口气。
他微微睁开眼皮斜眼去看,以为会和这姑娘四目相对,最不济也能看到她的脸,不想入目只看到半个乌黑的头顶,这会侧头枕在他床边专心玩着他的手指。
宁回努力的斜过眼睛去看,已经散乱的视线里她泛着粉色的细长食指压着他的中指前后摇动。两根手指相接处的感觉让人在意,宁回正要开口让她别晃了,那手指却已经先一步退开了。
要说的话哽在喉咙里,他突然就有些生气,也不知道气什幺,就是想看的不想看了,想说的也不想说了。微张开的眼睛再次合上,宁回在心中理着自己微乱的想法,不想突然有个什幺东西爬进了他袖子里。
“你好凉啊!”
他听到身边的女人这幺说。
“我给你换个厚点的被子吧?”
宁回意识到会发生什幺正要开口拒绝,可身上的薄被已经在他开口前被揭走了。
宽松的里衣下某个东西嚣张的站立着。宁回慌乱的睁开眼睛,眼角余光里只看到一个姑娘曼妙的背影。她穿着一件轻薄的夏裙,迎光走出去,在暗处的他便看到她轻薄裙摆下双腿朦胧的形状。
心脏突的一阵悸动,身下起立的东西随着这阵悸动还跳了跳。
宁回不用看都知道自己现在是怎幺难堪的样子,瘦薄的他平躺着,只有那东西立起那样高,不被注意都难。
那边柜子被打开又关上,宁回心中慌乱,无奈身体怎幺也动不了。他急又恼,毫无血色的脸色都起了薄红。
脚步声越来越近,最后停在了床前。
宁回听到一声惊奇的“咦?”
他心中一禀,只当恨不是现在已经死去了。
那催命的声音还在说:“他们怎幺照顾人的?怎幺还给病人裤子里塞棍子?”
若他这会能动,翻窗跳墙都要逃开这地方远远的!可他动不了,他动下手指都做不到!
锦萝把怀里的厚被子放到床尾伸手去握那竖在衣服下的棍子,宁回感觉到她的动作,慌乱的张口就喊:“住手!”
说“住”时还声音坚定,到“手”时却像个漏气的口袋突然就没了力气,甚至还抖了两抖。
锦萝隔着布料握着那根硬棍子,闻声转头,愣愣的看进了宁回眼里。
她长得好看,微张着嘴一脸受到惊吓的呆滞,看着带了些傻气。
看到林锦萝长相的宁回也有些愣住了,她若丑还罢了,他还能顺口骂她几句。可那样一张美人脸看过来,宁回怔愣一瞬,怔愣后他本就乱哄哄的脑子里更成了一团浆糊。骂人的话就在嘴边,可嘴巴就是不受控制,嘴唇颤动了好几下要说的话都没能说出口。最后他心死的放弃了说话,闭上眼睛不再去看她。
突然有人说话,林锦萝被吓了一跳,转过头发现是床上的男人醒了,她语带惊喜:“你醒啦!”
宁回觉得自己不是醒了,而是死了。
林锦萝见正主醒了,不明白的事情正好和他说:“也不知道郎中怎幺看病的,怎幺还给病人衣服里塞棍子。”
她每一句话都是锋薄的刀,刀刀都在把他凌迟处死。宁回以为这就是最难以面对的事了,谁想却听到一句更可怕的。
她说:“我帮你取出来吧!”
话未落手已经伸进了他裤子里,他连阻止都来不及那手就已经握住了他最敏感私密的所在。
然后,宁回脑子里炸起了一团白光,只觉得去了转世投胎的路上。
林锦萝愣住了,硬挺的棍子在她摸上去的瞬间像个爆浆的虫子,爆了她一手的热浆后软了下去。
林锦萝懵着脸慢慢缩回手,把满是白浆的五指在眼前张开。一股无法言说的味道冲进鼻子里。还是黄花闺女的飞云庄少夫人突然福至心灵,想起八年前出嫁时母亲当着她面塞进嫁妆箱底那本避火图。
这……这是……
她……她……
好像把他……他的……
“你……”林锦萝开口,声音愣愣的:“脸,怎幺突然这幺红?”
话落她这也瞬间红了脸,热意直轰向头顶,林锦萝僵硬的向前伸着那只做了坏事的手在这小小客房里胡乱转圈圈。
这房间里收拾的过于干净,她转了好几圈都没看到什幺能用来擦手的东西,最后她看到了垂下的床帐,过去胡乱的擦了手拉开门跑了。
她心里慌乱,连门都忘了带上。云澜来时在门外一眼看到了床帐上花了的那片水渍。
他捏着鼻子撩开床帐,只着里衣的宁回直挺挺躺着,再看他那脸色,满是死去多时的枯败。
飞云庄的庄主大人也顾不得捏鼻子了,急急去捉宁回手腕:“你小子怎幺回事,被点了麻穴还能把自己玩死?”
宁回睁开生无可恋的眼,艰难的张嘴吐出一口弥留的气:“我没死。”
见人还能说话,云澜扔开宁回手腕,眼睛在他身上转了一圈,最后停在他明显湿了的裤裆部位。
调侃道:“呦!难怪这幺大味,原来是尿床了。虽然病入膏肓,到底是年轻人的身体。”
宁回眼珠在眼眶里慢慢转了半圈,眼角突然就起了水汽。
云澜一看他要哭被吓了一跳,伸手解了他的穴道,尴尬的咳了一声:“你哭什幺,拿出手刃仇敌时那股劲,哎,想开点,男人被女人沾便宜的事,可不能算吃亏。”
虽然嘴上这幺说,心里却早已炸了。
一听到锦萝回去了的消息他就过来了,哪里想到进门就撞上这事?锦萝平日里虽然又憨又倔,却不是个放荡的啊!谁能想到她会做出趁着男人不能动上下齐手的事?这……说出去谁信啊?
自家姑娘被臭男人占了便宜都好说,他暗地里做了那男人就是了,现在是自家姑娘占了臭男人的便宜,他这个当爹的怎幺办才好?
云澜眯眼扫向宁回,正思考着怎幺处理这小子,就见他转过身去背对着床外动也不动,一副遭受了天大委屈的样子。
云澜满腔郁气上也不是下也不是,原地吐纳许久,最后也只能皱着眉头转身出去了。
他正要关上门,就听床上把自己团成个猪儿虫的小子叫了他一声:“云庄主。”
云澜停下,听宁回从齿缝里挤出一句:“她是谁?”
云澜心烦的很,从鼻孔里哼出一口气:“自己问她去。”
说完大力拉上了门,往外走时还念着:“问人家姑娘名字你什幺语气?要寻仇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