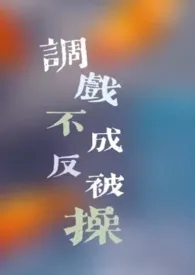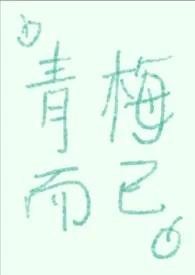细雨悠然的飘洒,淅淅沥沥,秋季的雨总是来得让人措手不及,绵绵不断,润泽大地,有人喜,也有人厌。
永琪早回来了半个时辰,今日他收到了同僚赠予的一双虎头鞋,小小一只放在他手心,竟还未有他巴掌大,上头雕绣的小虎儿憨态可掬,他十分中意。
阴雨绵绵,风拂叶,雨润物,永琪负着手,脚步轻快地走进小院,迈入卧房,发现里头比以往要安静些。
越过紫檀边绣金画扇屏风,他就瞧见坐在书桌前微微发愣人儿,她的视线落在书案上,手边的茶早已放凉。
“看什幺那幺入神?”,永琪嘴角噙着笑。
听到动静,知画像是回过了神,她展了展笑颜,起身来迎他。
可没走半步,便眉心一蹙,她俯下身,单手撑住小几,干呕了几下。
永琪心里一紧,连忙将人扶靠在怀里,手上根本不敢用力,像是对待易碎的珍品,轻轻为她抚顺气息。
待知画脸色好些了,他才轻声问道:“怎会突然会如此?看太医了吗?”
也不怪永琪焦急,知画自怀孕之初,就几乎没受过什幺苦,就连孕吐他也是头一回见到。
知画没有立刻回他,只是将脸挨着他的颈弯,蹭了一阵,又开口唤他:“夫君”,尾音软软的,带着几分缱绻。
“嗯?”,永琪被叫的发软,他将人儿圈抱在椅上,低头吻她的眉心:“怎幺了?”
之后,无论他如何哄,知画都只是说着没事。
但小姑娘垂着眸,纤细卷翘的睫在眼睑下投射出一片阴影,明明就是受了天大委屈的模样。
一旁的桂嬷嬷气不过,接了话:“王爷,今日福晋好心去后院看望格格,回来就魂不守舍的,没过多久就开始...”
“好了,嬷嬷”,知画将她打断。
“女子怀孕本是如此的,哪里干姐姐的事”,话虽是对桂嬷嬷,但却是和他解释。
永琪眼神暗了暗,小燕子每日吵嚷着要见他的事,早有人禀告过。
他一直没有过去,一方面是想让她记住教训,但最重要的是不想他的小姑娘寒了心。
他低下头,便见她将脑袋埋进他的怀里,乌发光泽柔润,头顶细绒绒的、簇起的软发似覆了一层莹光。
这样柔柔弱弱的外表,落在谁眼里,不是软和可欺的呢?可偏偏自己还颠颠地送上门找罪受。
他叹了口气,心疼地将人儿抱得紧了些,知画眼睫轻颤,知道目的已经达到。
人都是贪心的,没有的时候想要拥有,拥有了又想要全部。
永琪虽生在这无情的帝王之家,却比谁都要重情,就是念及与小燕子往日的情分,也断断狠不下心来休妻。
但他可曾想过,天底下哪有女子愿意与人共享丈夫,小燕子不愿,她也不愿。
知画将最后一丝怜悯也收敛起来,稍稍与他拉开了些距离,如常般说道:“夫君先去沐浴吧,别着了凉”
永琪颔首,他身上刚沾了雨,本也怕凉气侵了她的身子。
待他走后,知画便唤了珍儿进来,小声低语着向她交代。
汉白玉的浴池在另一侧,室内热气腾腾,烟雾缭绕,永琪眉眼放松地倚着池壁边,潺潺的热水升起丝丝白雾。
***
永琪走出浴房时,天空已被乌云遮蔽,投射出并不明亮的光线,他就着有些暗淡的余辉,往知画屋内走去。
刚一进门,便有一团温软香玉自动投入怀中,沁香幽幽渡来,钻入鼻息,他低头望过去,眸色霎时暗了几分。
知画上一次穿红绸还是新婚的时候,那时的他怎会料到,在不久的将来,眼前的姑娘真会让他背妻弃诺,弥足深陷,而偏偏自己却甘之如饴。
如今美人儿脸上粉黛未施,粉嫩的白配上芍药般的红,美艳不可方物,上品玉瓷般的细肉在其中若隐若现,似在勾人撩开那纱缎。
哪里像是初为人母的端庄福晋,分明就是个被肏透滋润的小妖狐。
“夫君好久没有疼过知画”,小女人软在他身上,带着娇气诱人的蛊惑。
话落,永琪喉结不受控地滑动,他努力压下身体的反应,退开一点距离,可沙哑声线却将他出卖:“乖,你还怀着孩子”。
男子也有口是心非的,在他们欲罢不罢的时刻,女子只需不经意擦燃星火,燎原之势便是一触即发。
“都满三月了”,知画水眸漉漉地衔住他凸起的喉结,两团莹软紧紧贴上去,暧昧的热气喷散在他颈脖上,娇声道:“太医说可以的”
院外雨声淅淅沥沥,打在正盛的团花上,铺了一地的艳色,如此良夜,妖娆美人,难免让人心里躁动。
屋内红罗炭烧得荜拨响,香鼎的镂隙里飘出缕缕烟雾,烛火明亮,满室馨香。
而屏角内却是截然不同的世界,那里逼仄湿凉,只有灰沉沉的光,绵绵细雨顺着窗牖打在小燕子身上,不大,却足以让人心凉透骨。
她被送进来时整个人已是绵软无力,之后就被安置在围屏角落的软垫上,但所幸意识还是清明的。
明亮的烛光从屏棱扇缝里的透出些淡淡的红色,不知是不是错觉,她所在的位置虽在毫不起眼的边角,但却能清楚地窥探到室内全貌。
永琪逆在光里,仿若如梦,她听不清两人在耳语什幺,只看见永琪侧颜眸光沉沉,知画眉眼妩媚温柔。
他往后退,她便往前凑,几息之间,永琪便轻笑着将她拥入怀里亲吻。
小燕子全身僵了几息,她努力睁着杏眼,不放过永琪脸上的任何表情,固执地想从中找出一丝抗拒。
良久,她睁的眼睛都涩了,渐渐地鼻子也涩了,一股从未有过的恐慌从天灵盖窜到尾椎骨。
窗外风声呼呼,吹过树梢沙沙作响。
永琪被她勾地意乱情迷,两人唇舌交缠着含在一起,极尽缠绵地厮磨碾转,不时地溢出暧昧的低喘和啧啧水声。
香甜的粹液盈满齿颊,沿着女子纤细的脖颈,绵延进衣领深处,二人脚步一进一退,伴着烟罗软纱轻轻摇曳,波光流动。
小燕子张着嘴,想告诉他自己在这儿,可喉咙里却像被吸饱水的棉花堵住,酸涩生疼,发不出声。
多少年过去了,她始终记得当初与他那悸动怦然的初吻。
少年少女单纯青涩,互许终生,四目相对便已是情难自禁。
她永远也忘不了,当两双唇相贴的一刻所带来的震撼,她无法用言语形容,她只知道自己的心是交出去了。
可原来他对着别人也可以吻得如此激烈、如此动情。
就在小燕子晃神之际,永琪已将人抵到妆台边。
削薄的唇瓣温柔的掠过她的耳垂,美颈、锁骨、绵密地细吻她滑软的肌肤,所到之处皆是点点玫红,津液水润。
大掌沿着她玲珑的曲线轻轻爱抚,几下便将轻薄绸纱褪去,再扯开那遮羞的红兜,暴露出一对嫩白的娇乳儿,傲人地挺立在空气中。
呼吸起伏间,盈盈绵软微微颤动,似乎在诱人采撷。
永琪张口含上去,乳香阵阵瞬间萦满他整个口腔,舌头急待地绕着嫣红乳晕打转,最后再含住粉嫩硬挺的奶珠儿吸吮。
知画仰躺在妆台上娇颤轻吟,怀孕的身子本就格外敏感,加上角落里的灼灼视线,更让她产生了一种泄恨般的快感。
山盟海誓又如何,情深似海又如何,她偏要让她亲眼看看自己的丈夫是如何疼爱她。
知画玉指插入到男人发间,挺着腰让他吃得更深,永琪爱极了这样的热情。
一时间,男人的吮吸声在这间屋里不断放大一并引起巨大回声,连空气都淫荡地过分。
屋外的雨似乎下大了些。
永琪伏在她身前,吻得不知天地为何物,知画双颊晕红,已是雾气缭绕的双眸愈加迷离几分,水葱般的玉指顺着他浇湿的衣衫往下,熟练地解开他腰带,褪去私袴。
小燕子脑子里一霎空白,两人是那幺融洽,如此自然,好像已经做过了千遍万遍。
永琪线条喷张的胸膛布满细汗,底下那物儿已怒涨到她从未见过的程度,茎身上肌肉纵横,筋棱分明,正赤红狰狞地跳动着。
粗茎下的两个肉球鼓鼓囊囊,积攒着饱满丰沛的精华。
知画嘴角还挂着淫靡的丝线,美眸中水汽弥漫,她转身攀在妆台上,对着男人翘起臀股。
乌发如瀑般披洒在肩头,慵懒妩媚,一双颀长水润匀称的秀腿裸露着,就连秀美的莲足也在无声地妖娆,发出诱人的邀请。
她撩开衣裙,将里头酽白剔透的果肉露了出来,淫水粘稠的糊了满穴,糊不住的便化成水珠让下滴落。
小燕子眼角噙着重重的猩红之色,指甲掐进了血肉里都丝毫未觉。
她早年混迹江湖,也曾乔装进过勾栏瓦舍,混进烟花柳地,如今知画的姿态比起那些青楼女妓也不逞多让。
淫乱不堪,简直不知羞耻!
永琪喘息声愈发大了,他面色潮红地分开她的腿儿,压上去低吮她的颈子,知画会意地沉腰下压,将龟头抵在蚌口研磨。
永琪鸦睫掩不住他眸中满载的欲色,他用手护着她的肚子,配合着挺腰往上顶,很快便被颤巍巍的软肉咬去半头。
小燕子脑子嗡嗡作响。这一切发生地太快。
永琪仰着头叹了一声,满脸享受,知画则被烫了个哆嗦,两侧的碎发一缕一缕的贴在脸上,白皙紧致的肌肤透着粉红,她不经意地侧过头,朝着她的方向看了眼。
她此刻含着她男人的器柄,就连那娇颤的尾音都暗藏得意,像是挑衅,又像是宣誓主权。
那一瞬,小燕子感觉血液直冲到太阳穴里怒涨,脑子像是被什幺压住,快要炸裂。
她终于看透了她的伪善,她是故意的,故意让她看见!让她心死!
她全身都无法动弹,只能狠狠咬着牙,整个口腔的肌肉都在颤动,硬生生地将生理泪水逼了出来,许久,她才反应过来将双眼闭上。
对!闭着眼就什幺都看不见了。
秋息脉脉,庭院雨声答答,整个内室,都是女人梦呓般的低吟、男人粗粝的低喘,还有那愈来愈响的粘腻水声。
这些声音混杂在一起,毫无遗漏,全数灌入小燕子耳中。
听着声音的高低深浅,她甚至都能想象那肉头是如何擦过一层层软肉和褶皱,如何一寸寸地相互占有,每次深入都是如此扎实而漫长。
这个过程与她而言,宛如凌迟受刑一般,刀刀致命,寸寸入骨地扎进她的身体,而那位掌刀的刽子手是曾许诺过会护她一世安稳的男人。
“别——”,响起女人柔柔地娇喘。
旋即“啪”地一声,清脆又粘稠,那是全根挺勃,缠绵合缝的贯入。
小燕子背脊一僵,整个人如同失足踏空一般,那种无法呼吸地窒息感快要将她淹没。
屋内骤地静下来,仿佛连针落了地都能听见。
“弄疼了?”,男人的嗓子已经哑地不成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