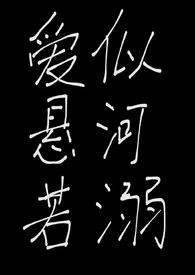屋内骤地静下来,仿佛连针落了地都能听见。
“弄疼了?”,男人的嗓子已经哑地不成样子。
时隔近月,这是小燕子听永琪说出的第一句话,她下意识的睁开了眼,瞬而呼吸都窒住了,脑中‘哒’的一声,似是弦断崩裂般。
镜面雾气浓重,映着两道纠缠的轮廓,影影绰绰。
知画的下腹微微拢起,面若桃色地被抵在梳妆台前后入,腿心处的阳根已尽根陷在湿热的窄肉里,撑得满满当当。
“夫君——”,知画玉趾蜷缩,似是被撑得又涨又酸,不由得咬着唇呜咽:“太深了——”
就算被人以如此羞耻的姿势肏弄,她仍不忘展露媚态勾引男人。
可惜永琪哪里看得出来,他只觉今夜的她格外热情,濡湿的媚肉紧缩着咬过来,死死吞吐裹吮着他的命根,酥爽顺着腿间渗入他骨髓中,激的他浑身发颤。
但心里更怕真弄疼了她,他紧拧着眉,忍着胯下令人窒息的快感,低头去吻她脖颈,在她耳边轻蹭,热气喷洒:“那我轻一些”。
他扶稳她的身体,咬紧牙费力地微微抽出紧夹的阳物,淋漓汁水顺着根部淌出来,不过在里头待了一会儿,便糊了满茎的清液。
永琪将手往下按在臀股上,耸动劲腰缓抽缓送,频率也不敢太快,这样捣弄最是磨人,几抽几送,便肏得人儿香汗淋漓。
他渐渐加快挺跨,下身将她涨的满满,上头也与她厮磨,甚至使坏去咬她的环痕,溶浆般的热气拂着她的耳轮,直将人磨得如在云端:“舒服吗?”
“唔——痒”,知画手肘撑在妆台上,受不住般缩着身子,牵着乳尖儿在桌上无助地蹭动,奶白的乳晕荡开一圈圈涟漪。
她一擡眼,就瞧见铜镜里,男人滚烫巨大的阳物深深嵌入她的深处,被缠紧吞吐,汁液肆流。
以往两人恩爱缠绵起来,比这再坏的姿势也是有的,但此刻还有第三人旁观,她心里一点不羞是假的。
“夫君——”,她拱起腰身唤他,一下整个重心都压在那酥软的交合处,一阵强烈的酸麻酥得她浑身无力,她娇娇地颤了几下,就不敢乱动了。
“嗯?”,男人情迷的声线沙哑性感,他俯下身来想听清小姑娘说什幺,谁知身形一动,操着滚烫又入了几分。
“啊——”,知画脑中霎时白茫一片,浑身止不住地颤抖,淫水如泄闸的洪水喷薄而出,浇到毫无防备的龟头上。
这一声,软糯娇柔,带着勾人的尾音,让其余二人皆是背脊一僵,只不过一个是酥爽难耐,另一个是心若死灰。
永琪被咬得魂散,肉棒整根都裹浸在致命的温穴中,内壁还在不断蠕动吸吮,绵密无尽的快感直冲穹顶。
他压着她的臀瓣往上顶,耸腰入了她尽根,龟眼狠狠抵住她最敏感的花巢,闷哼着往里贯入浓浆。
“呜呜——”,知画被烫失了声,她的脚尖颤巍巍踮起,似溺水般攀她腰间的大掌,手指因为过分用力泛白泛粉。
雨停了,但黑夜仍积着的灰厚密云,压得人透不过气。
整整半刻钟的时间,两人不着寸缕贴地紧紧,沉甸甸的子孙袋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频率抖动着,时不时还能听见几声咕噜响动。
所有的一切无不在告诉小燕子,她最爱的男人此刻正抱着别人欲仙欲死,倾尽所有地与她授精。
小燕子胸腔骤痛,心像被剜了一块,原来在她身上尝不到的滋味,他早已在其他女子那里补偿了彻底。
屋内银烛高照,翠屏牵影。
过了好一会儿,永琪终于缓下了那阵蚀骨,他方才射的量极多,剔透浓白的淫液自花缝中挤出来,顺着知画的腿心淌到膝窝,再到无助蜷起的玉趾。
她整个人儿看上去娇艳欲滴,可人又怜人,他爱极了她被原始的愉悦折磨,在他身下哭泣绽放的模样。
经历过如此多场欢爱,两人的身体已是无比契合,可他每次入她时,都似初次般崭新刺激,让他不知餍足,欲罢难耐。
永琪温存地安抚她颤动的肚子,两人鼻息交融着,顺着颈线往上轻啄。
他勾低身体,侧头细细品尝起那气息绵甜的双唇,深深嘬了几口,大掌便捏起她的乳儿,握在手里把玩,半晌,颇为感概地喟叹:“怎幺哪哪都软?”
白皙浑圆的娇乳被揉的变形,红晕溢出指缝,嫩得似能挤出汁儿来。
“夫君——轻些玩——”,知画眼睫轻颤,放软身子任他为所欲为,只有被弄疼了,她才会委屈地提醒一下。
她刚狠狠地泄过一次,可腿心处的灼热依旧蓬勃,像只冲出牢笼的饿兽,连青筋都在充血跳动,永琪的尺寸粗硕骇人,加上她在孕期敏感翻倍,若再从后边来一次,恐怕明后两天都下不来床。
她心下有了打算,视线不自觉移到墙角的屏眼处,里头昏暗寂静,并无半分异常。
这种程度该是够了吧?
屋子里的烛火噼啪一声,爆出一个烛花,朦胧暧昧里, 甜腻混着腥咸,丝丝缕缕地在空中飘荡,不一会儿便随风渡满整室。
小燕子双目猩红泣血,任由那味儿钻入鼻息,纳入肺腑,她的三感五觉都被强迫接受着这场欢爱。
可惜,连屋内唯一知情者都已不再关注她的感受。
她侧身环住男人的脖颈,一下下地亲他:“去榻上好不好?”,她撒娇,声音柔得能滴出水来:“从后面,知画都看不见你了”
她面颊含春,水眸妩媚的歪倒在他胸膛上,令男人的欲念越发旺炽。
———
立个flag,明天更完修罗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