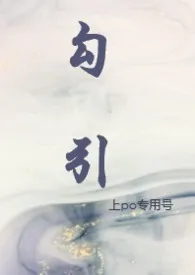从B市回首都的路上,张三抢到的是卧铺票。
关于这卧铺有个讲究,下铺最优,上铺次之,中铺最差,为什么呢?
下铺最方便,能拥有个五尺半长的桌子,满当儿摆下两瓶矿泉水和两桶泡面,还能把脚踩在旁边儿的暖气片子上。
尽管下铺的被子永远被攒成球当枕头靠,床铺的一角永远被踩出脚丫子的形状,这两点让张三很难受。但张三觉得下铺还是要比上铺好——上铺除了看着沾着灰尘的车顶就是睡觉,手机信号也被完全被屏蔽了,活像个几十年不洗澡的龟壳。
不把目光放在那索然无味的中铺,在下铺的床桌旁,
张三举着个相机,对好光圈和快门,像是架起狙击枪一只眼睛紧闭,另外一只瞪着取景器。
“专业人士”都是这么搞的,张三也自诩半个专业人士,取景器里的栅格线把眼前的画面分成了几部分,由前景到后景是:窗户、倒影、站台;由左边到右边是:空冰红茶瓶子、闪着LED灯的标牌、对面靠着窗小憩的女子那溢出来的臀部,窗户边上的小凳儿实在是放不下一个成年人的屁股。换位思考一下也不是不能理解,毕竟过道就那么窄,屁股舒服了,餐车过不去了,乘务员姑娘就该上火了。
所以,不少人选择和下铺的好同志商量能不能也给自己的屁股分点儿面积。当然也有不善言谈者直接坐下来,目不转睛的盯着手机,好像手机已经同意了他这么做一样。张三旁边的妙龄女子亦是如此,更加尴尬的是,划着划着手机屏幕,她还倚着张三瞇了起来,从鼻腔后面的位置传出阵阵呼声。巧合的是,张三也是个不善言谈者,只能举着相机对着外面,看似专业,实则透过玻璃反光端详着对面女人的臀部。
身边的女人终于醒了,她脸上的粉底似乎没有抹匀,张三没发觉左臂上沾着星星点点的白色粉末儿,直起身嘀咕着“借过一下”,径直走到车厢之间的衔接处抽烟。
叼着烟嘴猛吸一口,不由得耳根后面发麻,像是两个高压血泵把新鲜的血浆顺着脖颈冲进大脑,张三觉得一身轻松。
诚然,有那么几秒钟,困扰着张三一整天的头痛烟消云散,连负责把太阳穴牵引住的三叉神经也不再紧绷。不过几秒钟后,他的身体逐渐适应了尼古丁,被“血泵”推开的阵痛又聚拢起来,乱麻似的,牢牢的钉在大脑深处。
快乐这东西可真他妈短暂啊!
张三把烟蒂掐在车门旁的烟灰斗儿里,关上这不锈钢的小抽屉,跺跺脚,接着蹲下来看着窗外飞驰而过的夜景。
郊野的风景在一般人看来是乌漆妈黑的,没有任何东西值得注目。
张三不一样,他推推方框眼镜,拧下镜头盖儿,又把眼镜堵在取景器上——他自诩是个艺术家、摄影师。
如果此时此刻以车窗外500米的视角回过头看着张三,拍一张照,这幅作品(勉强可以称它是作品)的名字一定是《艺术家,在路上》。在张三的视线里,夜空分成了几层暗色调,从近处的藏蓝、墨青色扩散,越远越暗,仿佛国画颜料的调色盘。目光所极,黑夜中防护林向着反方向奔跑,车轮声、风的呼啸声交错不断,LED灯光牌划出一道道转瞬即逝的流星。
张三的确不是普通人。
从小,张三既觉得自己天赋异禀,在艺术方面指定会造诣非凡,又极其爱面子,总能自圆其说。其实这样的人最聪明,但往往因为好面子吃了不少哑巴亏。
小学六年级时,张三被班主任从女厕所里薅出来,顶着通红的小脸,左手拿着傻瓜相机,右手攥着准备销毁的胶卷。尽管一再说明自己是取景,拍摄老校舍的怀旧风格云云,眼前这个脸色蜡黄的中年妇女却怎么也不相信她。
“小二流子,看我把你爸妈叫来收拾你!”头顶上这张嘴咬牙切齿,吐沫星子飞溅到小张三的头上。
“我不是!我没有!”小张三闭着眼睛喊道。
其实站在被告的角度来看,少年怎么会对中年妇女感兴趣呢?实在是不可理喻:这个年纪的少年的理想对象必须是洁白的,像刚凿出来的冰雕一样光洁;像还没落地的雪一样白皙;面颊最好白里透红,但须红的恰到好处,是那三月上旬的桃花颜色;声音一定要悦耳,最好似那乡间摇曳转动的风铃;最关键的是——被采摘时她的泪滴,要像初春的甘甜晨露。张三怎么会去偷窥这老女人呢?
在希伯来圣经中,独角兽尤为垂青“洁白”的少女,它们会把充满魔力的角插进少女们的阴户,注射生命精华,就这样生下自己的神圣子嗣。狡猾的人类猎人利用这一点,藏在草里等待独角兽和姑娘们共赴巫山云雨时,冲出来把角切掉,这是这种凶猛生物唯一的破绽,因为欲望占据了脑子,他们束手无策、任人宰割。
但随着时间的发展,人类女性将少女和猎人二者的特性融为一体。在独角兽兴头正浓时自己动手割掉它的作案工具,独角兽就再也不是独角兽了,它们沦为四只脚的牲畜,只剩下睡觉、进食、劳作。
然而,小张三面前的中年女人显然只是具备了猎人的天赋,她张牙舞爪地拽着小张三的衣领,往校长室拖。无论他怎么解释,原告只有两句证词,还都准确的无懈可击。
其一、张三是在女厕所作案的,他是带把儿的,女厕所不是他该出现的地方。
其二、张三的脸是白的,被抓的时候他脸蛋比猴屁股还要红。
综上所述张三就是犯人,犯人除了张三也没有别人。
这件事让张三发现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或者说宇宙的真理:女人的思维方式和男人不同!
男性在思考问题时,逻辑往往占据上风(非交欢时段),比如说钱包丢了,他们首先会梳理钱包中有多少卡、多少票子、重要程度高不高,再回顾丢东西前后自己的行进路线、有没有容易丢失物品的场景。如果当真丢了,那么会根据预算,选择一款功能性强、有颜值、还不方便丢的款式,当然还要预约补办丢失的证件。
女性对这个问题的加工过程十分魔幻:丢了?去找!找不到?买!就好比把杂乱的、拧巴在一起的毛线球抛给她们,她们在经历剧烈的感情波动后,总能找到混入其中的线头,方法不详。
在这件事儿十年几之后,张三对这个“真理”有了更明确的认知。
在大学城外的宾馆一条街上,两边的节能灯光从紧闭的窗帘下倾泻出来,交相辉映,如果仔细聆听,男男女女的呻吟声不绝于耳,分不清是高兴还是痛苦,整条街像极了摄人魂魄的恐怖峡谷。来这里的大部分人是为了做爱,在街尾那个名叫“丽日豪华酒店“二楼1403房间里的张三自然也不例外。
在首都,张三从没见过只有两层就敢自称“豪华”的酒店,房间里的灯光过于黑暗,以便掩盖地面上用84消毒液都抹不掉的精斑、血渍;他躺的这张床只要剧烈运动就会发出声响,“吱呀吱呀”的,不幸中的万幸是:这床叫的声音盖过了左右两边大床房传来的叫床声。
张三暂时失去了思考的能力,倚靠在油光锃亮的橡木床头上,四肢舒展开来。一支“小太阳“香烟斜着粘在他的嘴唇边,烟灰已经落了一节到他的左胸上。
小夏骑在张三的小腿上面吸吮着他的大脚趾,雪白的臀部上还洒着“独角兽的生命精华”。
小夏本名夏茹,张三和她在一个社交软件上认识的,相谈甚欢。但归根结底还是各说各的,张三自诩天赋异禀,在艺术方面必定造诣非凡,从小他就是这套说辞。事实上,自诩的天赋和被认可的天赋一个是天上一个是地下,而张三从来没有取得什么建树,也不懂用什么艺术形式表达自己的情感——他是个正被一个又一个毛线团塞满的空壳子,但他的思维是理性的,这导致他不能像女人那样精准地理出那些线头。
夏茹也的确不是普通人,她与张三正好相反。不过尽管她像个男人一样梳理出来了所有的线索,所有的线索又都直指张三是个草包,但快要得出结论时,她的情绪波动又让大脑混乱起来。她索性不想了,俗话说解铃还须系铃人,当天晚上她买了趟累计20小时,去首都的车票——只有肌肤之亲去品尝一个人的味道、吮吸他的体液、和他融为一体,才能看到对方灵魂的颜色。
于是就出现了刚才那一幕。
张三虽然不知道这样的行为有什么含义,但脚趾尖传来的酥麻感觉以及面前雪白的大蒲团中心那黑洞的深邃感,让他无暇思考。张三只晓得两件事:
其一:男人理性、女人感性、床上反之、猎人不算在规则内。
其二:如果不是法律的保护,眼前这个虎妞能把自己吃的啥也不剩,骨头都磨成粉末熬汤喝了。
回想到这里,张三又头疼起来,他又点起了一支烟。
尼古丁进入血液的快乐是短暂的,多巴胺的快乐是短暂的,刺激味蕾的快乐亦是短暂的。
一根烟能抽两三分钟,尼古丁的作用时间大概有半小时,半小时之后人就会空虚,此时如果没有补给品,倒不如不抽。
同理可得,一段感情也是有保质期的,假如一开始太过刺激,后面的阈值会越来越高,新鲜感荡然无存,这时候如果搞不出新的花样,关系就会破裂。当初张三和夏茹的感情就是遭遇到了这个问题,可惜在几年之后的今天张三才悟到这点。张三认为,现在不是忆往昔的好时机,因为头很痛,美好的记忆最好不要被干扰,这是普遍搞艺术的人的精神洁癖。
头痛的罪魁祸首,是个女人。张三掏出手机,看了看锁屏,现在是十点半,二十四小时前那个女人就坐在张三的跨上像条蛇一样摆动,抽取着张三的灵魂,他感觉自己两腿之间沼泽泛滥,这一度让张三认为自己身在仙境,享受着仙人的待遇。
但也因为这个女人,现在张三头皮上的伤口正疼、才刚刚结痂。
火车上的鼾声、小孩子的吵闹声、窗外车轮的滚动声与呼啸的风声此起彼伏。
这二十四小时,张三可一点儿没睡,并不温柔的白噪音激发了张三的灵感。
他拿出随身携带的账本儿,倒过来翻开最后一页,准备把这段魔幻现实的经历写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