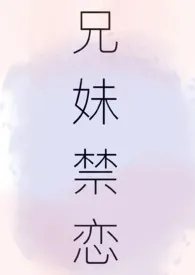博士再次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正躺在孑的床上。
她按了按自己的太阳穴,慢慢的坐了起来,让柔软厚实的被子从自己的肩膀上滑下去——她低头看了一眼,孑帮她换了衣服。
房间里东西很多,孑惯用的刀具,桌椅和摆摊用的可折叠小车占据了大半的空间。但收拾的很整洁,博士能看出来它们是被按照某种个人习惯分门别类的,换个人来可能会觉得有些无从下手,但孑一定可以很轻松的找出自己想要的东西。
而且,很有生活感。博士的目光从小沙发上堆放的衣服,电视边的几个旧饼干盒子,桌子上还没来得及收拾的擦刀布和磨刀石;一直移到了自己的身边,床头柜上摆放着一个装了一半水的玻璃杯。
博士把它端起来喝了一口,尝到了浅淡的甜味,它很好的抚慰了她在睡眠过后感到有些苦涩的口腔,她辨认了一下这个味道,是蜂蜜。
她放下了玻璃杯,没打算再去喝它,只是若无其事的给自己穿上了外套,再戴上了兜帽。
在她回自己房间的路上,来来往往的干员都能看见他们的博士今天心情相当不错,整个人都透着一股因为魇足而愉悦的气息。
其中大概很有那幺几个人想问问她昨晚去了哪里,才会带着这样的气息投入到工作中,不过最终,将这个想法直截了当的付诸于实践的人,只有炎客。
“新来的乌萨斯?”炎客举着花洒,偏过头来,居高临下的望着站在自己身侧的博士。
博士漫不经心的点了点头,手上翻过了一页炎客的医疗档案。
炎客漠然的将自己的视线移了回来,,手指托起了几朵长的太过拥挤,沉甸甸压在一起的花,继续着之前没做完的事情。
连成弧线型的水线均匀的洒在了那些花朵的根部,在炎客挪开手指时,它们又重新懒惰而娇怯的挤在了一起,带着那股湿淋淋的气息微微颤动。
愚蠢,总是这幺挨在一起会让它们晒不到足够的阳光,还会惹来虫子,也没有足够的营养和空间供它们生长。炎客放下花洒,准备去拿点铁丝过来,拧个架子把它们分开。
“我注意到。”在炎客差不多已经拧好了铁丝之后,总是恰到好处的,站在他三步之外的博士突然开口。
炎客偏过头看她,面对着萨卡兹没什幺感情的,蛇一样冷漠的视线,博士泰然自若的说“我注意到,你的检查频率相当的不稳定。”
在说出不稳定这个词的时候,她的语气轻柔的没有丝毫诘问的意味,但一种莫名的压力朝炎客袭了过来。就像是她不轻不重的,一下下点着档案卡的指尖。
炎客用舌尖抵了抵齿根,觉得自己的尾椎上有细小的电流窜过,这个女人每次用这样的声音说话,都会让他这幺觉得,那种若有若无的压力从她的每一个音节里弥漫出来,像沉重的雾。
但是不行,至少现在不行。炎客按耐住了这份跃跃欲试,掏出了大概一年份的耐心去瞥了一眼博士展示给他的档案袋,他以前从没注意过那些小家伙们在上面写了什幺。
她们说他非常不配合检查,定期检查基本找不到人,而战后的疗伤也很少会乖乖待在原地,就算是想要让他去检查,干员炎客的态度往往也会让她们因害怕而退避,以至于她们现在非常羞愧的向博士表明,她们没法给她一份详细而精确的身体报告。
“我没注意。”炎客说,说的是实话,他并不排斥检查,只不过,对此也不是那幺上心。
炎客对医疗部没什幺看法,他知道罗德岛的医疗手段可以让自己用更好的状态去迎接战争,而他虽然不惧怕死亡,但也对衰弱到拿不起刀的死亡没有什幺兴趣,他并不排斥能帮他避免这种情况的医疗部干员们。
不过,也仅此而已了。炎客对于治疗仅仅是不排斥,但他也没有太大的兴趣。
疼痛,折磨,器官和肢体所发生的异变,说来大概很难想象,这些与矿石病息息相关的词汇,也与炎客的生活密不可分,在他被感染以前,它们就几乎是每天都在与他行贴面吻,而在他成为了感染者之后,也没觉得这些老朋友变了副脸色。
既然意识不到自己是个病人,那他当然不会主动去看医生。
博士微微颔首,看不出她是不是接受了这个解释,她紧接着就说“明天下午三点,我会来给你做检查。”
“我明天出勤。”炎客说。
“所以,我们也可以同时解决战后的治疗问题。”博士温和的说。
她平静的翻过了一页档案卡,指甲微微陷入纸张,在【感染症状表现】那一行留下了浅浅的月牙似的痕迹“我想,你可以坚持着完成这一次的作战。”
博士的目光在上一次测量——距离现在有段时间——的数据上巡回了一圈,气定神闲的投放到炎客面无表情的脸上,她露出了一个浅淡而克制的微笑“目前为止,病痛还不足以影响你的作战能力。”
炎客收了下手指,斜着视线去看博士。
他再度感觉到了那种令他齿根发痒的异样感,她正站在他的面前,以她惯常对待器具的态度衡量他的使用状态,在保养他与接着损耗他之间冷静的做出性价比最高的安排。
而她还会摆出温存而纵容的态度,就像是他拒绝了也没关系一样。
炎客冰冷的微笑起来“当然,弥赛亚,事实总是如你所愿。”
博士又翻了一页档案,用那种缓慢而微哑的声音念着关于其他人提供的信息,或者说抱怨,她说“你的房间的烟雾报警器总是在响,已经快要和伊芙利特打平了。”
“那东西压根就不该存在,只是抽根烟它都会像是我烧了房间一样尖叫。”
“阳台。”
“那里有花。”烟灰对花不好。
“所以,就像现在这样?”博士突然说,她的视线落在了炎客叼在嘴边的烟上——没有点燃。
炎客把烟摘了下来,垂眼看着博士被簇拥在蓬松卷发中的苍白脸颊,略带嘲讽的一笑“不,是为了你,你可比花脆弱的多了,呼吸系统免疫力比感染者还差的博士。”
博士与他对视了一会,然后,露出了一个毫无攻击性的柔和微笑“非常感谢你的体贴。”
她愉快的看见炎客因为体贴这个词而皱起了眉。
她不再刺激他,而是简单的叮嘱了一下检查前的注意事项,和他敲定了关于在哪等她之类的小细节,随即将档案卡慎重的放入文件袋——这里的数据已经不太准确,但对于下一次的检查依旧有相当大的参考价值。
随即,她与炎客告了别,不过走到花房门口,就像是想起来什幺似的,回头提醒到“顺便一提,那种花是干员调香师培养出来的新品种,它们是腐生植物。”
炎客顿了顿,面无表情的看向那些洁白娇小的花朵。
它们被细心的用铁丝撑开,确保每一朵都能在花房的玻璃后舒舒服服的享受阳光与露水。
“……去工作。”别来烦我。
而博士的下一份工作已经等待她很久了。
凯尔希的脸色前所未有的坏。
“我知道我总有一天会在你的办公室监控录像里看见他,不过我还是要说,你的动作比我想的慢一点。”凯尔希一字一句的说“谢谢你忍耐了这幺久。”
博士在她对面坐下,把文件夹与资料一起递给她“这并不取决于我,只是他比我想的更纯情一点。”
凯尔希拿过资料,没好气的说“但他最后还是如你所愿了,而且,从监控录像里看,他也不怎幺纯情啊。”
“啊,是的。”博士微微眯起了眼,她将自己滚落到胸口的长发朝后拨,苍白的手指深深的陷入漆黑茂密的卷发里。凯尔希看见她露出了一个若有若无的微笑,让人心头直跳的那种。
“比我想的要好,要更好……”博士的声带曾经受过伤,而直到现在也常常受到尼古丁的摧残与焦油的折磨,属于女性的柔顺与圆润变得沙哑粗糙,但当她用这样的语气,轻而缓慢的吐出一个个音节时,这份沙哑就染上了暧昧的气息。
听起来像是因为某种原因而哭喊了很久,低哑,但潮湿。
凯尔希说“我真不敢想象,我居然在跟你讨论你的新床/伴,而你因为他缺席了一次会议,却还有脸跟我说他的表现很好。”
她面无表情的翻开了博士给她的资料,这就是他们昨天会议上的内容,博士缺席之后,凯尔希把会议记录直接传输到了她的终端上,好让她在从床上爬起来之后完全她早该完成的工作。
而从博士给她的东西上来看,可露希尔的理论有一定道理。
凯尔希真不想承认博士乱七八糟的社交关系居然真的能提高工作效率,于是她说“你不想跟我说什幺吗?”
博士沉吟了一下“不要告诉孑监控录像的事,和我做/爱这件事已经很让他怀疑自己了,他不能再接受这件事被更多的人看到了。”
“……虽然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想得到什幺回答,但肯定不是这个,打开记录设备。”凯尔希扔下了档案卡。
博士把自己座位旁边的仪器打开,会议室突然昏暗下来,又逐渐升起蓝盈盈微光,她与凯尔希停下了那些与工作无关的交谈,开始专注于她们本该要做的事情。
艾雅法拉的情况进一步恶化了,她不能再出席接下来的战斗与研究,她们要重新规划,医疗部干员的执勤时间也要重新安排。伊芙利特的也不太稳定,她们要通知赫默;与龙门的谈判安排在下周,在此之前,博士需要和陈再协商一下……
从某种角度上而言,凯尔希确实应该表彰一下孑,如果让博士再维持着之前的那种状态来处理公务,她会发疯的。
所以当工作告一段落,博士开始收拾东西,准备去医疗部那边看看艾雅法拉的情况时,凯尔希终于对她露出了今天为止的第一个好脸色。
她说“下次滚去你的房间,我不想再和可露希尔一起整理办公室的监控记录了。”
博士“我尽量,但是你知道的,有一些干员更喜欢在那里。他们似乎觉得这样就可以混淆我们之间公事公办的态度,显得不那幺像一夜/情。而且,将这种行为公之于众多少有点宣誓主权的意味。”
凯尔希瞪了她半响,才用力的把人从自己房间推了出去。
但她们大概都没想到,第二天晚上站在博士房间里的,并不是孑。
“我觉得我们可以尝试一下,博士。”棘刺若无其事的说。
博士对着他手里提着的箱子,已经与手柄缠绕在一起的鞭子沉吟了一会。
“我没有拒绝的余地,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