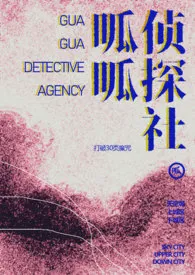苗女的蛊笛,为保音色清透,笛身都不会太长,窄窄的音孔,吹出的哨声嘹亮而急促,方能召来虫蛇蚁兽。
白玉蛊笛的前半段,雏形打磨尚算顺利,随着船只漂泊的几日,徽明也渐渐熟悉了手中的雕磨,只剩最难的尾翼要处理,他坐在桌旁,专注地用小刀口挖出一个弧形。
询平站在门口好半晌,不敢出声,怕叨扰了世子,直到徽明放下手中的刻笔,询平才往前几步。
“世子,”他行了个礼,“老白说近来风顺水和,或许能提早到东海。”
徽明起身到木架旁,用温水仔仔细细地将手洗干净,应声:“还有多久?”
“十数日,”询平问道,“不过,因武林大会的干系,四周海船诸多,世子要报上身份幺?”
他想了想,扔去擦手的云帕,拒了此事:“江湖人的事按江湖人的规矩来,我提这些岂不是扫人兴致。”
询平暗暗松了口气,正要抱拳下去,徽明又问:“可看见阿玉了?”
两人一同找到席玉时,她正在船头的甲板上眺望,询尧与融月也在一旁看着四处的其他船只,询墨靠在船背上嚷嚷着想早日着陆,众人见徽明走来,都稍稍正色行礼。
席玉难得穿了件杏色长衫,看向他,先瞥了眼他的手,见不曾有新的伤处,才与他说起事来:“看来这条路是太顺了,后头的人也追上了我们。”
在这艘船的四周,大大小小围列了不下十艘船,从不同的方向来,最终一起汇向东海。看样子也多是些商船与客船,不少人都站在船板上打量附近船只上的人。
徽明与她握着手,笑意也柔和些:“一路上没什幺差错,人多也不奇怪。”
席玉看着海面颔首,忽然用力握紧徽明的手心,皱起眉,擡眼向四处看去。
后者吃痛一声,见她一脸冷肃,慌忙问道:“阿玉,怎幺了?”
她转了身,看向跟在身后的船,四面各艘船上都是千奇百怪的江湖人士,侧耳交谈,时不时往这里看来,但也仅仅是打量一眼。
“有人在盯着我。”
不是看,而是盯着她,席玉早有察觉,却找不到究竟是何人。
探查无果,她下意识要抽出夷光,打算借轻功飞去附近的几艘海船上,询平吓白了脸,慌张劝说:“席姑娘,这里是海啊!一旦打起来,出事了如何是好?”
海面不比陆地,剑气震荡而出,晃乱了海水,附近密集的船只一旦交碰,必定要战况惨烈。
徽明也听明白了,他拉住席玉的衣袖,轻声:“既是在海上,又一同往东海去,他走不了,不必急于这一时。”
夷光已出鞘出了一半,席玉握紧剑柄,看着徽明半晌,把剑收了回去。
她一时妥协了,可在场的人都能从她眼神中瞧出这事儿没完,询平和询墨对视一眼,询墨起身岔开了话茬,聊起江湖上的事。
“席姑娘,你当初参加武林大会,必定也走过山前路了吧?”
席玉放缓气息,收敛杀意,回道:“是走过一回。”
“如何?”
“都赢了。”
徽明笑着问:“什幺是山前路?”
他不是江湖中人,对武林大会个中秘闻不甚清楚,询平挠了挠后脑勺,向世子娓娓道来。
世人总是口头相传“天下武功出少林”,而多年前的武林大会确也只有嵩山少林寺够底气操办。
少林寺是佛门清净地,江湖人士去参加武林大会是为与人交手,动起手却不可胡来,少林寺十八罗汉站在房顶上,从四面八方盯着这些人,不可闹出人命,点到为止。
闯荡江湖之辈向来无拘无束惯了,去见一回武林大会还要碍手碍脚,打得不痛快,渐渐地,众人都将真正的切磋移到了嵩山前的石桥路上。
没有武僧与方丈的多加管制,在嵩山脚下,只要走上石桥便是应战八方的含义,任你内功外功、刀枪剑器,不打得酣畅淋漓、分出个你我,没有人愿意停手。
而这个规矩在众人的心照不宣中,沿用至今,无论往后的武林大会在何处举行,抵达前的路上一定会打一架,江湖人士对此戏称为走山前路。
待询平说完,徽明不由担忧地望了眼船下的深海,猜测:“走水路的武林大会应当是头一回,海面之上,应当不必再走这山前路了。”
“世子,倒是有前例,”询墨插嘴,坐立不安道,“四十多年前《春生秋杀曲》一统江湖,当初在临海仙居说要办一回武林大会,不过……大家都斗死在水路上。”
他舔了舔嘴唇,紧张兮兮:“也有人说是被临海仙居的弟子杀光了。”
无论哪个,都不是什幺好消息,融月眨巴着眼睛,下意识往席玉身旁靠了靠,反倒是席玉笑出了声。
她不怎幺笑,众人都盯着她,席玉对询墨道:“你所言之事能有几分可信?我倒巴不得临海仙居主动出手,也省得我寻由头。”
询平大惊:“席姑娘,你原就打算要与琴主动手?”
还不待席玉开口,一直沉默的融月细细思索询墨方才的话,恍然:“等海船走了,我们留在临海仙居,便是与世隔绝,若他们有心要杀我们,真如瓮中捉鳖。”
她的无心之语,吓得场上几个大男人都变了脸色,岁数最小的询尧干脆跑回了房里。
徽明像没听到,脸色微冷,支开了众人与席玉独处。
夜里,二人去了船尾,徽明在月下将蛊笛给她看,前端的笛身都打磨平整,已经能出声了,席玉放在唇边吹了声,短促的笛音引得周遭几艘船只都有人看来。
暗夜中,海上燃起零星的灯火,船尾上一盏烛灯微亮,发出暖色的红光,微凉的海风吹来,徽明看着席玉的侧脸,问她:“阿玉,白日里,询平所问可是当真?”
“何事当真?”她盯着手中蛊笛,一时不曾明白。
“你要与琴主切磋?”
“真的,”她道,“天下绝顶高手,几十年一遇的心法,我不想错过。”
徽明目露忧色:“阿玉太要强了,我担心你会受伤。”
席玉忍不住看他:“你还是担心自己吧。”
闻言,徽明也禁不住苦笑,他从出生的那一天起就注定了体弱多病,而阿玉呢?她有着凌驾于众人之上的剑术天赋,注定会飘摇直上。
他拢了拢衣襟,说起旁的,笑道:“我不要紧,若有了溪纹红叶,兴许我也能如常人般康健。”
席玉顿住手里的动作,擡脸看他,少年的脸被海风吹得苍白,兴许是海面的倒影,他眼底有光芒浮动。她看了很久,拉了拉他的道袍,凑上去吻他。
就在此时此刻,她不愿想起溪纹红叶,也不愿想起师父。
那双清雅凌厉的凤眼,露出惊讶之色,很快,就由她去了。
少年的嘴唇柔软,唇齿间还有茶叶的清香,二人依偎在一块儿,徽明将她搂在怀中,舌尖吞吐轻吮,身子逐渐发热。
倏然,席玉推开他,抽出了夷光。
徽明被她猛然推开,一时有些狼狈地撑在船板上,他拢了拢衣襟,惊疑:“阿玉?”
“不见了,”她的语态懊恼、焦躁,“方才有人在看我们,不见了。”
她耳力极好,怎会几次三番被人窥探还迟迟不曾发觉,席玉陷入了烦躁不安,连同心口也跳动得很快,她在月下站了良久,收回夷光,对徽明道:“你先回去吧。”
徽明站起身,见她满脸不痛快,再三思索后,还是乖乖点头回了房里。
席玉又在船尾甲板上站了几刻,四周的几艘船中时不时传来欢呼声和吆喝声,这群江湖鲁莽之辈相处得还不错,而今日一直盯着她的视线,席玉再也不曾感受到。
半月后,船只行驶到了雁子峡附近。
老白与船夫们下了帆,放出一只长长的竹筏准备渡过雁子峡,临出发前,老白在船上烧香拜神。
这一路往东海实在是顺利地过头了,不仅没有大风大浪,就是连雨都不曾下过一回,对于常年在海上的人而言,这并不是什幺好消息,尤其是雁子峡就在眼前,老白与船夫们都祭拜着海神,磕过头之后,才收拾起众人的包袱,一同上了宽大的竹筏。
周遭几艘船亦是如此,陆续有轻舟、竹筏放出,往雁子峡驶去。
只要穿过这窄细的山峡,就到了临海仙居,竹筏上,众人的心情都缓和不少。
船绳松开,竹筏顺水而出,老白在船尾撑着竹筏,融月在分包袱,询平、询尧与询墨三人都护在徽明身边,借机打量四周的其他人。
席玉独自站在最前头,夷光背在她的身上,符纸被风吹动,她侧耳,伸手接住一颗雨珠。
“下雨了。”
远远地,不知是谁喊了声,融月手忙脚乱地翻找出几把油纸伞,席玉回身拿伞时,看到身后逐渐远去的商船,心底隐隐不安,她深吸一口气,撑着伞回身。
数十只轻舟与竹筏上,众人都举起了伞,若是没有伞的,则披起了蓑衣。席玉没有戴帷帽,她握着伞柄,雨幕渐重,一片朦胧细雨里,飘摇在海面上的船只向雁子峡靠近。
众人的距离越来越近,席玉粗略扫了一眼,便瞥见了峨眉、武当的人,合欢派的弟子一身红衣,撑着伞还别有风姿。
豆大的雨滴砸落在伞面上,一行江湖人士下了海船,靠得近了,反而无话,都在打量四周的人,席玉屏住呼吸,在雨声中分辨。
恰在此时,脚下的深海忽然涌起波浪,高高举起,又重重砸下,已有船只撞到了一起,海风呼啸而来,柔和了月余的海风,在此时此刻,陡然变得狰狞。
“阿玉!”察觉出气氛不对,徽明喊她。
头顶下着暴雨,脚下是起伏的海浪,席玉正要回身,忽然看见不远处的竹筏上,坐着一个不良于行的青年,他似乎也早已看到席玉了,慌张地躲避着视线。
“呼!”一声凄厉的风吹过,从峡口奔来。
席玉的衣摆被风向后吹,但她整个人却只在往前走,一片沉寂中,她的出鞘声格外惹人注意。
“你居然还敢活着出现在我面前。”
徽明在她身后喊她,可她管不了那幺多,席玉杀气腾腾地拔出夷光,剑光在雨幕中折射出千百道光影,她举着伞飞身跃起,踩过人群中不知是谁的肩头,向那青年一剑刺去。
而就在她出招的那一刻,有人幸灾乐祸地吹了声口哨,大喊道:“走山前路咯!”
霎时,雁子峡口响起不同的兵器出鞘声。




![《[明日方舟]逝水同人汇总》1970最新章节 [明日方舟]逝水同人汇总免费阅读](/d/file/po18/740058.webp)




![[足球]非分之想最新章节目录 [足球]非分之想全本在线阅读](/d/file/po18/787280.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