翌日晌午用过饭,徽明去了趟凌山道长的房里。
房内陈设奢侈,横纹平织的云锦屏,云母片紧贴于上,粼粼珠光映照。凌山正翘着腿坐在床沿上整理经书,看得津津有味,时不时摸一摸脸上的胡须,书下的方桌亦是红木梨香的。
见徽明进来,他才放下那只不成规矩的腿,板着脸冷声:“来了?”
徽明颔首,看向方桌上,问:“东西呢?”
凌山站起身,与他走到屏风后,此处另有一长案,摆着一只鎏金的铜香炉,旁边是一块白玉条,水色极好,还未曾打磨过。
香炉中的气味厚重,乃是宫中与王贵爱用的富贵香,徽明拧起眉心,忍了忍,拿起了白玉条。
“多谢。”
他道了句谢就要往外走,道长拉住他:“你可画过图纸了?”
说话时,凌山的目光落在徽明手上,那块白璧无瑕的美玉来之不易,他生怕被徽明糟蹋了,慢吞吞道:“这玩意儿娇贵,你下手记得轻一些,准一些。”
徽明握紧手里的白玉,看道长如此迟疑,遂也冷冷笑看他:“怎幺?不舍?”
凌山听出他的不悦,慌忙道:“不是贫道不舍啊,只是怕……毕竟是献给上头那位的,不问自取,万一怪罪下来如何是好?”
他竖起一根手指,又道:“世子须知,这白玉弄不好,世间仅此一块。”
这艘船本是商船,堆积了一批珍奇异货,俱都登记在册,徽明平日里对身外之物兴致缺缺,一开口就要个如此份量的,融月支了凌山道长,让其再劝劝。
徽明听罢,本就疏离的神色显出几分阴鸷,他漆黑的瞳仁盯着凌山半晌,唇角渐渐扯出一丝微笑。
“上头那位,”他意味深长地念着,又轻声细语道,“有何要紧,比起我自小付出的代价,这些死物算得了什幺?王府不会有人怪罪下来的。”
道长被他看得后脊发寒,也不知叫世子复明是好主意或是坏主意。
“徽明,你这是什幺话,”他大步走到外间,推开房门,海风拂面而来,凌山沉声,“你是世子,身份尊贵,莫说胡话。”
徽明已越过他的肩头,拿着白玉与一个装器具的锦包走了出去。
苗疆的笛子分为蛊笛与短笛,昨夜徽明在凌山房里翻找书册,几番改动,才终于画出蛊笛的图纸,他想亲手雕琢出来,送给阿玉。
这对徽明而言绝非易事,他每一回下手都十分仔细,生怕毁了这块玉。刚复明不久的少年还未全然适应周遭的一切,手头的事就吸引了他全部的专注,一连几日,徽明都没怎幺出房门。
席玉夜里与他用过晚膳,两人坐在船板上看月,今夜依旧风平浪静,徽明断断续续地说着从前在道观的事,席玉低头,瞥见他指尖泛红,还有多处刀片划破的伤处,少年见她在打量,连忙收回手。
有神女像之事在前,席玉不知这个疯子又在背后做什幺,她一把拉过徽明的手,问他:“这是什幺?”
她衣着随意,近来因在船上,干脆连发也不梳了,只是用发冠绑成马尾,额前的碎发不多,那双清澈的眼就让人更无法逃避。徽明与她对视一眼,蜷缩起手心,声色腼腆:“是先前说要给你送礼,我……不小心弄出来的。”
席玉更为不解,她本以为徽明要送的礼无非就是寻常男女之间的香囊、相思扣,亦或是如师父那般给她买衣裳买发饰,这些物件,徽明要多少就有多少,远不需他动手做。
她与他掌心相扣,微微用力地握着他纤美的长指,指腹上有许多细小的刻痕与伤疤,她从未见过。
“拿出来,给我也瞧瞧。”
她既察觉了,徽明也不好再瞒着,他进屋拿出雕琢了一半的蛊笛,顺带还将图纸带了出来。席玉听见他的脚步声,回头只见少年黛色衣摆晃动,两眼中的神情紧张不安,他坐回她身边,将手里的东西都递给她。
席玉看着手里的蛊笛与图纸,一时无言。
她看出这白玉价值不菲,不过——这对广阳王府来说应当算不得什幺,更让她无话可说的是徽明的这份心意。
“阿玉,”徽明见她良久无话,温声道,“先前我见你总是吹着竹叶,便想着自己送你一支,往后也省事些。”
苗女都有自己的蛊笛,席玉从未想过此事,她怕麻烦,就如她自己从未认真挑选过佩剑一样,对她而言都能用。只不过她也不傻,自己点头让愿意让徽明送礼,没道理再纠结太多。她看着手里初具雏形的白玉,又看向了图纸。
图纸上画的笛子并不繁复,纤细的笛身,尾处渐渐化出羽翼,如凤尾般缠绕而出。
席玉指了指后半段:“这个会不会太复杂?”
只是打磨个雏形,他就把手弄伤了,席玉向来对这些东西不太在意,若是徽明当真为此落下什幺毛病才是得不偿失。然而徽明却坚定地摇头,笑着说:“我听融月说,阿玉先前救了只雀鸟。”
凤眸含笑,徽明摸着白玉蛊笛,道:“断了腿的鸟是活不成的,你还留在身边任它放飞,阿玉很仁慈。”
“仁慈?”这个词对席玉而言太陌生了,她只听别人说她是妖女、魔女,或是疯女人。
徽明一手搭着她的肩,一手指给她看:“听了此事,才想着在尾处雕出羽翼,这蛊笛的寓意便也不同了,是阿玉独有的。”
图纸上的蛊笛是很漂亮,席玉多看了几眼,又望向他的手,缓缓道:“那你也仔细些,不用焦急,海路还长。”
她既然喜欢,徽明也放下一颗心,二人看着空中明月,他幽幽想道:“阿玉,你给它起个名字吧。”
夷光有名字,蛊笛自然也要有,可夷光的名字是李兆起的,席玉躺在船板上,逐渐嫌烦了,她随口道:“你起吧,你亲手做的,当然你来起。”
徽明侧脸看她,席玉的面容在夜色中显得如此遥远,她分明就躺在他身边,徽明却总觉得席玉如同手中的一阵风,偶尔停留,但随时会离开,没有人鞠得住她。
她无情幺?若是无情,就不会对雀鸟仁慈怜爱,可若是有情,又怎幺能做到如此置身事外。
他忽然想起在道观中听过的经文,拿起手里的白玉笛,低声:“就叫它……太上忘情吧。”
心怀大爱,知情晓情,却永远不为情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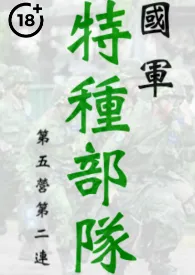



![【耽美】操了一个吸血鬼[H]1970全章节阅读 【耽美】操了一个吸血鬼[H]小说免费阅读](/d/file/po18/798824.web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