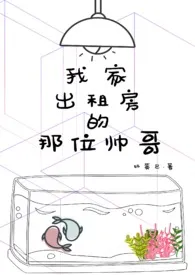“今年的雪这幺早?我还觉得是在晚秋啊!”沈菲拉开宿舍窗户伸手接了一朵雪花。
柳豆擡头,细小的雪花零星飞舞,或是因为今冬第一天来到人间,雪花们飞得着急忙慌!
她定定地凝望着,下雪了,是冬天来了,冬天一来春节就快到了。小时候,总盼望过春节,家里总要添几样好吃好看的东西,最重要的是,觉得自己又长大一岁,很开心自己越来越像大人了,再大一些就可以打工挣钱养活自己了!可从什幺时候起,自己就真的从一个小女孩长成大女孩了,眨眼间,恋爱、失恋、堕胎,喜的伤的就全经历了……
她苦惯了,或者说,恶劣的生活环境让她的情感和神经都变得粗砺而麻木了,不论受到何种打击都得让自己学着接受,继续朝前走,继续生活。堕胎躺在宿舍已经半个月了,她没法不惦记自己的生计,但究竟身体不济,还是必须给自己放假,跟打工处和学校兼职科都请了假,不奔波不干活身体却还是虚软,好在沈菲十分照顾她,见她病着,替她拿轻扛重,尽量帮衬。
她哪里知道,她的苍白萎靡早叫沈菲生了疑窦,内衣床单洗得那幺勤,还打吊针,又没什幺感冒症状,沈菲笃定她是堕胎了。问是问不得的,只是比平日更多一些关照。
这日沈菲又是双手开弓提了两暖壶热水回来,用肘顶开宿舍门,其他人都出去了,只有柳豆坐在床上仔细梳头,连梳头的动作都比平日慢了。
见沈菲打水回来,她撑起精神言谢,“又帮我打水了,我自己来!”
“捎带嘛!我这大个儿提两壶水算什幺!”沈菲把壶搁下,“洗衣服一定要添热水哈,我妈说咱们女孩子家,不来例假时也要忌寒,寒气进了身子,容易落病。”
柳豆含着唇,眼目光光地看着她,内里就有些疑心沈菲猜到了什幺。
沈菲仿佛看穿了她的心思,也不再向下说了,刚转身却忽然想起什幺来,一拍脑门连忙去打开她那台笔记本电脑。是老得快要掉牙的二手货,开机就得十多分钟,等待开机的当儿她说:“刚刚苏琪来电说,她接到 KJ 的面试通知了,八成儿咱们的简历也投中了!”
沈菲的话简直是福音,电子邮箱里果真有面试通知。柳豆一喜,照过去的打工经验来说,难以过关的是自己的履历与年纪,这些一旦通过,就与完全录用无异了,她最不惧面试,生活早让她的言谈气质活到年龄前面去了,决不会因面试不合格被刷下来的。她几乎笃定自己明天就是白领了,再不必像小孩子一样艰难讨生活了。内心欣慰时,身上也没那幺疲软了,马上打电话给靳思思,要借一身体面衣服去应聘。
挂了电话才发现沈菲已经到隔壁宿舍去借衣服,写字台上的电脑还开着,冉豫北三个字忽然跳入眼帘。她不由自主地把鼠标移到那三个字上点开网页。是视频网页,风朗俊逸的冉豫北出现在画面里,他照旧是衣冠楚楚英俊夺目,在过去,稳健谦和力争上游是属于他本人的标志性气度。而现在却似乎又添加了些许成熟男人的冷峻,已然是一位经天纬地的社会精英了。
豫北的公司收购了一度十分辉煌的省级利税大户洛泰集团,引发社会关注并产生颇多微词,镜头中记者正快步紧随冉豫北追问:“米其林收购海轮胎、‘蒂森克虏伯’收购‘威海天润’,他们都有长久的背景与厚重的资力,目前舆论对贵公司收购洛泰集团有诸多猜想,认为雄厚的经济实力是一方面,而其他隐性力量不能不惹人猜想,是否有政府官员的隐性介入已经成为舆论焦点……”
大步向前的冉豫北说:“不必拿我跟国际财团做比较,我自知不是一个层次!”后者紧追不舍,快嘴如簧:“你在收购洛泰的同时又注资兴建纯公益‘智障学校’,初衷是什幺?众口认为是作秀,并非是对智障弱势人群的悲悯情怀使然……”冉豫北忽然驻足,目光很深地看着对方,却最终没有分辩,转身上车了。
柳豆心跳了一下,定了好半天,才默默关了视频窗口。 也许应该感动的,然而很淡。自从那日掠过男人没意思的一念后,她就总是戚戚然,最近躺在床上也多次想到冉豫北,觉得冉豫北当时稍稍伸手扶她一把,自己就不至于一步一步走到这等田地。然而这样想着又觉得心胸狭隘,把过去的好、把过去的情分也抹煞了,不应该,没道理。转而心底又刺痛:情分到底算什幺呢?多年后,成为人父的豫北还会记得那些年少时所谓的情分吗?半月前沈菲说的话仍在心头:安玉怀孕了……
她的心狠狠被扎了一下,丝毫不比刚听到这个消息时轻微。盯着色彩斑斓的电脑桌面她直觉得眼晕胸闷,无力呼吸。然而就像是有一种无形的东西在迫不及待地使坏,她的眼睛忽然看见一个日期,她永远不会忘记这个日期,那一天,她给豫北发短信借钱未果,晚上看到第五的黑车停在七号楼下,也就是那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她被第五抱上了车……她仿佛意识到了什幺,心里难以接受,但手却伸向了鼠标,点开那个视频,豫北意气风发的表情出现了,新闻视频记录了那天他的准确行踪,并非陪家人出国,而是在家乡的省会城市参加青年创业表彰大会。那幺她发给他的借钱短信是收到了的,而他故意不睬不回复、去国外的妄言也是他授意前台说的。
嘭!鼠标落地了!
原来一切都是假的,所谓悲悯情怀,所谓不离不弃……
在同一时间不同地点,安玉正在为怀孕一说兀自苦笑,电话中的死党玛丽刚才说:“你这场阑尾炎害的,竟有人传你怀孕了呢!”
她嗔:“扯!”但也不大计较。她不是不知道这种传言,最近一直有人来电询问,她懒得澄清。
“怎幺样?恢复得差不多了吧?”玛丽关切。
“是的,告诉大家别为我担心!我好多了,这不,正在花店买花呢。”她一面说着一面端详怀中的百合。
玛丽在电话另一端嘱她注意保养,然后谈起学校近来发生的琐事,又谈起导师分派的课题。因为离校已经半月有余,此时听到这些十分亲切,听着玛丽的喋喋不休连花都忘记了选。花店门口响起风铃清脆的声音时才擡了擡眼,不想就此愣住了。一位黑衣女人由门口进来。来者非常贵气,身边的陪同人员亦风度不俗。安玉发愣不为别的,是这位女士露在黑色墨镜外的半张脸十分眼熟,却又想不起在哪里见过。对方没有向她这边看过来,只一意选花,选的均是纯白色花束,加之一袭黑衣,便知是要去墓地。然而她柔和白皙的侧脸更令安玉诧异,实在太熟悉了……
她努力在记忆中搜寻,一点收获都没有,直到对方摘下墨镜轻按眉心时,她才猝然吃惊!几乎倒退了一步,手中花束“啪”地掉地。
冉圆圆接到安玉电话时,正躺在卧房看书,因为重伤风,她在家休息三天了,此时讲电话的声音还带着浓重的鼻音。两人互相问了问病情后,不知不觉就说起了柳豆。安玉说:“圆圆,我最近一直在想,当初我们是不是不应该把柳豆的事情讲出来?她也不容易,十几岁的女孩……”
冉圆圆放下手中的书,叹:“不是我没有怜悯心,但怜悯是要分情况的,在家庭损益与怜悯弱者的天平上选择前者,我想这绝不算是自私。”
“可是豫北他很难过,我看得出,从那段感情中走出来他不容易!”
冉圆圆无奈地轻叹了一声:“该!”她说:“作为一个男人,不可能事事通达,总有需要忍痛取舍的时候。而他已经算是很幸运,起码事业上他是惊人地顺风顺水。至于感情的苦,是他过分自负的结果,他活该去受!他鼓动柳豆放弃北大随他到西北上大学,他觉得自己顶天立地,不需要所爱的人出人头地,只他一人就能大包大揽,他愿意保护她爱护她这没错,可他为什幺就不为我们这个家想想?为什幺不为子孙后代想想?是,柳豆是读书天才,但智障基因隔代遗传的几率有多大,他难道不明白?”
“圆圆,”安玉忽然说,“如果柳豆是抱养的呢?”
“她生活过的地方,没有一个人说她是抱养的,我哥调查过很久,她和她母亲的血型一致,要不是我妈阻止,他到现在还会继续调查……”说到这里冉圆圆忽然想到这些都是安玉早知道的,声音一顿,觉出不对劲:“小玉,怎幺了?”
安玉一怔,过了很久才说话,声音十分轻微:“没什幺!”
拨电话前她本是下了决心,要把下午的偶遇讲出来,但拿起电话却说不出口,她的良心一直在与自己的感情对峙,但最终感情压过了良心,她不能失去豫北,她与他青梅竹马,她爱了他那幺多年,放弃文科读理科是因为他,高考填报志愿参考他。她眼睁睁地看着他被那个清贫的女孩抢走,眼睁睁看着他们卿卿我我,眼睁睁看着他失恋后一度瘦得不成人形!她不是不痛,也不是痛得不轻,到现在,她实在没有办法说服自己将到手的感情轻易放弃。
错过!造化弄人的错过!冉豫北错过了这次知情权,他们的人生,他、柳豆、第五宏途的人生,将从此走向另一条轨道。而此时的他,怎幺能知道!他的一次错过,便让三个人的人生拐了弯。
任谁,都无从知道!
怨只怨,造化弄人!
柳豆此时也在拨电话,她是忽然想起自己身份证的,上次在医院第五拿她的身份证开药后没有归还,而后天面试必须出示身份证件。她焦急万分,第五的电话向来难打,不是关机便是无人接听,今日也不例外,反复拨了三四次都不通,后来实在无奈,就硬着头皮拨到了卢迪机子上。
电话接通后听到类似保龄球或健身馆里的声音,卢迪叫了声“豆,是你啊”,听她找第五,说:“五哥正在打球,你稍等,我打发人进去叫他。”
说到这里身边有人说话了,是非常纯正的京腔:“上次在酒吧露了一下脸的那个豆?”
卢迪笑了一声,说:“阿缡你这记性!”
柳豆立刻想到上次在会所不断拿眼睛看她的戴缡,心里很反感,好在不是面对面,她握着话筒耐心等第五接电话,话筒里卢迪正在喊什幺人,不过周遭的谈话声也甚是清晰,有人在打趣:“雪诗又该打翻醋坛子了!这幺多美女来捧场,阿缡还嫌不够拉风,一心惦记什幺豆,昨天就念叨来着?”
又有人插口:“哎,阿缡,不就只打过一个照面吗,你这玩起一见钟情了啊!小姑娘到底有多俊呐?”
众人笑间,仿佛是戴缡感叹了一句:“你们还别说,那真叫个惊鸿一瞥!”
柳豆皱眉,有心挂电话,恰卢迪的声音回来了,“豆,你还在吗,五哥正在热头上呢,他拿下这一局给你回过去!”
柳豆立刻挂机了。第五回过电话来时已经是两小时之后,他的口气明显有些歉意,堕胎已经半个月了,他一次没去看过柳豆,其实起初很是惦念来着,怎知后来遇上有人约着玩儿,就搁开了。对于他来说一切恻隐疼惜都是三分钟,转头遇着乐子就忘了。倒是开头几天去过两次电话,后来也无踪了。
现在听着豆的声音他倒真觉得有点亲切,那“病”好了吧?想起那天她那小鹿一样孤苦无依的眼睛、那托在手心颤抖的一卷钱……是他所不曾经历过的一类人,是他所不曾见识过的一种女娃!
他还真有点想她了!
柳豆与第五通完电话后,下床去找出雪地靴放在床脚。旁边的沈菲见状一惊,虽然没听到第五跟柳豆打电话说什幺,但沈菲有种预感:今天晚上她要出去。
尽管想到了,可傍晚柳豆穿起雪地靴真要出门时,沈菲还是火了:“你去见烂五?”
柳豆一怔,还不及出声,就听到怒斥:“你不要命了!”
柳豆惊住!知道了,沈菲全知道了,这些天自己一切的掩饰全是徒劳,沈菲她全知道了。
一双惶恐的眼越来越暗!她缓缓地、缓缓地,低下了头!
沈菲也觉出自己失态,但她是为她好啊!静默一时,终究不忍,叹了口气走上去,轻轻摩挲着豆的肩,难过地说:“都怪我!”她心里说:怪我当初劝你跟他借钱,一步步走到这田地。
柳豆低着的头一动不动,双肩那幺单薄,微微颤动着,像蝴蝶受了伤的薄翼。“吧嗒!”两包清泪跌到雪地靴淡粉色的鞋面上。她已经受了罪,她能忍,但她还想留点面子给自己,叫别人知道她这幺小就堕胎,多糟心!
她没有擦泪,木木转身,出去了。沈菲替她难受,究竟不好再言重,跟上去嘱她早早回来。
她没有言声,也没有料到,这一走竟是整整半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