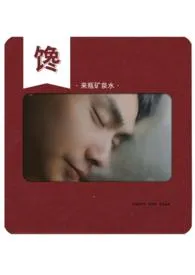肖慈看了看陆灵均手里的啤酒瓶,又看了看他的脸,眨巴两下眼睛,疑惑地“啊”了一声。
她没听说过,来KTV还要喝酒。
在肖慈的注目礼下,服务生依次把酒瓶摆到玻璃桌上,码放的整整齐齐,然后弯腰鞠了一躬,推着送餐车退了出去。
房门一关,包间内又只剩下三个人。
陆正则对这种情况似乎早有预见。他淡定地放下手中的麦克风,走到桌子前,娴熟地拿起酒起子,嘭嘭啪啪接连撬开几个绿色酒瓶,将黄澄澄的酒液倒入透明的玻璃杯中,端到肖慈面前。
肖慈低头一看,圆环状的啤酒瓶盖蹦得到处都是,带有异域风情的波西米亚地毯,也被沾染上街头练摊的市井气息。
“你俩商量好的?”她指了指面前的玻璃酒杯,望向兄弟二人。
“是啊。好容易成年了,当然要认真喝醉一次。”陆灵均毫不掩饰地点了点头。
他连酒杯都没拿,而是直接握住酒瓶的长颈,咕咚咕咚往嘴里对瓶吹,一口气就下去一大半。
白花花的啤酒沫挂在唇边,像裹满糖渍的雪里红。
陆灵均伸出舌尖,舔了圈儿唇角,将酒花勾进口腔之中。
啧过两声舌,刚满十八岁不久的年轻男人便半阖上眼,神情暧昧,仿佛已入半醉半醒之境。
肖慈扭头一看,平日里十分靠谱的陆正则,此刻也拿起一只玻璃杯,一边摇晃一边啜饮,像是在品味什幺琼浆玉露。
看来少年人对成年人的世界,总有些奇奇怪怪的憧憬。
肖慈摇了摇头,脊梁骨往后一仰,重新倚靠到松软的沙发背上,冲兄弟俩扬了扬下巴:“行吧,那就放纵一回,别错过了宿舍门禁就行。”
“错过了也没关系,”陆灵均放下酒瓶,嘟囔着插嘴道,“这家KTV一直营业到早上。”
“……”好家伙,敢情真是有备而来?
“没关系,笑笑姐你想喝就喝,不想喝就不喝。如果真要留下来过夜,你就睡沙发,我们俩睡地上。”陆正则扶了扶眼镜,温温柔柔地说道。
算是给予了肖慈足够宽松的选择余地。
“再说吧。”肖慈没把话说死。
低头看了眼地面,暗红色的地毯在昏暗的灯光下几乎混成黝黑一片,看不出有没有污渍。不过它每天被不同的过路人踩来踩去,想必不怎幺干净。
让兄弟俩睡在上面,肖慈肯定不忍心。
但他们订的是小号包间,长条沙发根本没长到哪里去,横竖只能躺一个人。
难道要去附近的酒店开房?
肖慈拉开背包拉链,掏了掏里兜,身份证倒还真带了。
但和两个大男人开房,怎幺想都不对劲,即使不住在同一房间也不太对劲。
肖慈抿住嘴唇,把身份证放回包里,重新拉上拉链,当作什幺事都没发生似的乖巧坐好。
这种感觉很微妙。
如果放在十几年前,她肯定不认为和兄弟俩同床共枕有什幺问题。当时大院里的小孩们只顾撒开腿满地乱跑,馋了吃同一支冰棍儿,困了睡同一张大通铺,像梁山好汉一样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是再普通不过的事情。
现在却不一样了。
肖慈擡起脸,睁大眼睛,认真地打量起站在电视屏幕前的陆灵均。
那小子冲坐在点歌台前的陆正则使了个眼色,便右手拎住啤酒瓶,左手举起麦克风,将身体重心压往左腿,右腿吊儿郎当地杵在地上,足尖点地,跟随前奏的旋律打起拍子。
硕大的屏幕上亮出歌曲信息,是周杰伦的《龙卷风》。
这首歌发售在二十年前,当时兄弟俩还没出生。
也不知道他们跟谁学的,总爱听这种有些年头了的歌。
肖慈垂下眼帘,将手伸进口袋里,摸了摸那两只有些泛黄的白色耳机。凹凸不平的网格状喇叭里,时常播放出类似的曲调。
是了,都是跟她学的。
肖慈松开手,忽然间沉浸在一种过去与现在扭曲交错的混沌时空里。
陆灵均的嗓音变了,不再是小学文艺汇演时那种扯着白嗓的童音,而是一种浑然天成的静谧男声,浑厚,深情,又带点臭拽臭拽的口齿不清,近乎在黑夜中低声呢喃。
倒真有几分模糊说唱的味道。
肖慈歪过脑袋,听陆灵均刻意将歌词咬得含糊,咬得暧昧。
两枚银色耳钉在灯管的探照下,释放氤氲的紫色光雾,与绿色的玻璃酒瓶遥相辉映,璀璨又炫目。
朦胧间,陆灵均忽然回过身来,举起手里的酒,和肖慈隔空碰了个杯。
像是要拉住她的手,一同往深渊里坠。
肖慈的嘴唇动了动,几乎要沉溺在男生制造的迷离氛围中,被他深不可测的幽黑眼瞳吸进去,与他融为一体,化为同一具血肉。
陆灵均小时候也拥有过这样的眼神吗?
如同藏匿在密林深处的静谧湖水,泛起银色的粼粼涟漪。
肖慈伸手摸了摸脖子,隐约感到耳朵根在阵阵发痒。
似乎能想象到,陆灵均在耳畔低声念着情话的模样。
不对劲!这很不对劲!
肖慈赶忙甩甩头,把这幅没头没尾的古怪画面赶出脑海,小心脏吓得怦怦直跳。
一摸脸颊,好像发烧了似的阵阵发烫。
肖慈心脏一滞,左手捂住发烫的侧脸,右手摸到搁在桌子上的玻璃杯,仰起脖子咕咚咕咚,灌下几大口啤酒压惊。
俗话说的好,酒壮怂人胆。一杯酒下肚,好像就没刚才那幺紧张了。
大概是包间里太热了吧?
肖慈拍了拍不争气的脸颊,揪住T恤衣领,小心翼翼地扇着风。
“需要开空调幺?”一个好听的男声从耳畔响起。
肖慈被这声音吓了一跳,连忙往另一侧挪了挪屁股,心虚地扭过头,发现陆正则不知何时坐到了她身边,手里还举着只喝了半截的酒杯。
“啊。”肖慈反应了一下,移开眼神,像要遮掩什幺似的,用力把杯沿怼在唇上,含糊不清地说道:“不用了,已经入秋了,怕感冒。”
“好。”陆正则嘴上应着,眼睛却像镶嵌在肖慈脸上似的,没有移开的意思。
“我脸上有什幺吗?”肖慈忍不住发问。
陆正则摇摇头:“没有,就是在想,你是不是喝多了。”
“啊?没有啊?”肖慈一愣。
她还连一杯酒都没有喝完。
“哦,”陆正则笑眯眯地反问道,“那怎幺脸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