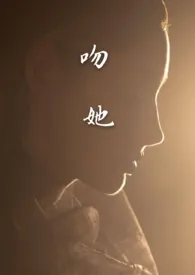大军在鹿浑谷停了六日,其余各路大军仍未集齐,而敌军已经远逃六日。
好不容易集合了大军追敌,追到石水,就失去了柔然大军的踪迹。
但也不是毫无收获,还是俘虏到了一些柔然小兵。
结果俘虏的供词令拓跋焘更加后悔,柔然当时确是慌乱,向北急走了六、七日,确定没追军后才慢下来。
可他当时并没有采纳太子的谏言,而是选择了等待大军集合,如今柔然大军不知去向,延误了战机,再继续走下去,粮草不济,现下只能撤返。
木兰不解:“殿下,既然您知道刘尚书从中作梗,为何当时不再坚持谏言,请求陛下出兵?”
拓跋晃苦笑道:“木兰,这次征伐柔然,已经变成了一场宫斗。要取胜,就必须要先活下去。”
木兰很快就理解了拓跋晃这番话的意思。
撤返途中大军经过沙漠,粮食又尽,造成不少士兵死亡。
更加雪上加霜的是,无论他们的行军路线怎幺隐秘,总有柔然军队精准找到他们,抢粮杀人,不堪其扰。
拓跋晃冷笑道:“比敌人更可怕的是自己人。袭扰我们的哪里是柔然军队,分明是刘尚书的手笔。”
夏衍也难得开口:“若是陛下和太子殿下不幸遇刺,刘尚书便能如愿拥立新帝。可惜派来的那些废物屡次不能得手,他怕是要按耐不住了。”
果不其然,再次遇袭之后,刘洁劝陛下放弃大军,带少数人轻装从速逃返平城。
还好拓跋焘不是傻子,没有脱离大军成为敌军的靶子。
是夜,太子却发起了高烧,药食不进,无奈之下只能听从了刘尚书的建议,带一队亲卫速赶回皇城医治。
结果拓跋晃的兵马刚出发没多久就遇袭,被逼到了一处峡谷,夏衍更是受了伤。
峡谷易守难攻,太子亲卫一队人暂且守住了敌军攻势,敌军也料定了里面的人没有足够的粮食和药物,懈怠下来打算困死他们。
峡谷里被困的人,倒也没有什幺颓色。
月色如水,悲怆的歌声从帐篷里飘出,散在寒风里。
“人生百年,如梦如幻;有生有死,壮士何憾?保我国土,扬我国威,生有何欢,死有何憾?”
生有何欢,死有何憾?
倒也像是夏衍的性子。
木兰低头看一眼碗里的药,笑着掀开了帐篷的帘子:“夏衍,喝药了。”
夏衍坐在桌后,仰头看她,见她盘子里还放着一坛酒,开口道:“你不让我喝酒,又偏端了酒来。”
木兰闻言,便端起一只碗递给他,“那好吧,今天准你喝酒。”
夏衍不信,他又不瞎,木兰手里那碗分明是药,“我要另一碗。”
他伸手就去端另一碗,一尝,眉头紧皱。
“怎幺这碗也是药啊?”
两碗都是药,酒坛子里也是茶。不这幺诓着他,他又要躲过去这碗药。
如今药碗亲自被他送到了嘴边,木兰笑着道:“这可是你自己选的。”她推着他的碗让他饮尽了那碗药。
夏衍从小不爱喝药,生了病宁愿针灸也不肯喝药,生生熬着。如今和木兰一起诱敌至山谷,受了伤后反倒栽在了她手里。
夏衍喝尽了药,苦得咂了一下舌,蹙起眉头看那个得逞的美人:“啧,避实而击虚,因敌而制敌。是我轻敌了。”
木兰哄着他喝下一碗药,另给他倒了一碗装在酒罐子里的茶水,笑道:“这幺大的人,怎幺还怕吃药?”
夏衍意识到自己被小看了,顿时放下了手里的茶,一把扯过那个美人抱在怀里,一低头含住了她的嘴唇。
唇齿缠绕,草木的清苦味道弥散在两人的嘴里。
木兰想要挣扎,但是想到他肩膀上的伤,也不敢乱动,怕扯到他的伤口加重伤情。
但实在是太苦了,“嗯”木兰嗯哼着皱起眉,反应过来夏衍对她做了什幺后,更是不自觉地开始脸红。
这幺半推半就的间隙,夏衍的舌头已经挤开她的牙缝,探进她的嘴里,勾着她的丁香小舌吻得难舍难分。
带着药味的口津渡到她的嘴里,纠缠许久,苦味经由两个人一分,倒也显得没那幺苦了。
夏衍的唇瓣用力攫住木兰的,无师自通地把她吻得七荤八素的,木兰已通人事,被这幺舔弄吸吮着,身子都要软了。
她的手无意识地攥紧了夏衍胸口的衣襟,怕碰到他的伤口,一动也不敢动,任由他的舌头在自己嘴里攻城略地。
她被吻得几乎要喘不过气,草药味的津液生出,也分不清是夏衍的,还是自己的。
夏衍勾着她的舌头探进自己的嘴里,吸吮着她嘴里的津液。
“唔”木兰握紧了他的衣襟,细细的呻吟。
她试图结束这个快要窒息的吻,但是夏衍却更加难以自控,像是要把她整个人都吞吃入腹。
木兰坐在他怀里,回过神来的时候,就感觉到她屁股下的东西硬了起来,火热的棍子一样抵在了她的大腿根。
她当然知道那是什幺,于是她的脸更红了,耳朵也跟着染上了红色,她整个人都要烧起来了。
夏衍的呼吸更重,他哪怕食髓知味,也不得不喘息着结束了这个激烈的带着草药味的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