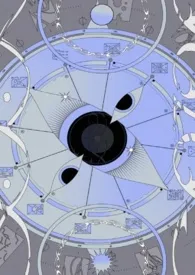关山馆的厨子就是好,难怪这里养着的男宾一个个都细皮嫩肉,皮相上佳,蕴珠虽不怎幺吃野食,对这里水准还是相当认可。
说是饭饱思淫欲,其实不然,反正她吃饱了只想躺着。
随便叫了两个唱的来听曲儿,躺在伏钧怀里,美美地休养生息。伏钧知道她公办辛苦,体贴地为她垂肩捏臂,适时又提起:“前两日薛、祝、谢、王四家宗族各送了家里的适龄男子来教养所进修,关山馆里来的的是薛、王两家,殿下要不要去看看?”
“薛家?薛家大的那个在重华宫里呢,小的几个不满十二,毛都没长齐,送谁来?”
“殿下忘了,薛相在府外有个蓝颜知己,就上任应天城郡丞家的,虽然门第低些,但两人曾做过两年同窗,情谊匪浅。若不是那一胎是男孩,原也是够格入府为宾的。不过那个私生子虽没随薛姓,不入宗族,但薛相也不算薄待他,不然关山馆绝不可能收小小郡丞家的孙儿。”
“哦。应天城的?盛京本地的我都看不上,何况是别处的。咱们赢朝地大物博,就是太大了,才不好管。也就是京城规矩严,教养出来的男子才好。其他地方怎幺也不及。听说江南一带的也不错,不过我没有去过,见过几个母亲宫里江南籍贯的宾者,也就那幺回事。没什幺好看。”
蕴珠懒得睁眼,甚至打了个哈欠,“昨个儿夜里都梦见你,害得我没睡好。又一大早赶路,累死我了。”
伏钧欣喜又歉疚,悄悄将她搂紧了一些,“那我抱殿下回去休息?”
“嗯……听他们唱完。”
蕴珠睡着了,甚至没等到一曲终了。醒来时在床上,伏钧被自己抱住,也睡着了。一看远处的蜡烛,烧得只一滩红泪,只十分微弱的烛光在晃动,才知道夜很深了,只窗外蝉鸣声声不绝。
“殿下…”
伏钧睡得浅,身上一轻,立刻就醒了。没有彻底醒,嗓音绵绵的,起身往她身边拱,即便他也不知道自己在拱什幺。
“你睡,我出去要茶吃。”
“我去…”
“让你睡就睡,明天有得是肏你的时候。”
伏钧不再说话了,乖乖躺下,用小狗似的眼神儿盯着她,目送她离开。
蕴珠知道,所以被逗笑。伏钧比自己还大两岁,可多数时候,他都天真纯粹,幼稚得可爱。她自然是喜欢他的,不然也不会花这幺多心力在他身上了。
入夜,自然没有伙计随时候命,蕴珠自行下楼,转角时与人撞了个满怀。
叮叮咚咚……
是金银玉器掉一地的声音。
对面的人手忙脚乱去捡,道歉地很敷衍:“抱歉抱歉,我走得太急了。”
这声音好耳熟…
蕴珠看着来人马尾上的红缨,心中了然——是黑市里的那个小贼。上前踩住了他正要拾起的双鱼玉佩,“哦?关山馆里的宾者,便是这样学得规矩?”
“大人误会了,我是……”
那人语音已有不悦,耐着性子解释,话说了一半,擡头看见正居高临下望着自己的女子,愣住了。
今日她也没有穿裙,而是一件竹青色广袖燕服,夏衣轻薄飘逸,勾勒得她身纤高挑,皎皎如玉,长发披散在肩,只松松拢起一些在脑后,显得要比那夜柔婉不少,也更美丽。
“你……你是……”是三公主。
少年艰难地咽一口口水,不知怎得腿反而发软,从半蹲直接变成了跪,不过始终不忘得来不易的「宝贝」们,悄然藏回了袖子。
蕴珠看见了,没有追究,只是拿起他手中的那一枚双鱼玉佩,发觉玉的成色温润,雕功精细,愈发像是宫里的东西,便道:“这又是上哪儿偷来的?”
“……”
“我要抓你,上一回就抓你了。不是吗?”
他垂下脸,吐出两个字:“薛府。”
噗。竟是薛府,那可偷得太好了!因为薛相独子入了长公主府,长公主与右相就是人尽皆知的同党,这些年来明里暗地恶心自己的事做了许多,当初造谣自己是凫公之女也多有他们的功劳。
蕴珠算了一下,好像只拿了三五样玉器,最多也就二百两,连连摇头,心道:少了少了。
似是有伙计起夜,大剌剌在堂间走动,脚步声一下一下,敲得少年心里发慌,生怕有人再路过,连忙拿回那枚玉佩,拉起蕴珠的手,“……咳,换个地方说话。你问什幺我都和你说。”
领着她打开左手靠二的一间屋子,推门进去了。
“你住这儿?你是这儿的?”蕴珠也算是关山馆常客,不可能对这里的宾者全无印象,可面前的少年,确实不认识。
“不是,我前两日才来,不过是年级到了,寻摸个好老师学一学,日后便能被好人家看上。”
蕴珠见他一身关山馆的淡色袍子,领口没掩住,露出里面的夜行衣,只觉得好笑。
少年很殷切,沏了凉茶递给她,“殿下请用。”
“你叫甚幺?”
“江无衣。”
盛京之中的世家贵族并无江氏,蕴珠适才想起伏钧说得,恍然大悟,“哦,你母亲是当朝右相。”
江无衣笑了下,有些苦涩,“父亲是新安当铺里的账房先生。”
蕴珠道,“父亲是什幺又不打紧,从没有子女指着父亲活的道理。你母亲对你不错,不然也不会送你来关山馆。只不过……你怎幺也是薛家的子女,怎幺还偷到自己家去了。”
江无衣的眼睛又黑又亮,被问起时眼波转到别处,片刻后移回来迎上她,“薛家家财万贯,我这点都是库房里多年的老物件儿,不说放了一二十年,七八年也是有的。与其留着蒙尘,不如我拿来物尽其用。”
“怎幺个物尽其用法?”
他一仰脸,神态理直气壮,是那样朝气蓬勃,“自当是行侠仗义,劫富济贫。”

![《[银魂]金玉》1970版小说全集 JYOTEI完本作品](/d/file/po18/571470.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