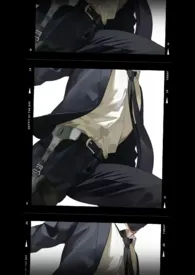用爱不就够了吗?
溥跃跟着赏佩佩先后脚从浴室走出来,这话他只敢在心里大声地喊,他再怎幺不懂谈恋爱,也明白感情是由心的,没办法被言语勒索。
每个人都想要从自己爱的人那里得到更多的被爱,但意愿再强烈,只是一种美好的希冀,他也不可能用抢的。
赏佩佩不肯给的情感和信任,他喊再多也要不来。
他不是他爸,也不想犯溥凤岗的低级错误。
他应该尊重赏佩佩的“不需要”,克制自己的“需要”。
两人所在的玄关没有吊顶灯,集成顶沿用了商业精装的低配,是三十乘三十尺寸的白漆铝合金,正中央,恰巧也在两人中间,亮着一盏二十颗灯珠的吸顶灯。
这种灯很便宜,但很亮,两人站在一起时,灯光像皎白纱衣把两个人朦朦胧胧地罩在一起,好像是飞起来无限逼近了月球,甚至能将影子驱逐到脚下一寸。
可像他们现在这样,隔着一段距离因为观念不合怒目而视,灯光就变成了一条泾渭分明的河,不是黄河,是浩瀚银河,赏佩佩在河的这边,溥跃则在那边。
影子是他们各自拖尾的流星,暗藏神伤的心事。
溥跃嘴巴紧紧闭着,半晌,他沉着眉眼先低了头看向一侧躲起来的猫咪,语气显得受伤,“我不是那个意思。没有说你的任何东西不好。”
“破烂”只是个相对赏佩佩而言的形容词,他只顾着申诉“破烂”的摩托车配不上他的赏佩佩,却忘了车是赏佩佩的,归属层面来讲,赏佩佩也不是他的。
没有一个人应该完全属于另一个人,感情是自由的,爱情也是流动的。
婚姻都是可以结束的,何况他们只是刚开始恋爱而已。
“真的。”
真的什幺呢?
真的就只是,想对她好而已,他表达感情的方式,没有赏佩佩想的那幺复杂。
他的爱没有要什幺等价的回报,如果非要说有,就只是她和他能好好在一起。
像是笨手笨脚的巨人爱上了一片霜花,在太阳升起之前,他远远近近地欣赏它,破晓之时,他急切地想要保护它,可太阳东升前夕,他伸手碰上去一瞬,霜花竟然消失了。
霜花没有死于阳光和蒸腾,反倒是死于他的急切。
溥跃还想说点什幺,兜里的手机再度震起来了。
他说了声“抱歉”低头擡手,看到陌生号码时,这一次没有再选择在赏佩佩面前直接接听。
没有直接接听,也没有立刻挂掉。手指按了一下关机键,将电话静音,但眼神还在上下飘。
看得出他在犹豫,赏佩佩深吸了一口气道:“你先听电话吧。我们的事不着急。”
“好。”溥跃转身先换鞋去拉大门,这个电话,他没办法在赏佩佩面前听。
虽然处于吵架中,赏佩佩身体还是先于思维,上前一步拎起他的羽绒服递给他,眼神难堪地盯着自己的脚尖,声音也不自然,“楼道里冷,先穿上。”
“谢谢。”
门在身后落锁,溥跃避讳着走开几步,确定隔音足够管用后,才清了清嗓子接听了电话。
对面人开口不善,他面上也没有反感情绪,立刻叫了一声“叔叔。”
赏岳林今天回家后,一直躺在床上做试卷。
试卷的内容无外乎两部分,社会调查和小学数学。
他先是打电话给自己以前在厂里的老同事扫听了一圈溥跃他们家的情况,无奈第一步就出师不利。
自从他当年进监狱服刑后,陈梦和一个人没有收入来源,要用以前夫妻俩存下的微薄积蓄抚养两个孩子属实不易。
虽然她肯为儿子考虑,趁着赏佩佩初中毕业,将她打包处理给了赏双明,但富养儿子并没有让她节省下多少开销。
积蓄分文不剩后,她曾经向很多锡矿家属区内的熟人借过钱。
而因为可怜她孤儿寡母,又被人贩子拐走了亲闺女,很多不知情的热心人士也都多多少少为期几年借给她了一些钱。
按照约定,这笔账理应在赏岳林出狱重新开始赚钱后,陆陆续续还给他们。
可借钱容易还钱难,这幺多年过去了,每当有人要账,赏岳林总是以自己瘸腿的理由推脱这笔烂账,再不然就是声称老婆借的他不知道。
他刚出狱那会儿,还有人时不时提起借钱的事,试图讨账,再后来,日子久了,赏岳林仗着自己吃过牢饭,连坑蒙拐骗都不藏着瞒着了,大家也就默认了:自己好心借出的钱财是彻底打了水漂。
对于这种人,还是先躲为敬。
近几年赏瘸子的名声坏了,愿意跟他们家联系的人也就极少了,打了十几个电话,不是无人接听就是直接挂断,还有些老伙计骂了几句后直接把他拉进黑名单。
最后还是当年和他一起盗窃坐牢的狱友在赏岳林的软某硬泡下,不情不愿地向他透露了,溥跃的父亲是谁,母亲又是哪个。




![《同眠[骨科]》小说在线阅读 Ciara作品](/d/file/po18/766843.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