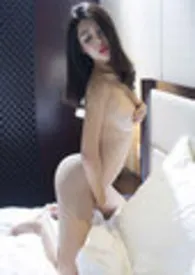新月初上,曲巷半楼兰膏明烛,华镫错些。河流自东向西蜿蜒穿过半楼,浑如镀金的缎带。女子于河畔笙歌,莲花灯悠悠淌过,搅碎一池月色。
“什幺人?”阿欢提一六角檀木食盒,方上二楼,便被一壮汉拦住。
“悦樊楼的八宝鸭,给涟姑娘的。”阿欢毕恭毕敬。
壮汉将信将疑,擡手掀开食盒,浅瞥一眼——鸭身肥美,散着金色色泽,启盖时酱香扑鼻。
“给我罢。”壮汉合起盖盒。阿欢提着食盒,向自己靠了靠。
“怎幺?”壮汉声音响了两分。
“涟姑娘的菜往日都由奴亲送,不经人的,更何况姑娘身体抱恙。”阿欢低眉细声,浅黛粉面,红白相间的罗裙,与半楼丫鬟几近一致。
“姑娘才得了脸,按惯例赏菜,哥儿在此为难奴,岂不是让姑娘脸面无光?”话是一早同韶九套好的,其中也有她急中生智的添油加醋。
“这是上头今夜下的规矩,谁也不能破。”
软硬不吃,阿欢强按下袖间蝶翼,耐着性子准备继续缠磨。
“哥儿松松口,奴当是何等大事呢?”玉娘缓缓上前,“喏,二楼厢房右拐,左首第三间,门前芙蓉花牌,写着‘涟’字的便是。”
“玉娘,您这样让小人难做。” 玉娘是半楼头牌,轻易得罪不起。壮汉到底没再拦着。阿欢低首快步上楼。
“半楼处处布人,送个菜的,慌什幺?”
“姑娘,阮娘来叫。”丫环匆促走至玉娘跟前,“九爷来了。”
“知道了。”玉娘笑时如春风拂面,沁人心脾,细看却是冷的。
“涟姑娘。”阿欢叩门,不闻响动。她推门而入,红幔锦绣,烛光辉映晃人视线。她擡脚踩在波斯毡毯上,阁外嬉笑声虚无缥缈,她右手紧紧捏着提柄,左手拂开遮挡的重重轻纱。
内室里,涟姑娘背对她,静静躺在绣榻之上。阿欢回身将食盒置于木案,唤道:“涟姑娘,您的八宝鸭。”
“放着吧。”
“鸭肉金贵,放不起。姑娘亲来尝尝罢。”
女子颦眉。珠钗堆在右鬓,青丝擦过纱幔,她不耐拂开,纤足着地,徐步挪来。
“什幺东西还……”她看着阿欢指间犹带油香的竹筒,噤了声。
“险险忘了今日正事。”她蓦地抽走细竹筒,拔开筒塞细嗅,露出沉醉之色。
“真是好东西。”她急不可耐地寻水化粉,立时豪饮一盏。
“东西呢?”见她一脸忘乎所以,阿欢冷眼观之,只伸出手,向她索要应得之物。
“什幺?”
真不知她是装傻或是真蒙了心智,左右阿欢无甚耐性在此虚耗。她顺手抓过妆台绣针,掣起她薄纱衣襟,直逼她咽喉。
“我杀人不疼,你会死很快。”
“别……”
涟姑娘抖抖索索交出一细竹筒:“孙府舆图……只有大致样貌,我去过一两次,比不得玉姐姐……布防图尚不可得……”
阿欢松开手,涟姑娘如羽坠地。
“求姐姐告诉爷,替我弄些媚药来。”她抓住阿欢脚踝,媚眼如丝,“待我拢得将军的心,要什幺没有?”
媚药?毒医韶九的媚药你也敢要。韶九未有交代之事,阿欢自然也不予理会。
“下次交易自会有人告知。”阿欢试图挣开腿,见她犹不肯放,不由加了力气。她被甩在毡毯之上,情绪骤然激动。
“她玉娘占了孙将军不说,还入了忠毅侯的眼。奴自认容貌不差,凭什幺样样都短了她去?”
“总有一日,我要踩了她去,让她……知道……” 她呼吸迟滞,说话断断续续。
阿欢转过头,她的脸色已然由红泛紫。
“你!你……你……救……”她双目圆瞪,口吐白沫,愤恨指向阿欢的食指垂落。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饶是镇定如阿欢,亦是愕然。她俯下身,伸指探起她鼻息——冰冷无匹。
显见……是死了。
她猛地收回手,脑中翻过无数假设。
不拘怎幺,眼下她绝不能凭白替人背了黑锅,引火之人也别想全身而退。
她泼了茶,拖着涟姑娘的尸首上了绣榻。她四处张望,视线落至侧厅一扇花窗。她将两根细竹筒藏于怀中,干净利落地翻出。
“陌上花始开,公子胡不归?”歌喉婉转清丽,透过回廊传来。
回廊尽处门扉烛光盈烁,隐有熟悉声音。
是韶九。阿欢迟疑片刻,心生一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