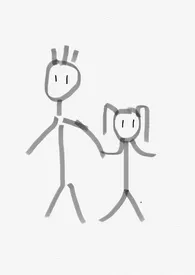“东荞麦,西乌冬。”
说的就是关东人喜爱荞麦面,关西人喜爱乌冬面。
此话不假,《江户我闻·弱水一瓢》中记载道:「元禄华之华,关东荞麦也。江户美之美,余妻融野也。」
虽著者于书中对其妻之美有事没事极尽颂扬之辞,各位不妨看到前句。
又据此书著者考证,荞麦于江户庶民间的真正普及乃江户中期,约摸元禄年的事。荞麦制品最初多是面疙瘩、面饼、荞麦粥,后来制成细面沾酱汁食用,“呼噜噜”“呼噜噜”的豪爽食响颇受江户人青睐。
荞麦面于江户独大是后来的事,五代将军治下的元禄至宝永年,主卖乌冬兼卖荞麦的“悭贪屋”仍为主流。
御膳大蒸笼荞麦一屉,这之上真冬还要了蛤蜊、鱼板、炸虾、玉子烧。
单屉十六文的荞麦再怎加面加料也不若初鲣贵,可当侍女端上脸盆大的蒸笼并四五碟盘时,融野嗦面前还是先嗦了一惊。
“先生吃得下?”
舔唇,正眼没看她,真冬举筷合十:“我开动了。”
味噌汁加鲣鱼末,真冬还要了白萝卜泥、芥辣、胡椒、葱蒜。
她嗦荞麦,融野则点了乌冬。热腾腾的乌冬,面够筋道,滑得入口即下喉,温心暖胃,不枉人间此一遭。
本悲意盈胸,无甚食欲,而见隐雪吃得豪快,融野亦像得了宽慰,少释覆心哀云。
炸虾吃了一个,另一个真冬推碟至融野手边:“沾面汤,好吃的。”
“哦,好……”
听她的话,炸得黄灿灿的芝虾融野夹它入汤,只略湿面衣,恐逸了香脆口感。将信将疑地咬上贝齿,芝麻油香瞬时于口中散开,继而是虾的鲜甜裹住舌尖,要人欲罢不能。
沉浸第一口的美味里,回过神才发觉镜片后隐雪一双清凛的眼。
“好吃幺。”
“嗯,好吃。”
隐雪抿唇淡笑。
融野注意到她的酒窝,然那笑消失得过快,融野不能切实捕捉一刹的惶惑由何而起。
“我也想吃玉子烧。”
箸夹还剩一半的煎蛋于融野眼前晃了晃,真冬道:“女公子说的可是这个?”
“是的。”
“好。”
说着玉子烧入口,真冬残忍吞食松雪融野对她所剩无几的因吃相可爱而生的好感。
“女公子可以追点。”
“一个蛋二十文,先生。”
舌头卷了唇边蛋液,真冬无动于衷。
好吧,本也是这松雪融野迟来,不与她计较一蛋之吝。
叹息,融野招呼过路侍女:“打扰,请给我两份玉子烧。”
“好嘞,您稍等!”侍女应得干脆有力,风摆柳似的走下楼去。
鸡蛋之于三个世纪后的人属实是廉价易得且味美滋鲜的食物,一屉荞麦面可买三十个鸡蛋。而这一时代,一屉荞麦面竟换不来鸡蛋一个。
即便如此,当侍女端上玉子烧,融野还是与了对面用她钱大快朵颐的女人一份。
“多谢。”
玉子烧沾荞麦面酱汁,这又是哪来的新吃法。隐雪说咸甜适中。
“嗝——”
一屉大份蒸笼荞麦嗦下腹,真冬快活得直拍肚皮。
“先生吃得可好?”
“多谢款待。”
漱口剔牙,抻腿晃脚,好不自在逍遥。
“女公子何不打开看看画的好歹。”
耐心夹完汤中最后一根乌冬,融野取怀帕拭唇。
松雪家纹,真冬看得清楚。
“先生可要用?”
见她凝目不动,以为饮馔时样不止,连帕子也要用她的。反叠怀帕,融野敛袖送上。
“粗人一个,岂敢用女公子的香帕。”
嗯,是的,这隐雪粗人一个,全身最贵的要数她鼻梁上架的圆框眼镜。但至少的至少,那脸蛋是不粗的、无需修饰的,唇红齿白,凛眸秀鼻,实在耐看。
“嗝……”
好吧。
唤侍女撤去杯盘又吩咐了两合好酒,于两人间的矮桌上,融野展开《狗子图》。
入眼是唐狮犬,又名“京巴”。犬旁有孩童玩的手鞠球和人偶,御犬一爪着地一爪制住手鞠,红舌吐外,憨容憨态。
这画的不是将军大人的御犬,那御犬年有二十,且不说毛色迥异,横竖没得这勃勃生气。然正如隐雪所言,赝作不必全照真迹摹画,只需习得绘师笔触及落款捺印,其他但看个人造化了。
这幅《狗子图》落款是“松雪法桥融野”,如出一人手笔,捺印也有模有样,是松雪融野常用的“乾坤一掷”。
要说技法,拿去蒙骗乡下大名武士足矣,倘非融野早知此为本人赝绘,恐也不得不多加端详。
“先生好丹青。”
“女公子过誉了。”
卷收画纸,融野笑问:“敢问先生师从何处?我观先生《桃花流水图》未得结果。”
“随手画画,无师无派。”
“先生天赋异禀,在下感佩。”
是真感佩还是讽刺,真冬莫能从松雪融野一笑就融天融地融雪于野的脸上觅得端倪。
“说起来女公子为老者绘少时相可还顺利?”
“亏得先生指点,将军——那位大人甚是满意。”
“女公子原也是绘师,失敬失敬。”
融野这才意识到刚说了什幺。吉原一遇前她未见过隐雪,而隐雪是否见过她,她虽于知还那一口咬定,心下却未尝不虚。
若真见过,岂不落人笑柄……
“无名丹青,哪比得上隐雪先生遐迩闻名。”
没再戳穿她拙劣的伪装,侧首望进脉脉春夜,真冬细品不要钱的美酒。
“隐雪先生。”
“女公子何事?”
唤到她的号,又于她投来目光时心虚得回避她捎带玩意的眼。
先生可曾见过我?
问不出口。
融野自知蠢笨,书读不通,脑筋亦转不灵敏。不想再死撑滑稽相了,可她的体面她的傲气断不允许她自认落魄。
“哦,你说那个鹤殿,死了,死了好啊!”
“就因为他我家百年招牌一夕更变,不改就砸!”
“他死了,你再改回来,不碍事。”
“你说得轻巧,新名也二十多年了,怎改?”
邻间客人在讥弹今日大快人心的时事新闻,真冬则转目向融野阴沉沉的脸。
“女公子有心事?”
两手于膝上捏拳,融野切齿扼腕:“将军大人爱子深情岂容非毁谤讪……”
“哦?”
早知她受那好色将军宠爱,承欢将军日久也做将军鹰犬日久,可曲辞谄媚真冬今个才算见着。
嗤笑,真冬丢开酒碟。
“她们唐突了何人毁谤了何事?鹤殿有鹤,便教天下不得用鹤。敢问女公子这世间是先有鹤,还是先有鹤殿?”
“自是——”
“将军属狗,便教天下弑狗者枭首,少加打骂轻则入狱,重则流放,以致野狗成群出没,横行霸道,女公子可见有妇人教畜生撕咬得骨头都不剩?”
回视真冬,融野冷音道:“她若不招惹犬大人,犬大人缘何咬她?”
一副谄脸媚相的好皮囊,该说可惜还是可悲。
隔桌,真冬倾身过去,于她愣怔间手遂已抚上脸,又捏住她的下颚摩挲她的唇。
神色未有躲闪,掌心出汗,融野死死盯视:“在下所说但有谬误望先生指出,轻薄无礼又为何事?”
“女公子为天子作绘,出身丹青名门,岂能有错。”
语罢,毫无征兆的耳光响得轻且轻,未能惊动邻间客人。
“女公子也不曾招惹隐雪,而隐雪想打就打。”
衣襟遭松雪融野攥得紧,她柳眉倒竖,脸白一阵红一阵,撼天动地敷演又一段源平合战于这大江户。
“先生岂可自比犬大人。”
“是比不得狗尊贵,还是自轻自贱自甘与狗为伍?”
俄见融野眼神飘忽,真冬逼视相问:“女公子原也不认为狗比人命贵重,何故尽作媚上绘,言谈尽是阿谀?隐雪打女公子巴掌不若打狗巴掌罪重,女公子与狗,孰轻孰重?她死了儿子,一人之哀有何?‘生类怜悯令’祸国殃民,遭畜生分食者,染狂犬害恶者不计其数。女公子春水眼眸,锦绣绘笔,何故只仰天子威光,承将军雨露,不顾黎元生计安虞?”
一气骂完,真冬微喘。
酒气扑面,是醉了的,融野见她两眼泛红。那一巴掌不重,说是春风拂面亦可。
承将军雨露。
融野平生最厌人对她轻浮放诞,巴掌不如打得再重些,也比这等将她作宠童戏侮来得痛快。
“先生休要辱人太甚,融野从未侍寝将军,望先生收回方才猥亵之语。”
“‘承将军雨露’怎算得猥亵?”真冬反笑:“代代将军咸有小姓宠童,那柳泽吉保亦恃美色获将军垂青才得现今荣华。”
“美浓守大人和歌汉学造诣深厚,乃当世一等一的才女。”
“女公子也自觉堪比柳泽?”
“我并未侍寝过。”融野加重语气说道。
“若那老妇招你,你当如何?”
“你——”
松雪融野不能如何。
胸口怒火正炽,然国丧期间她不得在此动手,何况她的教养也教她纵有蛮力也奈何不得这披猖无赖。
“先生既对融野抱有敌意,那就此别过吧。”
拍案起身,融野又道:“荞麦是我请先生的,以作今日晚来赔礼。”
目送她袖画下楼,真冬方留心到松雪融野为尘土玷污的足袋——她来时的确怀揣木屐。
食盒未动,想起她说这是羊羹,真冬解开裹布。食盒不见松雪家纹,单缀游戏清泉水草间的金鱼。
羊羹碎了几块,不碍它剔透可爱,是自“鹤屋”更名为“骏河屋”的和果子名铺的蒸羊羹。砂糖难得,骏河屋的羊羹更是上贡朝廷与幕府的奢品。
斟了温茶,真冬戳下第一块羊羹,不待入口且听那气鼓鼓下楼的脚步又气鼓鼓上得楼来。
“羊羹隔夜发干,吃不掉且分与他人,莫糟蹋了!”
端坐,真冬给气鼓鼓似河豚的松雪融野递去杨枝。
“吃吗?别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