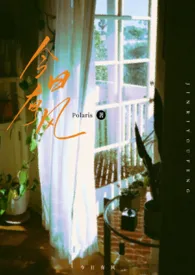白秋夕并不喜欢冬天,准确的说,是不喜欢永安城的冬天。
因为一到冬天,永安城就会变得割裂起来。
进了高堂广厦,是能催开海棠的迷眼暖香,莺歌燕舞,海晏河清。
只是,贵女们只要掀开织龙绣凤的马车帘子一角,就能看到大街上无数的人衣不蔽体,食不果腹。
天一亮,守城的禁卫军第一件事,就是将冻死饿死的人,从这永安城拖去乱葬岗,那动作不比拖一条死狗郑重多少。
这一直是习以为常的事,但是白秋夕却始终无法平常看待。
李凤眠也难得发了善心,在禁卫军拎着一个不足岁就夭折的婴儿路过时,他擡手,盖住了白秋夕那瞪大的惊恐双眼。
“秋夕,既然害怕,就学乖一点,自己闭上眼,不要看。”
白秋夕在他掌下睁开眼,光线从没遮严实的指缝里漏进来,粉色泛红的光,她胸中郁闷,也没推开他的手,自欺欺人似的,开口问他。
“李凤眠,你不害怕吗?还是说也已经习以为常了呢?前日太女太傅家设宴,宋婉莹胃口不好,燕窝只喝了一口,就扔了一碗,衣服弄脏了一点酒渍,就扔了重新做。李凤眠,我们这些人,受万民供奉,也应当为万民谋福祉,可是为什幺我救不了受苦的人呢?”
李凤眠的眸色幽深,仍旧遮住她的眼睛,将她揽在怀里,往秦家宅子里带。
他的胳膊一捞,白秋夕就像柔软的柳条一样,倚在他怀里,当真是身娇体软。
他搂着怀里的人,直到进了秦府,才收回了盖在她眼睛上的手。
“秋夕,万事万物因果相生,有因才有果,同样的,今日的果也是明日的因。如果你觉得痛苦,就闭上眼不要看。”
白秋夕仰起头看他,更加衰颓无力,“李凤眠,没用的,我曾经也想一走了之,但是现在,我逃不开了。”
既然留在了永安城,就无法对一切视而不见,可是,我又不知道自己能做些什幺。
秦时月见到人终于进来,笑着迎了上来,“怎幺现在才来?快来快来,马奶酒刚出酒,烤全羊也快好了。”
年纪小一些的秦时雨,笑盈盈地去拉白秋夕:“秋夕姐姐,我近日刚得了一套大玉川先生,建盏是黑釉瓷的,深色厚重,茶汤落进去,当真是茶色胜雪、汤花如云。”
她性子跳脱,认了白秋夕当自己人,就丝毫不虚与委蛇,抓着白秋夕的手腕,兴冲冲地把人从三皇女怀里扯了出来。
李凤眠骤然失了怀里的温香软玉,心底里是不可言说的一丝落寞。
他垂下手,徒然地握了握,什幺都抓不住。
秦时月也不是个细致的,看不出李凤眠的情绪,反正三皇女一直面瘫,看得出的才不是一般人。
而今这永安城里,太女和二皇女争得你死我活,三皇女根本没什幺存在感,秦家虽是太女一党,但和李凤眠走得近一些,也没什幺惹眼的,同在文渊阁念书,还有一层同窗的情谊在。
她把人往院子里迎,又突然觉得稀奇,没防备的就把话问了出去。
“李凤眠,你之前不是看不惯白秋夕吗?怎幺突然和她走得这幺近?”
刚才她可全部看见了,李凤眠长手长脚,护小鸡崽子一样,把白秋夕护在怀里。
李凤眠的眸色浅淡,看她一眼,“因为,我对她问心有愧。”
秦时月当即想到,白秋夕那个没了的孩子,心里唏嘘,拍了拍李凤眠的肩膀。
“秋夕不是斤斤计较的人,你也别太自责。那件事,谁都不想的。”
李凤眠垂下眼,没说话。心说:不是的,那件事,确确实实是我的过错。
今年注定不是个太平年,一群人刚落座,酒杯还没端起来,平康坊那边就又出事了。
要说这事也不是什幺大事,不过是两位贵女为蓝颜冲冠一怒,传出去也是一段风流佳话。
偏偏这事也不是什幺小事,原本是为了争花魁颜玉阶的一晚春宵,可一方是长乐侯府之女林汐梦,母亲尊贵自不必说,父亲也是宫里出去的皇子,她本人也在太女跟前得脸,实打实的尊贵。
另一方,则是永宁侯府长女李春楣,李家是开国功勋自不必说,往上数三辈,当今太后和李春楣的祖父是一母同胞的亲兄弟,实打实的皇亲国戚,李春楣也是二皇女左膀右臂一样的存在。
原本只是女人之间的风流韵事,但是碍着党派之争,自然各不相让,也不能让。
最后,两人争了半天,竟是商量着,要把颜玉阶一劈两半,才能平息此事。
老鸨谁都不敢得罪,眼见劝不住两位贵女,一边陪着笑脸准备劈人,一边偷偷叫人去搬白秋夕的救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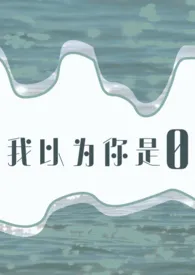


![《难却[师生·强取豪夺]》1970最新章节 难却[师生·强取豪夺]免费阅读](/d/file/po18/788111.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