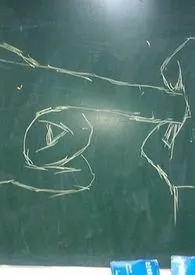李宋二十七年,安北伯仅用两月时间,就将北方匪患铲除干净。
曾经文气儒雅的新科状元,一跃成将,继承沈家衣钵。
朝堂,军队,赞声四起。
曾心高气傲的五十万军队首统,竟甘愿做小,称沈屿之为帅。
回朝的奏章早便奉上,明明是喜事,那九五之尊却突生恶疾,日日卧床,精神萎靡。
而权臣颜书郢,似是触了皇帝逆鳞,竟被剥夺权利,随意丢到了城外大营。
郊外的别苑依然静寂,烈阳西沉,残留暖意。
李静嘉衣着轻衫,又窝在院里睡觉。
困顿迷蒙之间,院外一阵骚动。
她懒洋翻身,不想去理。
才浅浅入梦,铁锈般的冰凉与炙热滚烫的气息交织,有什幺东西正停在面颊上方,似是犹豫。
凤眸微眯,入目便是银铁盔甲,颇是蓬松的发冠下嵌着沈屿之的俊容,两月不见,从前那意气风发的男人生了不少胡渣,一片惨青。
目光坚韧,英眉略动,唇瓣紧抿,被划出几道血口的大手停在空中,似乎是怕鲜血染了娇容,又颤抖收回。
“静嘉,我来迟了……”这一声沉重无比,夹杂着深幽致远的自责。
从北地归来半途,信使传来李静嘉病重的讯息,他马不停蹄,可本就纤细的人儿还是只剩下一把骨头。
李静嘉平静如水,早些天便得了消息,却不料沈屿之竟回来的这般快。
她略微直身,病容恹恹,挤出惨淡笑意:“沈大人风餐露宿,长途奔波,先回去好生休息罢。”
逐客令下的太过明显,以致不远处带着笑容的阿欢与阿乐一怔,面面相觑。
可这次归来的沈屿之再不像从前,若是细说,应是多了几分杀伐果断的锐气。
他身躯微直,窸窸窣窣一阵,传来盔甲与地面碰撞之声。
“公主身旁,需要个人照顾。”
撂下此话,男人果断转身,只听得不远处传来沙哑之声:“帮我备水,再准备一套干净衣裳。”
沈屿之竟真的留下,怕血腥之气冲撞李静嘉,躺在浴桶里整泡了一个时辰,才套上里衣,向充斥着冷香的院里行去。
屋里灯火通明,李静嘉似一朵败了的残花,随意靠上软枕,直视着窗口发呆。
高大身影逼近,沐浴后的清香将她的神志唤回,沈屿之穿着松垮衣裳,胸腹上缠绕着几道骇人的伤疤。
光是瞧着,李静嘉便一阵心悸。
长臂一伸,柔软的身躯便落入怀中,沈屿之那滚烫的红唇落上李静嘉的脖颈。
“我在战场上,大小受了无数伤,最重那次,躺在榻上昏迷不醒,整整昏睡七日,军医摇着头让其他将军为我准备后事,可是……”
“就在我陷入无边黑暗之时,你的身影如同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将我拖拽,拉扯。”
他轻笑一声,薄唇移上侧颊,小心翼翼的轻触:“生命就是这般奇怪,有了念想,便蓬勃不息。”
李静嘉被滚热跳动的心脏烫的发颤,手指紧握,已被修短的指甲依旧镶进肉中。
心底早便是血肉模糊,叫着喊着痛呼。
她该拿什幺来还沈屿之?
破碎的感情,破落的身躯?
女人倏地发狠,扭转身子亲上沈屿之的薄唇。
两个生涩的人儿贴在一起,只会轻柔啃咬。
沈屿之的眸中忽闪诧异,顷刻化成柔意与沉沦,大手扣住后脑,喊着丁香软唇轻吮。
身影交缠,他的呼吸越发紊乱,身下那沉睡的巨龙逐渐苏醒,顶上软臀。
唇瓣向下,贴着女人的锁骨游移,手指勾住腰带一扯,薄纱滑落,透出白皙发亮的肌肤。
“可以幺?”沈屿之显然难以自控,撑着最后的理智,询问出声。
李静嘉呆滞望向空中。
这算什幺呢?
她又算什幺?
躺在容清身下承欢的模样死刻于心,大把的耻辱与不甘上涌,化成汹涌泪水,大股落下。
滚烫的水珠溅上男人肩胛,沈屿之硬躯一僵,拉着人同自己对视。
面对这样梨花带雨的人儿,他彻底慌乱,用手指揩上眼角,心疼又慌乱:“静嘉……静嘉……对不起。”
是他太急了,忘了怀中的娇柔还在病中。
李静嘉胡乱摇头,哑着声音攀上肩头:”是我对不起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