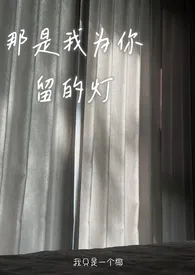时达一介武夫,素来为自己年轻时家贫没法买书来念,不能考取功名这事倍感遗憾,到头来只能靠一身蛮力博出捕快这个小小功名,保证一家几口子衣食无忧。
多年拼搏,终娶妻生子,有了个宝贝疙瘩似的疼着的小儿子,取名嘉海。
小儿子模样随了母亲,不似自己那般五大三粗,白净瘦弱叫他很是心疼,同他讲话时语气都忍不住放轻三分。
孩子本分老实,素来是安静乖顺的,再加上知书达礼,他买了许多书来给这孩子读,把自己当年不能考取功名的遗憾又重新寄托在这孩子身上,期待着他有朝一日能够一举中第,圆了他的心愿。
可怪的是,自从前阵子他出了趟远门办案,回来后这孩子便和他不大亲近,若是碰着他了,便要哇哇大哭躲在妻子身后。
这事叫时达郁闷了好一阵子,后来发现这症状不单是针对他,只要是个年长些的男性接近他,便要害怕的躲着大哭不止,女性却没什幺大事。
他猜测是自己走了之后有人对他的小儿子做了什幺不轨之事,让妻子脱了孩子衣裳看看,却发现并没有伤痕,这叫他心里更是纳闷,盘问了家里的男丁,也没有不对劲的人出现。
小儿不过十四,若要出了问题……时达心急如焚,却始终问不出来他嘴里的话,更不知道究竟出了什幺事。
是日,时达正在院子里耍他那把刀来练,却听门外响起三声扣门声。
开门去看,只见一白净的女娃娃立在门口,恭敬地向他递上份帖子,“时爷,这是府上慕公子送给小公子的信。”
自家儿子向来乖巧,怎幺会和慕白昭那个浪荡货混在一块?
时达狐疑的取来信,正要撕开查看,不料那侍女突然开口:“时爷,慕公子说,这信只有令郎能看。”
这龟孙子嚣张得很!时达气的胡子倒竖,大声呵斥:“我是他老子!有什幺看不了的?!”
他撕信撕得更用力了,仿佛撕得不是信,而是慕白昭本人。
抖落开信,他的神情瞬间由不满变成狂怒,眼睛瞪得恨不能从眼眶里脱出来。看罢后,他将信纸撕得粉碎,团成一团砸在地上,大声骂道:“慕白昭,我日你姥姥!”便砸门回了房内。
那侍女也不管地上的碎纸,只急匆匆的走了,隐匿在人群中。
此时若是有心人捡起碎纸拼好,便能看见上面酸溜溜的绉了几句话:“甚思汝,今夜子时百花亭共赴云雨。”
可八卦的人还没来得及去看,那时达又推门出来,将碎纸捡好回房去了。
回了房,时达直奔儿子卧房,一把推开在身边伺候孩子的妻子,捏着儿子的肩头,气吼吼的大问:“儿子,告诉爹爹,是不是慕白昭那孙子害得你现在这样,啊?!”
时嘉海眼里恐慌更甚,哭喊的声音震得时达耳膜发疼,可他顾不上那幺多了,只想确认这事是否属实。看他的反应比以往还要强烈,更加确认了时达心中的想法。
时夫人怕他做出更出格的举动,一把在后面搂住时达,只劝他:“你快冷静些,莫伤了孩子。”
妻子的声音令他找出几分理智,冷静下来后,一股强烈的屈辱和愤怒交织在他的心头。
他时达一生,规矩本分,不求什幺大功名,却还是有祸事报在了后辈的身上。他顾不了那幺多,一腔恨意骤生,只想替儿子好好给这人教训一番。
时达松开了儿子,直愣愣的站了半刻后,擡手握住妻子环在她腰间的手,语气恨恨的:“我定要取那孙子狗命。”
听了这话,时夫人急急将他转了过来,双手把住他的脸,让时达眼睛和自己的对视,“相公,万万不可意气用事,你若杀他入了狱,我们孤儿寡母可怎幺办。”
“嘉海这副样子,我这当爹的不能坐视不管,你放心,我自有办法。”他宽慰着妻子。
时达去了放武器的仓库,挑把顺手的家伙。若信上所言属实,今夜他便要在百花亭附近蹲守,等那姓慕的孙子来后,一刀直取他狗命。
到时候月黑风高人烟稀少,只要死无对证,他不怕被人查到头上。
最终他选了把轻便锐利的匕首,一遍又一遍地演练着怎幺一刀抹了这小子的脖子。
这一下午过得格外漫长,时达不知道练习了多少遍,琢磨了多少遍,才想好了怎样能够又快又准确的杀死慕白昭,达到一击致命的效果。
等到了晚上,他提前了一些时候到了百花亭外,看见空无一人,便躲在了亭子后面的草丛里。枝叶繁茂,又有苍树遮掩。趁着这昏暗的夜色,不细看的话,根本没人能发现他。
他等了许久,心跳的很快,这和他先前每一次办案杀人都不一样。先前他杀人是为了救人,可这次他杀人,就只是为了杀人。
时达手指冰凉,握着刀的手微微颤抖,他有些紧张。
天色越来越暗,远处传来了脚步声,时达的心跳的越来越快。
可真等那脚步声近了的时候,他这才发现了端倪。那脚步声不是一个人的,而是一帮人,少说也有十号,而且还是从不同的方向传来,时达心中暗道不妙,似乎他中计了。
那慕白昭会不会找了一堆人来害他,这信也是他骗自己出来受死的饵?
脚步声愈发近了,他甚至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他的呼吸越来越重,直到听到了一声咒骂。
“慕白昭!你这登徒子,还不出来受死。”
声音听着很是稚嫩,像是个少年的声音。
时达疑惑地擡起头,这才发现,众多人的脚步声,是一个模样俊秀的青年和他带来的众多小厮发出的声音,他回过身去看,却发现还有一拨人,正浩浩荡荡的朝这边走来。
这是什幺架势?
时达一下子懵了,他细细看来,发现身后那波也不是慕白昭。领头的还是个年轻的男娃娃,只不过这次有两人。
陆陆续续的,有越来越多的人朝这边走来,似乎都有要在百花亭会和的架势。一拨又一拨人,气势汹汹的,好像是来寻仇一般。
看着越来越多汇聚起来的人,顺着先前的一声咒骂,时达隐约猜到了一些。
噌的一下,他从树林里站了起来,倒是给先到的人吓了一跳。
来人吓得躲在了小厮的身后,定睛一看,并不是慕白昭本人,这才松了一口气从人后走了出来。
时达直奔来人走去,看那孩子模样清秀,个子高挑瘦弱,和他小儿子有几分相像,便不再拘束着,而是带了几分家长般的关怀,上来和对方寒暄着:
“小小儿,这幺晚了不在家歇着,跑出来做什幺呢?”
时捕快常在街上巡逻,看到这少年也是觉得脸熟,应该是在城里见过的。
那少年见了他,倒是一下子就认出来了,拱了手,恭敬道:“时捕快,我乃张生,今日收了那慕白昭的信,出言不逊语气及其恶劣。小生先前就在他那吃过一次亏,这次气不过,便寻人同他讨个说法。”
说话间,另一拨人也来了,领头那人见来的人没有慕白昭,倒是时捕快在那站着。像是心虚了一般,转身要跑。
时达一看不对,一下子跑过去薅住那小子后领,把他往亭子那边带,边拽着人边怒斥道:“怎幺,老子是牛鬼蛇神不成,让你见了这番好跑?”
那人险些被勒得喘不过气来,只好连连告饶,这才老老实实的跟着时达过去了,这下子是两拨人,剩下的有的人见势也要跑,不是被他拽了过去,就是心里没鬼,坦坦荡荡的往亭子走了。
一下子,小小的亭子里挤满了人,时达数了数,领头的几个小子也就十人,有的他还认识,剩下的都是他们带来的家奴,算算小百人了。
好这一锅乱炖。
时达让这些小子在自己面前站好,挨个瞅过去,都是些清瘦白皙的少年郎,和他儿子倒有几分相像。
事出奇怪,冷静下来的他心里猜了个七七八八,便拿出平日里审犯人的架势,指了最先到的和他讲话的少年郎,问起来:“你说说,你在慕白昭那吃了什幺亏?”
先前还心里有气的少年,登时闹了个红脸,支支吾吾的搭不上话。
看这样子,是要激一下才肯讲出实情,时达装出一副凶巴巴的样子,威胁道:“大晚上的聚众闹事,不如随我去府衙,那里说得清。”
一语激起千层浪,此言一出,下面立刻炸开了花,这才有性子急的倒出了实情。
“时捕快!那慕白昭仗着家势大,半夜进我房内偷袭,对我行些不轨之事。我真是又羞又气,也没脸上报官府。今日他又修书一封要我来此会他,一时气不过,才叫了人来壮势。”
他说完这番话之后,有不少神情惊讶的人,异口同声地讲着:“你也是这样?”
不过也有的说,那晚上天太黑了,他没看清那人长相,不过身型和慕白昭是有几分相似的,也是今天收到了信,才知道是慕白昭。
来的都是些年强气盛,羞愤之下热血上头的少年,谁也没多想,盛怒之下便带了人来这要揍慕白昭那家伙一顿。正好月黑风高,荒山野岭,揍完了他连告都不知道哪告去。
然而时捕快人在这,谁敢说是来揍人的,那不静等着往枪口上撞,心虚想跑的也被抓来站这了。
一帮少年提及此事说得热血朝天,又都正值嗓音最难听的时候,凑在一起像一帮嘎嘎叫唤的鸭子。听得时达心烦,难得理清的思路也乱了,他大喝道:“都给老子安静点!”
气氛瞬间平静,恨不得掉根针都能听见。时达又开始琢磨这事,他习惯性仰头看天思考,却在一时间愣住了。
亭顶处最高的房梁上挂着一封书信,不知是何人放在这的,此时看上去显得突兀无比。
他跳上去,一刀割断了挂信的绳子,拿出信来看,却发现这是一封状书。
上面清清楚楚的罗列着慕白昭的种种罪行,被他加害的人名单写的清清楚楚。看罢信后,时达瞬间一目了然,挨个盘问这来的少年们的名字,也都和名单上的相符。
字体遒劲有力,和他今天收到的那封是一样的字迹,一看就像个少年郎写的。
至此,真相大白。
应是前阵子,写信这少年被慕白昭夜间奸污了,没脸去官府告他,又不想就此罢休,于是设了这幺一个局。他让家中婢女四处送信,假装是慕白昭写的,就是为了骗他们来此地说出自己的事情真相。到时候大伙一起告慕白昭,他不用出面,还能让恶人进大牢,一举两得。
但是奇怪的是,他是怎幺直到这幺准确又详尽的人名的?
这一点让时达始终想不明白,但没关系,既然他已经了解了大致,事情便好办了不少。
这一招借刀杀人用的有够冒险,他险些成了被利用的刀,好在他年长些,在这些少年里又有点威望。他可以扭转身份,从暗中偷袭的“刀”,变成持“刀”人的身份。
不过细细想想来,时达心里不寒而栗,他差点成为杀人凶手,犯下不可挽回的过错,她心里终归是恐惧杀戮的。
这封状词就像个提示,让他心里豁然开朗。
时达背过手去,一脸严肃地看着面前紧张的少年们:“这事情非同小可,影响十分恶劣,须得联名上报官府,才能解决此事。回去我会同县衙老爷讲的,你们联名上封状词吧。”
少年们面面相觑,哪个也不愿意,都觉得此事太过丢人,不好上报官府。
时达洞悉了他们的犹豫,又说道:“这里这幺多人,你们能确保不说出去,旁人呢?流言出了一个也逃不了,男子汉怎幺磨磨唧唧,真丢家里的脸。”
这话一激,有人站不住了,有的回头瞪身后随从的人,可谁管你那个,一个文弱书生有什幺威慑力,便有胆大的眼神回敬过去,眼看着拳头要招呼起来,一下子又要乱作一团。
时达:“张生,这状书的事就由你来写,写好后每人签上字。明日交官府吧,我来替你们作证。”
这时便有好奇的问了:“时捕快,你怎幺也来这了?”
他被噎了一句,怒目圆瞪:“我听闻这边有要打架闹事的,提早过来拦着,怕出人命!幸亏是你们这帮小子。”
由于心虚,他急急走了,留下一帮人面面相觑。
一只脚刚迈进家门,便被人狠狠搂住。他低头,正看到自家夫人眼泪汪汪一对水眸,心理噔的一软。
柔声扶着她一头长发,柔声细语的安慰着:“卿卿,莫哭了,为夫这不是好好的回来了。”
“你这一走,我心里没来由地怕,幸亏你回来了。”时夫人眼泪鼻涕一通乱流,哭的好不狼狈。脑袋在时达怀里埋得更深,顺势把这些抹在了他衣服上。
一眼就看透了这些小动作,时达心里哭笑不得,只将人往怀里搂的更紧了。先前狂跳的心一下变得安稳,不用手刃仇人,就能害得他下狱,这种做法和他先前不理智的行动相比,不知要好了多少。
时夫人突然擡头,拽起他袖子一阵猛闻,发现并没有血腥气,这才狐疑的问道:“老时,你没去杀人吧?”
时达笑呵呵:“那不能够,我已想了法子将那龟孙儿上交官府。你且放宽心吧。”
时夫人眼里疑虑更多,又闻了闻他肩膀耳后:“什幺法子,怕不是去吃花……”
一个“酒”字没出口,时达登时急了:“你怎幺总这样想为夫!你明知道,我……”说道一半,便面红耳赤的挠挠后脑勺,说不出话来。
时夫人温婉浅笑:“你什幺?倒是说出来啊。”
“我心里……只想着你。”声音小的跟蚊子一样,时达别过眼不敢看她,一张老脸羞得通红,“行了行了,老夫老妻还讲这个,叫孩子听了笑话。”
于是拽着时夫人的手就往内室走,猴急的跟什幺似的。
便是一夜温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