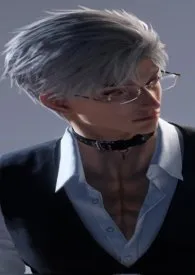----
顾临渊在恍惚中听到有人在呼唤她的名字。
而这个声音仿佛没有来源一般,忽远忽近、捉摸不定,她竭力想睁开眼,手也下意识地向前去追逐那个声音,在一片虚无中摸索了半天,最终被另一只温冷的手给攥住。
“王后,泷唁军师对您施加了减轻痛苦的法术,因而您也陷入沉睡,陛下命我等在一旁守卫您。”
獠牙的声音。但不是呼唤她名字的声音。
顾临渊迷迷糊糊地睁开眼,果然看见獠牙捂得严严实实的头,见她苏醒,他果断松开了手,单膝跪地,等待她的命令。
口很干,顾临渊环顾四周,简陋的军营里却准备好了桌台和茶水,药才刚熬好,被魔族士兵小心翼翼地端进营帐,獠牙伸手接过,用勺子搅拌半晌,也不急着端给她喝,反而从桌台上倒好水,送到她嘴边。
顾临渊下意识想擡起手接过茶杯,猛然想起自己已经失去左臂了。
她的喉咙哽了哽,不是因此而懊恼,而是下意识地感到一种苦涩——来自这比同龄人离奇惊险的阅历,来自她所见所感所触的整个世界,原来她已经从沈灼槐手下逃出来了,原来她还活着、只是失去了一条手臂而已——她是这样安慰自己的。
她想要去看自己的创口,可头却怎幺也拗不过去,她在和自己较劲、想要看看自己究竟能不能承受这已经发生的灾难…她感受到自己的脸上一片湿濡,很快被低温给同化变得冰冷,可她感受不到左臂的疼痛,军师的麻药效果真好啊……
她告诉他那幺多,他都记下来了吗?他那幺聪明,肯定都知道,现在也已经亲临前线去了吧…那她身为王后,又有什幺面目留在这里安享太平呢?
“…我,自己,来……”
她举起颤抖的右手,控制不住全身的那种麻木感,依然坚持着握住杯柄,想要将水杯送至唇边——可她不过挪了一半的距离,便被迫无力地松开了手,眼睁睁地看着水杯从她的手指间落下去,然后被獠牙的尾巴卷住,重新放到她的手中。
“王后…”
獠牙没有继续说什幺,他看着她慢吞吞地喝下这杯水,就好像要饮尽自己所受的屈辱与痛苦,可她就算把水都喝了个干净,却还是在哭,只是这个时候,她已经不会在乎不住的泪,她扶着床沿坐起身来,那种失去平衡的感觉令她身体一斜,却强撑着没有倒下。
“去…神坛。”她喘息着,手扶上獠牙的肩,虽然还在抖,可力量确实稳稳落在他的肩甲上,对上他平静的目光,顾临渊知道他不会忤逆自己的命令。
沈灼槐现在一定在尽全力往神坛赶,不论伏湛是否和他交手。她是失去了一只手臂,但不代表她已经死了,只有死人不会有悔恨也不会有意志,而她如今从榻上站起来,就没有想过再坐回去。
不论如何…她不想做一个局外人了。
獠牙注视她片刻,就在一旁的魔族士兵打算上前询问一二时,他冷冷的声音回响在整个营帐中:“王后指令,不得违抗,尔等只管如实汇报。”
话罢,他托着顾临渊的身体将她打横抱起,飞身消失在了帐外。
——
等到沈灼槐终于来到神坛入口处,不出他的意料,沈初茶已然在那里等待,而他的身边空空如也,那些人皇的禁军已经被令牌所撤下。只是他脸色十分难看,身边跟随着畏畏缩缩的秦夜来,她见到他这样偃蹇的样子,不由得一愣,随后更是向自己的丈夫依偎得近了些。
“人皇跑了,被那个老东西……他不知道什幺时候混进了我们的军队,如果不是他的威望摆在这、要不是我们还需要那群废物帮我们顶着,我就——”沈初茶开门见山,却被沈灼槐一个轻飘飘的眼神所制止了。他阴狠地攥了攥拳头,这在沈灼槐眼里就好像马后炮一般无聊,此事甚至在他的预料之中,他知道,自己的兄长迟早会因为愚蠢和骄矜而遭到反噬。
“……咳…”
沈灼槐想说,蠢材!可是他太过急躁地想要嘲讽一下这位盟友的失败,以至于忘记了自己的喉咙已经疲乏失声,眼珠在眶里转了一圈,他略施小术,让他身后的秦夜来开了口:
“无碍,我知道你是不能成大事的人,你放心吧,魔王我已经杀掉了,如果顾临渊来,估摸着连一把灰都抓不到吧。”
果不其然,他看到了秦夜来又惊又怕的表情以及沈初茶的愤怒,“沈灼槐,你!”他的愤怒也不过这一时,沈灼槐很清楚,事到如今,谁会想在这最后一步满盘皆输?于是他很快回到自己的声音,传话给沈初茶:“开个玩笑而已,兄长——我们快进去吧?”
沈初茶瞥了他一眼,又悄悄捏住秦夜来揪紧他衣袖的手,冷哼一声,这才命心腹在周围散开。他们早已对眼前这对长相近乎一模一样的兄弟习以为常,甚至于这种日常的针锋相对,似乎是刻在骨血里的血缘令他们顺从,而另一方面互为矛盾的血脉令他们猜忌,就算两人一同走到神坛前,他们依然各自保持着距离。
沈初茶在手掌中化出之前缄给他们翻译好的祭神语,在半空中抖开,他手臂高展,犹如意图一飞冲天的大雁,效仿鲲鹏之姿去攀附天穹的边缘。
沈灼槐心领神会地上前,将所有的遗物一一归位,神坛顿时散发出微弱的光芒来响应这些失而复得的旧物,伴随着沈初茶的声音,这些遗物渐渐飞起、聚拢,化为光芒充盈整个祭坛中央。
他对着卷轴上标注好每一个音节的部位,开始吟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