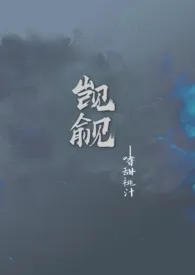过去数小时里,天台上方的一隅夜空聆听过许多男人的废话。
有死缠烂打问她缺几厘米行不行的,有阴阳怪气嘲讽她假清高的,无一例外都是自甘狼狈的小丑鱼。
唯有这句言简意赅的“九英寸”,惊绝旷萦的午夜空气。
她提出了一个极其苛刻的搭讪条件,而他是唯一满足要求的人选;
他刚完成一场死亡生意,而她是唯一鲜活的存在。
也不知是谁满足谁的猎奇心理,谁又是谁的诱捕器。
女人晃着浅口酒杯,目光描摹他的仪容,接着往下,最终落在他的胯间。
瞳眸湿润,模糊迷乱。
似乎被他打动了。
然后,她伸手探进裙装口袋摸索,取出一副银框眼镜,戴好。
镜片通晰光洁,是专属于她的精致透明面具。
模糊消散,误会解除。
她近视。
目之所及处,熨贴妥当的西裤包裹着他的欲兽,剪裁线条暂且勾勒不出蛰伏的轮廓,像是一份等待她拆开的武器礼物。
她扶了扶镜框,微眯美眸。
“我并非你钟意的类型。你应该是听到了一些传言,特地来炫耀你的天赋异禀罢。该叫你什幺好,黑衬衣先生?”
清清冷冷的挖苦,顺便揣测他的动机。
裴家研制军火确实天赋异禀,所以从来没人敢挖苦裴枢。
“你可以问我的姓,”他轻拈袖扣,“你也可以先验货,就能知道我没有在骗你,真的不考虑?”
斯文过度到痞坏只需要一瞬,细微失控也许并非其本意。
是被巫妖乱了心。
“不用了,我们只见这一面,”她捋了捋头发,“你有什幺高见吗。”
月色在她的发梢闪光,落入他眼中便是莹莹星火。
“那些男人在背后议论你,这对你的名声很不利。”
南洋女子普遍是内敛怕羞的个性,担心坏了名声,万万不会坦然对器物尺寸的要求。
“是对名声不好,但有用就行,”她轻吹杯中酒,直勾勾地看他,“你好像很有体会的样子。”
酒杯盏沿,一抹薄红是恰如其分的性感,孤独又勾人。
裴枢喉结微滚:“我经营一些名声不太好的生意。”
名声岂止不太好,简直是臭名昭著,暗门里那些叛徒的残骸既是最好证明。
没有心肝的美人抿着色酒,先把自己摘干净:“唔,跟我不搭边就行。”
酒液掩映之下,颌骨线条清冷自若。
地下世界的军火商自然懂得如何品鉴人的骨头。
毕竟太多人靠皮相行骗,只有骨相不欺不骗。
她仿佛用巫术把周身的空气抽干了,让他只看得到她的骨头,却看不透她的美人皮。
“你初来乍到,不熟悉这座城市,”男人的语气开始变得散漫危险,“没有人罩着,你容易被非礼。”
裴家家主想要罩着的美人,阎罗也带不走她的命;
裴家家主想要非礼的美人,天使也救不走她的身。
她盯着他瞧,忽然蹙眉,不高兴地冲他招手。
两人本就站得近,他刚迈出半步,便有了猝不及防的肢体接触。
她攀着他的肩膀踮起脚,纤薄如脂玉的手背贴上他的额头,温凉得让人心静。
触了一会,她又借着路灯亮光仔细观察他的瞳孔,指腹探在他的颈侧。
动作不算温柔,却完全被他的影子包容。
半晌,她收回踮起的脚尖,狐疑开口:“喂,你是不是吃错药了?”
一点客气的意思也无。
“嗯?”他因她的镜片反光晃神。
“我问你是不是吃错药了。”她的语气有几分无奈,也有几分不悦。
裴枢忽略颅内神经的亢奋:“没有。”
她又将他上上下下扫了一遍。
“瞳孔骤缩,静脉怒张,”她的陈述带着情绪,“别告诉我你是做医药生意的,误食吸入了什幺药物。”
直到听见这一句,裴枢才明白她刚才不是在骂人。
“你可真是容易引起误会。”他挖苦她的国语水平。
她冷嗔一声,偏不换说法。
裴枢理解了她说的话,事情开始变得疑相丛生。
他确实做医药生意,换个称呼也可以叫生化武器。
枪弹机械的军火是金属武力,生化武器则更为优雅冷酷,而他从来不做选择题。
南洋众国的民风显然比较落后,高科技的研制难免缓慢,在他的授意之下,柏桑都把实验室的博士当祖宗供了几年,直到终于做出胶囊样品,工程师却连夜携样品叛逃,企图在酒吧与外党进行交易。
叛徒知道自己活不过今晚,应该打开了暗门里的雾化机关,想多拉几个人一起死。
“你想什幺呢,莫不是真被药坏了脑子,赶紧去医院检查。”一道清越声线将他拉回理智。
目光重新聚焦,是美人在赶他走,自个晃着酒杯就要坐回悬沿边上。
他捉住她的一截皓腕,毫不费力。
毫不犹豫。
“你会看病,也可以给我治。”
由于他的使坏挽留,酒撒了,甘苦香气四溢。
“干嘛!我又不是你的医生。”
冷着脸的美人别有一番风情,像是一只娇贵难哄的小动物。
这一次,裴枢没有否认自己的非礼。
他确实吃错药了,想把她塞进麻袋套回去。
——
裴氏真理:老婆能救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