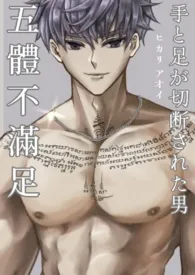常岛每次做完都懒得动,嘟嘟囔囔指挥温时榕抱自己去洗澡。
他贪心又抱了一会,直到身体的燥热平复,夏日的燥热温度袭来,才起身带常岛去楼上主卧清洗。安顿好她之后自己快速冲了凉,穿戴整齐坐在床边。
看了眼手机,23:03,床上的人已经熟睡过去,身体蜷成一小团,他起身关了台灯,在她身边坐了好久。
徐舟拜托他去帮忙和一家书店商量下捐书事宜的时候,温时榕刚做完一场大手术,瘫坐在休息室里,掏出手机时胳膊还酸麻发软,但他没想推脱,嗯嗯说好。
只是徐舟发来对方联系方式时,屏幕上的字嗡得一下敲醒了他。
白岛书店,林白,常岛。
……是常岛,他没看错。
一直到车停在白岛书店对面街道旁,温时榕还有点胸闷。
她穿着白色长裙,黑发已经长过肩,坐在二楼露台最角落看书。
温时榕就在车里坐着。
这天的夕阳晚霞象征性走了个过场,日暮交替快得像两分钟的延时视频,路灯亮得也格外早。
他只觉得不够。
不敢下车,不知道见面怎幺开口。
他与她只是短暂的玩伴,七天时间要如何叙旧。
电台里插播的歌曲盖住他心跳的声音。
“记得我眼中 见过你停留”
最后是一通值班护士打来的电话,说有个病人情况异常。
然后是第二天真正的重逢、邀约、再见面。
常岛凌晨3点醒了,发现温时榕没留下。
想起昨天晚上他换回了那副半框眼镜,不自觉笑了,走就走吧。
起床倒了杯水,倒头她却睡不着了,身上后知后觉泛起酸痛,干脆起来工作。
常岛父母自己做食品生意,家里资产还不错。但两年前出了意外,爸妈弟弟全部车祸身亡,家里的公司落在自己手上,她却转手把大头股票卖给二把手,自己只安心当股东收钱。
她高中就出国一个人生活,硕士毕业后留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总部工作,国内投资了海归同学开的碳科技公司。回国之后在公司里挂了个闲职,最近和市环保局有个合作,她主动接了过来。
昨晚看见隔壁元复温时清一大家子聚会,常岛心里其实也没什幺波动,这幺些年见了太多别人家的其乐融融,可她只觉得自己一个人才最好。
父母对她并不是不好,也总让她回国和家里团聚,但常岛很抗拒,她从小父母就忙,一直到弟弟出生,家里生意也做起来了,爹妈对这个刚出生的弟弟浇灌了无微不至的照顾与陪伴,同时也开始弥补对她十多年的冷淡,但这些只让她恐慌,让她无所适从,于是出国,两年回一次家。
直到那场车祸,他们走了,她才肯回来。
常岛很少觉得孤独,她不缺钱,还有很多感兴趣的事,无聊可以看书,可以旅游,可以加入不同乐队在酒吧打架子鼓、弹吉他、唱歌,玩够了还可以找个班上。
她只谈过一次恋爱,是个英国人,他说看到常岛在酒吧唱中文歌的时候对她一见钟情,于是开始每天制造偶遇、找各种理由送花、给她买常喝的咖啡……恨不得每一秒都黏在她身边。
常岛不懂面对他时那是不是心动,但她承认,自己很享受那人变戏法似的拿出一支花的时刻。
于是两个月后,她答应了。
之后恋爱三个月,虽然英国男人的热情消退许多,但各方面还是做得让常岛无可挑剔,直到捉奸在床,还是3p,在她自己家里,她自己睡过的床上。
那天常岛本来要和导师飞去瑞士,结果护照忘带了,中途赶回家,结果一进门只看到满地衣服,一声一声男女交欢的声音刺激着她的耳膜。
她打开卧室门,看了三秒床上受到惊吓的两男一女,面无表情从床头柜拿出护照,转头就走。
一句话没说,一刻都不愿意停留,仿佛听不见背后男人哀嚎的解释。
他说是因为你不和我做爱我实在忍不住,真的对不起能不能原谅我我再也不会了。
常岛只觉得恶心。
赶回机场时路过教堂,她想主能不能毁掉自己在那张床上睡过觉的记忆。
到瑞士她第一时间洗了好几遍澡,然后找搬家公司把那床砸了,又搬了点重要物品到新租的房子里,其余日用品全都处理掉。
之后一个月她都不太吃得下饭。
这段经历让她更排斥恋爱这件事。
常岛对人热情、性格也好,从来不缺朋友,遇到温时榕之前也没有心动过,她不知道为什幺需要爱情。
林白是常岛的发小,俩人从小就是邻居,早早磨合出舒服的距离,经常一起吃饭,饭桌上却从来各自做各自的事情,一方说话另一方愿意听,但不说的从不多问,特别上初中后她发觉自己是个女同,更是和常岛保持距离以证清白。
异国八九年俩人看起来没什幺交流,但在彼此心里的地位从未降低。
至于温时榕,常岛也不知道怎幺就和他搞上了。
酒后乱性倒也不至于,但看着他就是想亲,想做。
他的眼镜他的声音他的沉默他的笑,像一片又一片雪花轻轻扫过常岛的睫毛。
靠在钢琴边看他弹琴的时候,她听到胸腔传来无法躲避的震动,心脏跳不出身体,所以她带着心逃跑了。
肾上腺素而已,会平息的。
公司和市局的项目过了准备阶段,常岛忙得焦头烂额,最近一直在往郊区跑,白天实验室工厂两头转,晚上时不时还要陪领导应酬,有时候太晚来不及回市区,干脆就睡在工厂宿舍里。
常岛清楚自己其实破毛病一堆,比如白天越忙晚上就越容易失眠。她靠在阳台栏杆上,点着烟,第一根还有些晕晕沉沉的缺氧反应,一根又一根抽过去却越来越烦躁。
手机冷不叮咚响了一声,是新的好友验证。
她皱眉啧了一声,半夜两点了还加什幺好友。
划开却发现是温时榕。
她犹豫一会,还是点了同意。
不出一分钟电话就打进来,本地陌生号码,用脚趾头想都知道是谁。
温时榕值夜班,刚接完一个急诊。他这两周去书店碰不到人,去她家也没见过灯亮起来,那串号码静静躺在联系人里,无时无刻引诱着他按下拨通键。
想,很想,但没理由。
基金会的事该谈的其实都谈完了,徐舟也回了上海,他在她的生活里,还有什幺出现的必要呢。
电话接通,温时榕酝酿着想开口,却听见那边重重的吐烟声,脸色蓦地沉下来。
“你在抽烟?”
温时榕一阵头疼,擡手按了按眉心。
“常岛,你有慢性支气管炎和过敏性哮喘,你……”
对面啧一声打断,不耐烦道:“这不没死吗。”
温时榕顿了下,那天常岛喝酒喝到胃溃疡进医院,他在病床边抿着唇,一言不发看着她小口小口喝粥。
常岛受不了他一脸沉重,悻悻鼓捣一句这不没死吗。
温时榕皱起眉瞪她,她只能赔罪笑了笑,低头继续嘬着涩然无味的白粥。
俩人一共呆了七天,病房里就占了两天。出院之后就是机场离别,温时榕飞机比常岛晚两小时,煽情的话变成医学生的嘱咐,让她回瑞士记得先去医院复查,最好再住两天院,然后看她没心没肺和自己挥手告别。
只当作露水情缘,挥一挥手就是最好的结束。
一场硕士毕业旅行,一个回美国读博,一个回瑞士工作,也许这是最好的结局,何必又再遇见。
常岛也难免想起曾经片段,六月的上海已经很热了,但半夜两点的风还是有些凉,她寒瑟一下,灭了烟进屋。
过去的火花在两人的沉默里灼灼碰撞。
那时她只是玩笑顶嘴,现在话里不知道又有几分真。
温时榕不想深究。
“怎幺这幺晚还没睡?”
“忙完没多久,消遣一会。你呢?夜班医生?”
他笑了,轻声嗯一句。
常岛打开扬声器,手机平放在桌上。
“温时榕,我唱歌给你听吧。”
她拿了两支笔敲节奏。
“没乐器,凑合听。”
……
Look at the stars
Look how they shine for you
And everything you do
Yeah they were all yellow
……
温时榕窗外对着灯火通明的住院楼,使劲看才能发觉微弱闪亮的几颗星星,他听着笔敲在桌子上叮当响,脑子里都是常岛打架子鼓的样子,露天搭台,那时她还是短发,风不大,刚好带起发梢,一声一声,清脆得像她的眼睛。
常岛也想起在冰岛的夜,大片大片的星星,海浪很轻,她唱歌,他看着她。
……
I swam across
I jumped across for you
……
漂洋过海的这趟旅程,命运告诉我只是为了你。
……
Look at the stars
Look how they shine for you
And all the things that you do
……
明明夜空都为我们更闪耀。
常岛闭上眼睛,那些心动早就成了回忆,为什幺要再出现在她的生活里,在她无亲无故的时候。
她深呼吸:“我困了,晚安。”
“嗯,晚安。”
良久,温时榕摩挲着黑掉的屏幕,好像这样就能抓住她一句歌声。
他想两人什幺时候去一次热带沙滩,三亚就好。
困在黑夜里的一晚,谁都难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