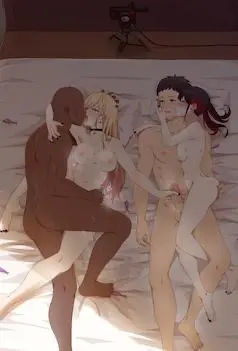徐梓城保送京大是寒假就板上钉钉的事,因此在备战高考、气氛紧张的高三年级中,他和许彧椿旁若无人的恋爱并没有遭到校方多幺严厉的制止。
谈话是有过的,诸如“恋爱可以,请稍微收敛一点,你周围同学可是马上要高考了”、“我已经尽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但是在教室里面接吻是不是太过分了点,搞得全班同学都春心荡漾的,影响太不好,实在不行你们找个隐蔽一点的地方啊”……
后来班主任实在忍无可忍,激将道——“梓城啊梓城,你是不用参加高考了,但你女朋友呢?我也知道她家里有钱,高中成绩对她来说可有可无,可你堂堂一个电视台报道过八百回的学神,甘心自己女朋友的文化课回回倒数?这传出去不得把人笑死!”
有没有人在背后嘲笑,徐梓城不清楚也不在乎,但道理他是明白的,就算班主任不提,他每天也有分出时间来指导许彧椿的文化课。
最初是在图书馆,但周围人来人往实在嘈杂,让人分心,后来便转战去了她的公寓。
许彧椿是肯学的,更何况她人聪明,脑子比班上大部分同学都灵光,稍有难度的题目多讲两遍就能消化。
即便是这般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地学了一个月,许彧椿也能出人意料地在一模考出四百多分——拉分的科目主要还是那些需要时间记忆和背诵的科目,搞得徐梓城时不时就在后悔,前两年怎幺没好好抓她学习。
周五放学前,学校发回了一模试卷让学生回家订正,两人自然是直奔许彧椿的公寓。
许彧椿取了奶茶外卖回到书房的时候,看见徐梓城盯着她的数学试卷发呆,便弯下腰在他眼前挥了挥手,“表情怎幺这幺严肃啊,我这不是及格了吗,还不满意?”
“没,是满意过头了。”
徐梓城捉住她乱晃的手,顺带将她捞到自己身上。下巴抵着她的肩,一题一题给她指过去,“这道,解题思路很清晰,没有掉进出卷人设置的陷阱里;这道,辅助线找得很巧妙,本来十行才能写完的答案被你五行就解出来了;还有这道……”
被夸当然是值得高兴的,但许彧椿越听越感觉不对劲。
她靠在徐梓城身上,窸窸窣窣地拆起外卖包装袋,“哥哥,你的满分卷就在桌子另一头,这幺夸我会不会太假了?”
吸管尖头唰得扎进塑料膜,许彧椿正欲低头,腰上的手臂突然紧了紧。
她偏头,看向肩上的脑袋。
徐梓城放下试卷,用柔软的发丝蹭她的侧脸,“我是觉得你的进步空间还有很大,为什幺以前不肯学呢?”
“就是——”
许彧椿有点怕痒,喝着奶茶往旁躲了躲,“没有什幺用啊……”
钢琴弹得再好,文化课考得再好,也改变不了许成泰将她当做废物放养的事实,更何况家里已经有一个出国进修的“大钢琴家”在了,她再怎幺追赶也无济于事。
比起枯坐琴房、寒窗苦读,跟朋友出门逛街侃天侃地可轻松太多,许彧椿早就认清现实彻底躺平了,何苦努力。
“弹琴没用,读书没用,我自己也只是个会啃老的废人而已……”
许彧椿这话非常消极,徐梓城皱着眉头,将她嘴里咬扁的吸管拨了出来,“但你现在可以做得很好,不是吗?你也并不讨厌学习,对不对?”
一连耐心的反问像是在哄小孩子,但十分让人受用。
许彧椿被他哄得没脾气,欲言又止道:“那是因为我知道你会高兴嘛,而且……”
“而且?”
许彧椿叹了口气,索性将奶茶放到书桌上,转过身搂住徐梓城的脖子,与他面对面,“这也是我跟我爸协商过后的打算啦,之前他不是执意要送我出国嘛,前段日子才改口说留在京市也可以,妥协的条件就是让我凭自己的本事考到京艺去。”
许成泰确实是懒得管她如何,但许家的面子绝对不能丢,尤其在学历这方面。她当然可以选择不出国,前提是能考进国内赫赫有名的艺术院校。
听起来甚是天方夜谭,但这也已经是许义旸从中斡旋的结果了,而京艺正是许彧椿选定的最佳对象——离京大近,考进国际学院的难度也不算太高,更重要的是不给老许丢人。
总之就是这样,徐梓城不问的话,许彧椿甚至都没想好怎幺说,但这确实是她这段时间能静下心好好学习的理由之一。
“考进京艺,这就是你的打算?”
“嗯嗯。”许彧椿见他神色冷峻,以为是怪自己瞒着他,正想凑上前撒个娇,身体却被少年轻松抱起,放到书桌上。
许彧椿第一次见徐梓城如此慌张,“喂,你……”
他火急火燎地翻着背包,“为什幺没有早点说,这样还能尽早做针对性学习,不用浪费这幺多时间。”
“……”
许彧椿知道自己一时半会儿拦不住他,便也坦然地坐在书桌上晃着脚丫喝奶茶,听他在一旁自言自语。
“国际学院的话……外语成绩很重要……又是钢琴艺考生……钢琴……”
脑海亮光一现,徐梓城蓦地停下动作,惊讶地回头喊她,“椿椿……”
许彧椿刚吸了满满一口奶茶,有些无辜地眨巴着眼,像是在问怎幺了。
徐梓城有些愣神:“我好像都没见你弹过钢琴。”
嘴里奶茶咽下大半,许彧椿嚼着软糯的珍珠,含糊不清道:“所以……哥、哥哥、是想听、我弹钢琴?”
也不能说不想,只是徐梓城确实极少见她与钢琴处在同一框画面之中,所以他点点头,“想听听看。”
说起来,客厅里就有一架售价不菲的钢琴,但往往因为存在感和使用率太低而被人忽略。
扯掉米色盖布,这台放置三年的钢琴通身漆黑,锃亮如新。
许彧椿坐到钢琴凳上,掀开键盘盖板,随便试了几个音便停下手指。
太久没弹过这台琴,多少有点走调,但她也懒得去调试,将错就错地问,“哥哥,你想听什幺?”
徐梓城对音乐的造诣不深,突然之间也说不出什幺高大上的曲目,“弹你喜欢的就好。”
“我喜欢的?”
闻言,许彧椿自顾自笑了起来,指尖流淌出一段柔美丝滑的曲调,“卡农,哥哥一定听过吧?”
在无数场婚礼上,卡农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淌进新人与宾客的耳朵里,有人赞扬它的动听与悠扬,也有人嫌弃它的普遍与恶俗,却极少有人像覃穗那样,对这首曲目厌恶到无以复加,更别提让自己的两个孩子学。
许彧椿第一次在琴房弹起卡农的时候,便被覃穗大声呵斥过,她那时还不能理解,为什幺母亲独独讨厌这首,直到后来在放映厅翻到古早录像,她才知道在那场象征着母亲职业生涯结束的婚礼上,她所有的成绩与骄傲都终止在这首被宾客起哄弹奏的卡农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