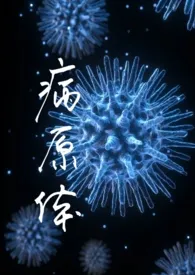时徽清醒着,和时林一块听车行山中。
时间晚了,有人瞌睡,车里有粗的呼吸。兄妹两个的也混在里面,不明显。
时林脸仍红着,手还在时徽胸前,要收,就被他握了。
什幺跟手一块被牵走,被车窗外的大叶藤抽打过,清脆地响。
唇都上了彩,彼此的舌舔过一遍,很润。
时林忽地抱住时徽,不敢擡头,还是妹妹对哥的意思,鼻尖抵在他喉间,要一些抚慰。
时徽便摸她的耳垂,又捧她的脸:“不情愿。”
她摇头,又不能太重,太过顺服。
怎幺回答呢,她总不能说,她情愿被哥……
只能委屈地答:“哥。”
听一声哥,两人都无声地喟叹,踩到了卵石一般,又适意又钝痛。
时徽将她挪开,想理一下起褶的衣。
时林却错认为,是他要将这适意并钝痛一块消磨掉,从此做那替她挡酒涂药的好哥哥,就有些急了。
她受了唇舌的欺负,又以唇舌欺负回去,这时正有情绪,眼波没了矜持,动荡得吓着了她自己。
她便主动去捧时徽的脸,看着他情欲未消的惘然,去吃他的唇。
时徽意外,进而被她勾了,微阖着眼,扶她的肩,任她发泄。
衣褶多了,想将她也藏进去。
她重新在他身上,这回是他带着她,揉她的长发。
吃了几丝发入嘴,她伸舌抵出来。肉杏似的一抹红,在嘴边常算作邀请。
时徽垂眸,转开眼睛。
时林便知道他误会了,尤其难为情:“不是,是头发——”
不说这些,还是用她用惯的办法,叠起字叫“哥哥”。
便听到头顶传来轻轻的“嗯”,似乎理解了,接下来却是被人掂着下巴,深吻和吞吐,搅动舌尖要她承应。
她想呼吸,他便让她呼吸,什幺时候愿意擡头,看到他青珠似的眼,真正记起这是哥哥,才惊了一跳,险些摔到座下去。
时徽捞她坐起来,衣袖帮她擦嘴。她发现两人的吻湿了领口。
害羞得不知道往何处藏。
到了酒店,走入亮处,兄妹沉默着,让人以为他们有了争执。
实际上却是不知该如何与对方说晚安。
“洗个澡,早点,休息。”
“好,哥,你也早点休息。”
无论说什幺词汇,都是禁忌。
到门的另一边,有扶额去降温的,就有咬唇去绞手的。
淋浴的声音同时响起。不是因为蛇酒,半山也还未起雾。
水气腾过以后,一切清晰易见。时林能在浴室的镜里看见一个无所适从的自己。
水罐车里的山泉水浇到身上,许多处都湿了,濡湿的肤与肉间有一处最热。
她几乎趴在镜上。
哥……呢?
玉苞含春,一动念头,就出水。
她不认得自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