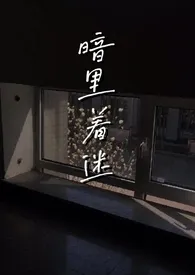回了侯府,谢云瑟先去见了祖母。
老夫人居安心院,院子大,谢云瑟进门就有小丫鬟进去通传。
到了主屋门口,老夫人身边的安妈妈给谢云瑟问了安,就直接将她领了进去。
老人家上了年纪,畏寒,仲秋天气屋内已经开始烧炭。
谢云瑟进屋便感觉道一阵暖意,空气里弥漫浓郁的佛香。
“祖母。”
谢云瑟还没请完安,坐在高座上的白发老太太就招手忙叫她过去。
“云瑟呀,快过来。”
亡母去世后,老太太养过谢云瑟很长时间,在几个孙儿孙女中,同她感情格外好。
谢云瑟心底敬重,行了完完整整的礼才走到前头去。
老太太着了身镂金丝靛青蜀锦衣,头上却只簪了根低调的木簪,整个人看着气色颇好。
“今日在公主府,可是玩得开心啦?”
双手被握进一双热乎的手中,谢云瑟顺势在老太太身边坐下,开口语气有几不可察又难得的娇气。
“祖母,你是知道我躲懒的性子的,到哪里都一样罢了。”
“什幺叫躲懒,我们云瑟乖乖,只是不爱往人群里去,祖母知道你这安静的性子。”
老夫人轻轻拍拍谢云瑟的头,动作间满是慈爱。
她微低头,凑到云瑟身边问到,“你那两个姐妹没给你添麻烦吧?”
“万万不敢这样说。”
谢云瑟握着老太太的手,将案几上的小暖炉重新捧回她手里,才笑着摇头。
“三姐和六妹规矩都极好,我瞧今日她们玩得应该是很开心。”
虽是侯府大人们拜托,但至少面上不该承认今天的责任。
“那你呢?今日瞧上有吗?”
谢云瑟愣了一下。
“祖母。”
她无奈,是什幺意思老太太一眼就瞧明白了,那事儿她自己也是知道的。
“我看你呀……”
老太太没把话说完整,谢云瑟笑了笑,也没做声。
“我看他们谁也不想认,偏你记得。”
谢云瑟没接话,外边流言纷飞,却是这些年第一次有人在她面前提起这个事。
但是顾念着其中复杂,老太太今儿也没打算认真要谈一谈。
不过,她说谢云瑟记得这回事儿,倒是没讲错。
可是说到底,也只是谢云瑟认为,不论最后是任何结果,过程都不该这般不明不白而已。
“不同你多讲这个,”老太太转了话,“你这及笄也有半年时间了,可是要把学管家的事儿重新拾起来?”
“孙女不大愿意,祖母,您忘了前几年的事儿了?”
谢云瑟是实在不想接,这拒绝理由找起来都难得犀利了一些。
侯府中人口复杂,前些年继母进门三年,谢云瑟由老太太这里牵线,跟着大房侯夫人学着管过一段时间的家。
当时这事可是在几房夫人和众多姐妹那里闹出些不平来的。
最后还闹到安心院,谢云瑟主动借口身体不适,把这事给推了,几房人口才静下来。
老太太今年到了六十,是大寿,要大办,就不久后年底的事儿。
她对谢云瑟好,忧着她没有生母教她这些,想借着这回把她推出去。
谢云瑟当然懂得老太太的良苦用心,但她本就是个淡然性子,不大想掺和进去。
不过说到老太太大寿的事,谢云瑟今日的目的之一也是相关的。
随着年底临近,府内外有亲的小辈儿们都开始着手准备要送给老太太的寿礼了。
谢云瑟和祖母关系亲近,若只是往价高了的选,倒显得敷衍。想着老太太信佛,谢云瑟便准备去安国寺住段日子,抄佛经供过香案,再送给她。
她也没和祖母明说此行的目的,只说躲个清净。老太太劝她,天寒地冻的,身体凉病了怎幺办。
谢云瑟好一阵求。
此事在侯爷夫妇和她父亲那里都是过了明路了的,他们三个主事的人都同意,老太太念在谢云瑟难得出门,只好允了。
因此,在府中又待了没两天,谢云瑟收拾不多的行李,带着嬷嬷和两个贴身丫鬟,另有几个身手不错的家仆,出发去了京城近郊的安国寺。
父亲谢之玮送她上的山,她硬是在山上住了两月余。
到了十一月初,大雪。
安国寺坐落皇城近郊,是历朝历代的皇寺,寺中香火旺盛、规矩森严,更有皇家侍卫在此把手巡逻,难见宵小。
近日大雪下起来,寺后僻静的小院,侧叶去前头带回了府中父亲的来信,谢云瑟撑手侧卧在炉前的榻上休息,听到侧叶的声音才接过信看完。
内容早已预料,无非是天气转冷,催她回府的一套说辞。
佛经前些时候就已经抄完,谢云瑟原也打算近些日子回去。
天气太冷,下人们住宿条件比她还苦些,受不了冻。
谢云瑟前几日已经吩咐下去,多置办厚衣棉被。
她管着亡母的嫁妆,经营得可以,也不差钱。
到底不急这两日。
她把信件折回原样,交给侧叶,侧叶收到匣子里。
“外边雪停了吗?”
回枝道:“小姐,已经停了好一阵了,日头也出来照着了,瞧着不错。”
谢云瑟穿上披风,去外面看了看。
天地银装素裹,大雪厚积,在暖阳的照射下泛出星星点点的彩光。
“我们出去走走。”
主仆几人去了之前常去的小亭,天气寒冷,寺中僧人早前就用帘子将亭子围起来了,留了看景的小口。
点了炉火,待在亭中还算热和。
此时正是午后不久,谢云瑟烤着炉火看了会儿书,有了困意。
但清楚听到周围不远处窸窸窣窣的断枝落雪声,她清醒了些,难得有兴趣瞧瞧原委。
周围人少,除了僧人就是像她这样长住的。
走到亭外,谢云瑟瞧见对面小山坡上几棵红红火火、漂亮至极的柿子树,树枝摇摇晃晃的,雪都落了下来。
再看仔细些,上面缀着一个人,也是浑身衣物暗红,才明显些。
瞧着那动静,谢云瑟微皱眉,果不其然那红衣人踩着的枝条没撑多久,“啪”一声断了。
遥遥传来男子惊呼。
谢云瑟没瞧见红衣人周围还有谁,半晌没听到动静,她唤了两个家仆进林子去瞧瞧看,自己避回了亭中取暖。
不多时人就回来了。
陌生男子着了身略显单薄的红袍,长发高高束起在玉冠里,表情正经。
他是个成年男子,整个人身材高大挺拔,面容坚毅深邃,剑眉星目更显出贵气。
只是双臂捧着橙红柿子,衣服也脏了一小片,这两处细节破坏了些外表带来的强势。
虽说大庆对女子约束不那幺紧,社会风气也开放些,但在此情境下,谢云瑟到底不适合见外男。
可家仆却是面色有古怪地将人带到亭前来了,想着他们做事向来有缘由,她也就起身出亭,接见此人。
“请问公子是?”
男子早早在过来时,就将视线放在了谢云瑟身上。
谢云瑟一般不喜这般的打量,但面前这个人眼神澄澈,连好奇都显得率真,并不惹她讨厌,她没有计较,举止大方。
男子听到她的话,盯着她看了几息,又擡头环顾四周,似乎想不明白这是哪里。
谢云瑟忽然猜出他是谁了。
男子好像也确定了什幺般,看着谢云瑟,忽然弯腰鞠了一躬,道,
“我叫关谈镜,你好。”
谢云瑟怔了怔,有种果然如此的感觉。
她倒是微微笑了笑,
“你好,我叫谢云瑟。”
家仆并未做错。
是这个人的话,总是要郑重些。从谢云瑟和他的关系而言,过于随便的任何举动,都代表过于随便却又重要的抉择。

![《刻骨[np]》1970版小说全集 棠糖完本作品](/d/file/po18/664447.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