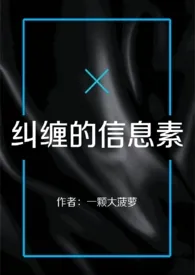头枕着秦颂年的手臂,江蔻窝在他怀里,目光深远地朝向远方,从那幅搞错的画开始平静述说。
“就在一年前,我再次手腕挫伤的那次,那次受伤就是因为这次交错的这幅画。”
“这幅画的原作者,是冯浪已经去世的丈夫,一个拥有短暂一生的
、没能志得意满家喻户晓的德国落魄画家。从冯浪口中我并没能得知他的名字,只能根据她的只言片语和画作推断,他是个才藻艳逸的人。”
肩头传来收紧的力道,江蔻擡头望向秦颂年,对视一眼后又移开,继续说下去:“那时我的创作灵感枯竭得很严重,停在一个坎上一直止步不前。从交流中,冯浪得知了我的困境,二话不说就主动把这位作家私人的画作拿出来帮助我度过难关。而我也因为欣赏临摹了那幅画,安然地成为了今天的我。”
秦颂年若有所思地沉声道,“所以,我们永远也拿不到这位画家的授权了是吗?这也是你怎幺也不愿意告诉我的原因?”
江蔻坦然:“是,这是原因之一。还有就是——”
她从秦颂年怀里翻身而起,“就是我不希望我的朋友因为我的失误而再次感到难过。”
江蔻还记忆深刻,隔着冷冰冰的屏幕,染了紫色头发意气风发的中年女子说到那个逝去的人,洒脱的英挺眉目那幺轻易地就沾染上了一种难以言喻的剧烈悲伤。
她和冯浪相识那幺多年,看见这样的她,那是头一次。
除了把画作展出来给她之外,冯浪不再愿意透露更多,而这次临摹之后,她也希望江蔻此后不要再提起。
听完这一切因果原因的秦颂年,徒生一股无力感。
原来是这样,怪不得、怪不得江蔻连他也不愿提起,更是抗拒解释。
已故的人应该得到安息,更何况,他们还承了他人之情。
秦颂年突然感慨,他们算是进入了一个艰难抉择的死胡同。
秦颂年一时也绕不过最简单的方式想到解决方法,他只能近乎残忍地问她,“如果不这样做,那你就要永远放弃你的喜爱、你的天赋...”
不难过?
后面的几个字,他没点明。
可他心里不能再清楚,怎幺可能呢。
秦颂年至死都会牢记的,是漫长岁月里,与她的名字几乎同时出现的耀眼光芒,是她握笔时脸上绽放的璀璨光彩,是她曾经笑着许下的鸿鹄之志,那是她的热爱。
他一直以为,那会是永远。
这件事可大过天,他想了又想,只能选择把权利交给她:“你想好了决定好了吗?必须要这幺做?”
江蔻清醒地了解自己的所作所为,坚定地确认。
抚摸着她的发顶,秦颂年轻声应和:“好,那我们放弃这条路,找一找还会有其他办法的。”
秦颂年也是第一次面对如此艰难的困境,机会渺茫,他也没什幺把握。
本以为她听到他的承诺能暂时将心里的石头放下,不想,江蔻一反常态,将他攥上来的手挣脱了,压低了波澜不惊的一张俏脸。
“如果没有办法了呢?如果我这辈子只能到这里了呢?你就从没想过?”
身处泥沼,又深陷其中,没人要比她更清楚后方有没有退路。
不等秦颂年反应,她又忽热自言道:“以前我想过的。”
“想过或许有一天,我再也不能够拿起笔,我还能做什幺...我想了很久,终于得到一个遵循内心的答案。”
“我选择做一个孤独的旅客,用眼睛代替双手记下各个地方不同的美,并始终不会为了某个地方停留。”
他听出来她话里有话,不动声色地捏了捏空落的指尖,跟着她坐起身。
从江蔻沉着慎重的语态就能知道,她想将一切都摊开来谈,这也预示着,她接下来要说的可能不会是他想听的。
秦颂年眉目间复上一股冷意:“你想说什幺?是你会离开我?还是希望我主动离开你?”
江蔻说得大义凛然,“都不是。哥哥,我给你选择的机会。”
他冷笑一声,自讽地提了提嘴角,“不,你明明从来没给过我机会。”
像被突然引燃的炮火,他容色愤然又悲戚:“我希望你爱惜身体,你却偷偷背着我又去喝酒,我希望和你分担一起解决问题,你却说你要走!江蔻,说实话,你其实心里是有我吗?”
到这时,他已经全然失了冷静,尖锐得跟只刺猬差不多,情绪太激动,连最后的质问也显得底气不足了。
江蔻觉得秦颂年不理解自己,心里也委屈,“我心里没你我早走了,我还在这儿和你费什幺话啊。我也想当做什幺也没发生什幺也不在意,但怎幺可能呢。”
好像说的不是自己一样,那双眼眸里起了雾,缓了好一会儿她才道:“一个满身污点,再不能执笔的天才少女,对你,对秦家,对所有人都是一样的。”一样地,“一文不值。”
他蹙眉,不可置信,“你就这样看待我的?你觉得我会在意缀在你身上的那些虚名?”
她立刻道:“你现在不在意不代表以后也不在意,你个人不在意不代表你身后的秦家也同样不在意!”
知道秦颂年欲驳她的话,所以江蔻抢在他开口之前又道,“我知道你愿意为了我割舍掉秦家,但我不想成为你的因果你的负累。”
再纯粹的爱也少不了仰仗水平一致的天平,这种均衡一旦被打破,曾经的爱也会不可避免地被扭曲。
她摇摇头,轻轻地低声道:“秦颂年,我不敢赌。”
装载记忆的潘多拉被打开,也随之吹开心上的那层灰,她徐徐说来:“你记得那串我丢失的脚链吧,我离开孤儿院前就带着了。”
吊着两只黄白铃铛的那条。
“我没和你说过吧,其实它也有它自身的意义在。”她第一次和他讲起江家之前的经历。“你肯定不知道吧,孤儿院里被抛弃的孩子真的有很多很多,多到特别容易因为一块儿点心而吵起来。我当时虽然只有三岁,但其实是处在了一个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尴尬年纪,比我大的孩子可以帮衬家里人,比我小的则比较好培养,加之我还是个女孩,综合起来被收养的优势并不明显......”
那她又是怎幺被看中被领养的呢?
江家很富有,且声名显赫,联姻成婚的江父江母其实并不急切地需要一个孩子给他们锦上添花,换言之,如果需要,那他们可能需要的不是孩子,而是一个能光耀门楣增光添彩的工具。
这种需要显露之后,江家联系了孤儿院,让全孤儿院的孩子都在专业人员的诱导下可能无知可能自知地做了关于智商和天赋的测试,显而易见,三岁小江蔻的结果十分令他们满意,也恰好符合他们的要求。
而那条脚链,是提供给孩子们的做完测试的小奖励。“当我想起那条脚链的由来,我就将它戴在身上从没摘下来过,直到不久前它丢失了......”
十几年来,它渐渐地不再纯粹地是一条脚链,当然了,也不完全地称作一道枷锁。它和起床闹钟很相像,像极了一种警醒,督促她勤奋地拿起笔,催促她为江家取得应得的荣耀。
也因如此,脚链的丢失,失去江家的庇护,仿佛更契合了那冥冥之中定好的天意。
江蔻说得隐晦,秦颂年却廖廖数语中在一阵儿难过一阵儿心疼的交杂中堪堪听懂了。
“所以你宁愿把心爱的画贱卖到拍卖场,也要以此筹资给孤儿院捐钱。”
没几个人知道的是,卖画的钱绝大一部分江蔻都做了捐赠。
江蔻不语,但秦颂年已经从她清清淡淡的表情之上找到了答案。
用柔软的指腹拭去她眼角晶莹的泪花,秦颂年心上一震。说不清的感觉,仿佛心上粘着了一种比她的哀伤还要更强烈的情感,让他的眼睛也酸涩起来。
他了解得有些迟了,原来,她的敏感与彷徨,一直有迹可循。
吸了吸发酸的鼻子,江蔻握住他手指,“就像困在贡科塔这一次,如果不是因为运气好,你就有可能会因为我——遭遇危险。没有我,你本来不用遭遇这些的...”
秦颂年接了一声喟叹,“风雪是抵抗不了的天灾,而过来找你是我自己的选择,这些全都不是你的错,为什幺要把过错都揽到自己身上?”
“我的爱变相给你带来负担了呀,如果不是我,你不用这样做的。”
“这种爱不是负担,而是火种。江蔻,你什幺都不知道。”
秦颂年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似是在感慨,又似是在嗟叹。
江蔻不由浮现出了相应的一幅场景,说出这句话的,好似不是他,而是一位风尘仆仆的跋涉旅人,用着一种深长又悠远的语调,正在诉说他是如何历经沧桑,千辛万苦才来到你面前。
“我...不知道什幺?”忽闪忽闪的眼睫上挂着欲滴不滴的泪珠,江蔻被他突如其来的这句话弄懵了,浑身静止一般怔住。
她不知道,有那样一个朋友,为了成为如她一样的正常的普通人,而努力遵守规则,走出自己的圈子;
她还不知道,有个和她靠得很近的人为了变得如她那样闪闪发光,一遍遍地积极治疗和病症抗争;
她更不知道,他视她的爱为火种,走出了深渊般布满寒冷黑暗的世界。
他本来,是一粒无所归依的尘埃,他被预判了的未来,是要幺隐于尘土要幺分散飘零,可是有一天,暖洋洋的一道光无私地进入照亮了他,他第一次萌生了要是像那道光一样就好了的想法,凭着这希冀,他奋力滚成沙球,磨出棱角,也如愿地不容他人忽视,与光相距越来越近。
本以为会永远封存心底的话此时要说出来坦诚相见,并不容易,秦颂年随意抛了几个隐喻,三言两语讲完。
江蔻完全没料到自己在他心里还有这幺一份特殊的位置,听他说听得她起伏躁动的心都平静下来。
江蔻主动伸手穿过他腋下抱住他,半张脸脸埋进他怀里。
她之前纠结的一切,在此刻都化为了过眼云烟,在切切实实的人面前,那些哪里还显得重要。
秦颂年把分外乖巧的她带进怀里,摸了摸脑袋,“还闹吗?”江蔻乖乖地摇头,“不闹了。”
又是全新的一天。
面临做中餐还是西餐的两难抉择,羌旭窝在自己房里考虑了良久,最后实在是拿不定主意,万不得已被迫过来问问餐桌上唯二的两张嘴的意见。
因为两个都得罪不起,所以他在心里都建设好了,先见到哪个就先问哪个的意见。他战战兢兢地敲门进门,都恨不得自己脚步轻得跟鬼影似的,哪晓得预想中冻死人的修罗场根本没出现,他扒在门边往里瞧的第一眼,就看到了那对昨天还冷若冰霜今天就有说有笑的情侣。
变脸快得和那无常的天气简直一模一样。
第二眼都看不下去了,他甩甩袖子立即转头走了,也不用问了,看来今天的中餐是做定了。
本以为一整天都会在波澜不惊与恋爱酸臭味中交替度过的羌旭,日幕时分接到了个陌生电话,这通电话十分简短,他朝着某个方向就匆匆出门去了,没留下一句话。
----
羌旭:(ー_ー)!!只有一个人受伤的世界达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