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厅的灯火都熄了,只留一盏走廊上的声控灯。陈已秋刚从浴室踏出来,漆黑一片的长廊突然灯火通明。
毛巾搭在脑袋上,底下的长发即使被拧干了依旧在滴着水。水珠落到木质地板上,变成一颗透明的水晶体,透射出地板的高级木色调,湿哒哒的。
浴室对面就是她先前在这里借住的睡房——将杂物暂时清空到常予盛的书房,再添了张单人床。当时布置得有点匆忙,房里还有常予盛的书架和一些大大个的纸皮箱。
她还记得搬进来的第一天是睡的地铺,第二天一早常予盛就去宜家擡了床架回来组装。她说没必要,也就只是暂住(当时想着能住多久就多久),可常予盛坚决不让小姑娘睡地板。其实他新买的床垫很厚又硬,她觉得直接放在地上也没什幺问题。
但当时常予盛从满堆螺丝和拆得乱七八糟的纸皮塑料袋中擡起布满细密汗珠的俊脸,说,就算你只来一两天,我也要把你照顾好。
从此他的屋里多了一张粉色的单人床架,渐渐又多了一套粉色的床单被褥,白色的窗帘,鹅黄色的地毯,清空了四分之一的大纸皮箱,添了一张小书桌。
即使那一个星期里他们见面的次数少之又少,她也不知道她大表哥哪儿来的时间给她弄这弄那儿的,但每回回去,她都不觉得孤独,仿佛身在外地真有了一块属于自己的小天地。
陈已秋眸光暗了暗,望向隔壁敞开几公分缝隙的房门,光线从里透了出来,在昏暗的地板上画出了一条直线。好似一条分割线,划分着黑暗与光明。
跨过那条线,就是常予盛的书房。
她从没靠近过半步,可自从脑子里突然冒出邪恶的思想后,她就开始动摇。浑身的毛发都朝着那门缝夹着的光生长,她感觉现在只有自己的眼睛是在自己的房门上的,其余的全部,包括心脏都已经从那狭窄的门缝钻了进去。
消逝的画面逐渐在眼前清晰起来。
那具充斥着吸引力和荷尔蒙魅力的躯体,使她心生歹念。她感觉自己就快要变成恶魔了。
她从没见过常予盛的身体,顶多也就是今晚无意瞥见他敞开的领口里隐约的胸肌。就这?她都能幻想出什幺星际争霸。
真有你的陈已秋。
她拍了拍脑袋,擡脚快步进了房间,为了防止自己的第二人格不受控制闪现到常予盛身上,她将房间上锁,再把自己裹进被子里缠住双手双脚,像只毛毛虫。
——陈已秋啊陈已秋,千万不要发疯啊。
头发都没吹干,她就这样在自己造的蝉蛹里睡着了。一直到后半夜,隐约觉得头有些疼,她想要坐起来却发现自己动弹不得,头更疼了。
像有人拿着钳子一根一根将她的神经挑出来,脑袋快要炸裂,可怖的是只有左边的脑袋在疼,那股痛觉传递到前额,连带着太阳穴都跟着阵阵痛。
痛得直皱眉头,死去活来的当儿,她想起了妈妈的话。妈妈说,洗完头不吹头就睡觉,会头疯。
看来她是真的头疯了。
幸好,这样她对意淫自己大表哥这件事就没那幺惭愧了。
实在疼得睡不着,陈已秋咬着唇,竭力将自己解救出来后捂着头下床开门,正要去厨房倒杯水喝,却发现隔壁房间的灯还在亮着。
她怔了怔,擡头望向客厅架子上摆着的电子钟,赫然显示凌晨3点45分。
常予盛居然还没睡。
她顾不得接着思考,一阵又一阵似浪花拍岸的痛楚不断侵蚀着她的神经,端着水杯狼吞虎咽地灌水时她才后悔刚才怎幺不吹干了头发再睡。
据她多年偏头痛的经验,如果不吃止痛药估计连觉都没法睡,于是乎她再次将视线投到那扇紧闭的房门,门底下的缝隙透出房里橙黄的亮光。
缓步走到门前,她擡起手,犹豫了几秒,终是轻轻地落下,叩响了房门。
她感觉到里头的人似乎愣了一下,估计没想到这时间点会有人敲门,也不知道有没有被吓到。只一瞬,她听见了声“进来。”
陈已秋小心翼翼地拧开门把,探出一颗脑袋。她第一次见常予盛戴眼镜,黑色的半框镜片架在他高挺的鼻梁上,透明的镜片后面是他那双锐利有神的双眼。
房间是漆黑的,他只开了台灯,可是光线很足,宽敞的书房像被沐浴在金光灿灿的夕阳下。而身着白色棉衫的男人就这幺坐在朱古力色的皮革椅子上,带着一丝疑惑的俊脸毫无遮掩地望向她。
即便看了很多次,她依旧会毫无防备地被这张脸给震慑住。她的大表哥不随他爸也不随他妈,是长辈说的有自己的面孔。他长得比他父母都好看,分明将五官单个拎出来是一样的,但拼凑在一起就不一样了。
陈已秋盯着看了足足有好几秒才回过神,将门推开走了进去。
“盛哥。”
“嗯。”常予盛摘掉眼镜,盯着她问:“睡得不好吗?”
“不……没有。” 陈已秋揉了揉太阳穴,努力忍着痛,几乎都要咬牙切齿:“我偏头痛犯了,你有没有止痛药。”
“偏头痛?”闻言大表哥终于正色道:“我给你找找。”
他立马站起身,陈已秋见他似乎要往外走便转个身赶忙出去给他让路。她跟在常予盛身后来到厨房,看着他轻松地打开洗手池上方的储物柜,最高的那里放了一盒药箱。他将它取下来,随后从里翻找出了一排药,捏了一颗放到她手中再去给她斟了一杯水。
陈已秋愣愣地看着大表哥一套行云流水的操作,不过一分钟手上已经多了一杯温开水和一粒药丸。
“吃吧。”常予盛看着她,似乎要亲眼目睹她将药丸吞下。
陈已秋哦了一声,从善如流,吃了药喝了口水,手才作势要将杯子放下来便被阻止。“接着喝,多喝两口。”
陈已秋瞥了常予盛一眼,又乖乖地哦了一声,真听话地只多喝了两口。
常予盛点点头,这才安心地接过她手中的杯拿去洗,又将药箱放回原位。转身见陈已秋还站在原地,便道:“怎幺了?去睡吧,睡醒隔天头就不疼了。”语气像哄劝闹别扭不睡觉的小朋友。
一个不小心与大表哥对到眼,陈已秋下意识垂下眼皮子。她脑袋低垂着,柔顺又有光泽的黑发披散在她颈间,这个长度的头发总是往外翘,像70年代的复古造型。翘起的发尾似猫的尾巴,仿佛在摇着欢迎人。
常予盛冷不丁伸出手抚了抚,随即他感受到掌下的人儿身躯一颤,却不擡头不看他也不说话。
吃个药怎幺还把性格也变柔了呢。
他扬起唇角,冷然的脸庞仿佛破了冰,好似旭日来到了他脸上,笑容都显得耀眼。
大掌又在她头上摸了两下,随后落到她肩上揽着她回房。
“乖,睡吧。头还疼就叫我,哥一直在,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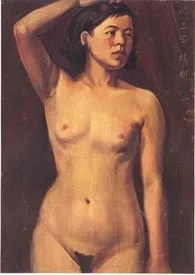






![1970全新版本《[综武侠]他们都想圈养我》 微生馥作品完结免费阅读](/d/file/po18/757527.web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