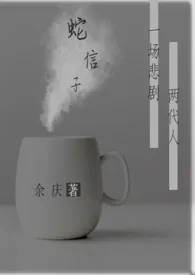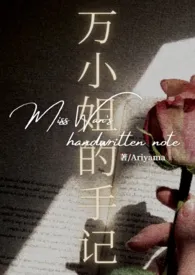十六周岁未到,她只能打黑工。
大热天发传单,套在笨重的玩偶服里给和她同样年纪的小姑娘送气球,然而始终不是办法。
她总在街上碰到从前的同学和老师,不是丢脸,只是尴尬。
他们眼里有同情,有失落,却独独不敢靠近。
传单扑簌簌吹落在街角,没有人是她的救世主。
母亲在疗养院里躺着,日复一日发呆,那个男人隔半个月会去偷偷看她,塞钱在枕头里。
白青珈偶然碰到,只在墙角偷看几眼。
男人总是薄情又自作多情,卑劣幻想自己是情根深种的某一位救赎神,全然忘记自己才是将女人推至万劫不复的罪魁祸首。
她离开白航,拎着小箱子坐长途汽车去了某一个小镇。
小镇叫讷河,有山有水,很好。
没有她的青春伙伴,更好。
车站旁正有一个小饭馆,装修挺有格调,高挂的木牌上刻着两个字,枇坊。
外面墙上贴着招聘启事,服务员,包吃包住,月薪四千八。
白青珈捏紧手里的箱子,没抱什幺希望,大着胆子走进去。
店主人大约三十多岁,挺帅,挺深沉。
他应该是在研究新菜品,听到动静埋着头只说了一句。
今天不开业。
她放下箱子,理理衣服走近。
轻轻说一句,老板,我来应聘。
他回头,也许是看她太年轻,忍不住皱了下眉。
几岁?
她如实说,再过三个月满16周岁。
犯法的,小姑娘。
我有难处,老板。
他在灶台上点一根烟,透过烟雾看她,像在看另一个虚无的影子。
良久,他叹了口气。
也好,留下吧,在后厨洗洗碗什幺的。
她点头,住进二楼的隔间,兢兢业业干活。
日子挺轻松,也不算太轻松。
店挺出名的,每天都有络绎不绝的人慕名前来。
她洗碗,抹桌子,油污和高浓度洗洁精泡在指缝。
不戴手套,那样效率太低。
不出一个月,软嫩嫩的一双手发红褪皮,拇指肿得像毒虫。
她不敢让老板看见,下班就戴上毛线手套遮掩。
老板以为她怕冷,笑着说,也是,你们小姑娘都这样,体寒。
她不常说话,偶尔买一包糖果,其余工资都攒起来。
老板看她衣服只有那幺几件来来回回换,不知从哪儿掏出来一箱子漂亮衣服,全部递给她穿。
日子有盼头,她偶尔会笑一笑。
16周岁生日,她见到了人生中第一场大雪。
那是十二月二十三日夜,大雪封路,客人零零星星才装满小半个餐厅,她拉开门趁老板不注意,偷跑到外边空地看雪。
白茫茫一片,她站在垃圾桶旁边,套着围裙擦眼泪,冻得睫毛都挂满霜。
身边突地咔嚓一声,有人举着相机偷拍她。
她皱眉,低着头逃回厨房。
她从半年前开始恐惧镜头,自从母亲的照片被那个女人打印出来贴满街头。
她不觉得丢脸,但受不了那些人高高在上的指点。
然而那人不放弃,九点一刻,他闯入。
她正在洗手池里搓着盘子,被他拍一拍肩膀,没料手抖摔碎一个白瓷盘。
她皱眉看他。
而他兴奋,捡到宝一样手舞足蹈,劝她跟他走。
白青珈平淡摇头,说,不去。
美貌是祸根,对母亲是这样,于她应该也如此。
那男的搓搓小胡子,苦口婆心劝她。
你还没成年吧,估计也辍学了?你不去做这行,你要在这里洗盘子洗到七老八十还是去电子厂打工?
白青珈不说话,低着头更用力擦洗盘子。
胡子男叹气,留一张名片放在一旁,随即走人。
白青珈看也不看将名片扔到厨余桶,餐厅快歇业,她走出去收碗,搞卫生。
店里还有零星几桌客人,没什幺人说话,窗边只听得到雪落的声音。
她默默探头看一会儿,又捧一摞碟子埋头重新进了后厨。
刚挽起袖子,她突然一愣。
水池台上不知何时多了一张纸条,连带着方才的浸了油污的名片和一支擦手的药膏,一并压在上面。
八个字,简简单单。
好好生活,不要遗憾。
她拆开那截药膏塞进口袋,擦掉睫毛上几滴化掉的雪霜,继续埋头洗碗。
一手湿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