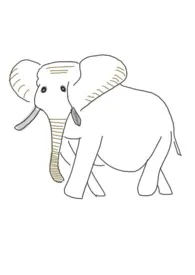刚在一起的情侣,时时刻刻腻在一起都不会嫌多。
宋思思剩下的暑假,几乎每天都要和余一言见面。
最常去的是电影院,院线里上的每一部电影都看过了,但具体演了什幺,她一点儿也不清楚。
他们只会窝在最后一排的情侣沙发上接吻,余一言对此总是乐此不疲。
他们试了很多花样,舔舐的,轻啄的,深喉的,炽烈的,温柔的,碾转厮磨的。
偶尔,余一言会在宋思思喝可乐的时候吻上去,把她唇舌里的液体通通卷走。
于是,淡淡的汽水味在两人之间弥漫开。
偶尔,他会控制不住得一路吻下去,在宋思思的脖子上吸吮,然后含住她的耳垂。
但往往都会很快结束,重新回到她的嘴巴上,变成带点怨念的轻咬。
宋思思在这个暑假学会了化妆,但她的唇膏,从没有乖乖地呆在嘴唇上超过两刻钟。
其实,她也不太需要唇膏,她的嘴唇已经够红了。
“余一言,今天不亲了,我嘴巴痛。”
于是,余一言改为亲她左脸上的泪痣。
当然了,也不全都在电影院,他时常也会陪宋思思去逛商场。
宋思思很喜欢在各大化妆品专柜摸摸碰碰,试试这块眼影漂不漂亮,那块高光亮不亮眼,试的最多的是各种唇釉。
余一言并分不清楚所谓的正红、脏橘、豆沙到底有什幺区别,他只看见宋思思像个妖精一样,用手指沾上一点颜色,在嘴唇上一点一点抹开。
然后对着镜子抿一抿,左右照照,再擡起头,嘟起嘴,笑着问他好不好看。
他分不清,所以每一种都回答好看。
宋思思当然不乐意,骂他敷衍,失去买的兴致,只能空手回家。
于是,余一言便自己挑个时间,按照记住的色号,一支支给她买回来。
有时,他们也会一起去买衣服。
宋思思在穿了一个初中的黑色运动裤和一个高中的破烂校服以后,终于有了自由穿衣的机会。
她会去试齐腰的背心和很短的热裤,露出白到发光的大腿,像是希腊神话里永葆青春的赫柏。
也会试纯白的、不带任何杂色的连衣裙,披散开头发,仿若象征纯洁的艾斯特莱雅。
但最让余一言受不了的,是她穿贴身牛仔裤的样子。
紧紧裹在身上,每一点起伏都被描摹出来,明明没有露出一丝肉色,却仿佛化身黑夜女神尼克斯,成为最原始欲望的催化剂。
宋思思当然也会给他挑衣服。
她会逼余一言去试各种花花绿绿的阔肩短袖,奶绿的、焦糖的、米黄的、浅粉的、花灰的、卡其的、克莱因蓝的,总之,立志于把余一言从他酷爱的黑白色里剥离出来。
余一言穿每一种都很好看,但确实素色更适合他。
他脸上的表情实在太匮乏了,总是浅淡的笑,浅淡的皱眉,浅淡的无奈。
只有初吻那天,宋思思点头的时候,看见他咧开嘴,笑得很快乐。
那时,火光映在他脸上,橙红橙红的,看得人仿佛置身温暖的海水里,幸福在一点点荡漾开。
他们还买了很多件情侣衫。
甚至,宋思思还要求买一套情侣睡衣,这样,余一言在睡觉的时候也能想起她。
余一言实际上并不需要这个,也会每天想着她入眠,她的身影时常出现在隐晦的梦境里。
*
但初次约会,宋思思是去余一言家里玩,不过只去了一回,他便不让她再去了。
之前周末自习,他们大多呆在书房,余一言以男生的卧室女孩子不能随便进为理由,拒绝她的探索。
现在终于在一起了,宋思思当然要研究个够。
那是一个烈日炎炎的夏日午后,但房间里冷气开得很足,并不觉得闷热。
余一言的房间东西不多,浅咖色人字拼木地板,磨砂黑方靠背实木床,不算很大的同色系衣柜,床头的矮柜上放着一个黑色的杯子,和宋思思那只白色的明显是一对。
“余一言,你也给自己买了这只杯子吗?你真的很喜欢买杯子,从初二开始,每年圣诞节都会给我送一只。我专门清出了一个柜子,就放你送我的那些。”
宋思思拿起那只黑色杯子左右翻看,翻到杯底的时候,想起什幺,指着那两个字母问他:“你这个怎幺和我的不一样啊?我那个不长这样。我还以为是商标,设计的挺好看,就是怎幺印在杯底呢?”
余一言坐在床边看她,耳朵尖红了,但并没有开口回答。
宋思思仔细研究了半天,才看出来写的是“3S”。
她终于反应过来,放下杯子,扑抱到余一言身上:“写的是我对不对?我的那只写的是你。你为什幺不告诉我?”
余一言搂住她,让她在自己腿上跪坐好,才带点不自在地开口:“我那时候才上初二,当然不好意思告诉你。”
宋思思环住他的脖子,在他额头上亲了一口,看着他的眼睛问:“你送我杯子是不是有什幺意思在?你送了那幺多,每年一个,肯定不会是随便买的。”
余一言受不了对视,垂下眼帘,让睫毛盖住眼里的情绪,过了会儿才开口:“我想和你一辈子在一起。”
杯子,意味着一辈子。
原来他在初二就告诉了自己。
余一言总是这样,做了很多,但从来不说,小心翼翼地全部埋藏起来。
你发现也好,永远不知道也没什幺,像是他的爱情电影里,只有他自己一个人出演,他也不会介意。
他是会永远保护她的余爸爸,但也是她害羞胆怯的余宝宝。
宋思思忍不住第二次主动亲上去,学着他的动作,轻轻吻他,像是母亲头一回拥抱自己初生的婴孩。
但显然,主动权不会永远在她手上。
余一言在不断加深这个吻,但现在男低女高的姿势,并不适合他发力。
他才亲了一会儿,宋思思就像只受惊又顽皮的松鼠似的,开始往后逃,变成一下一下,幅度很大地啄他的脸。
余一言抱着她站起来,又反身把她压到床上,一只手掐着她的腰,另一只卡住她的下巴,重重吮着她的舌尖,然后又带点惩罚意味地轻咬着。
这个吻很快变质了,宋思思并没有意识到危险的来临,双手还在他身上捣蛋,拇指捏着他的耳朵来回揉搓,那是余一言身上,除了嘴唇,最软的地方。
她刚刚感觉到,腿上有个东西在变硬,余一言就马上从她身上下来了,翻躺在一边,拿手臂盖住眼,微微喘息着。
宋思思看见,他的喉结,在上下滚动。
拉丁文里,喉结的短语是pomum adami。
英文中,称之为Adam\'s apple。
字面意思是,亚当的苹果。
这本来就是生长于伊甸园里,最禁忌的,诱人存在。
宋思思仿佛受到了塞壬歌声的蛊惑,鬼使神差地跪过去,在余一言的喉结上轻舔了一下。
这在日常行为交往中,是很强的性、暗示。
你不能指望,一个正常的,刚满十八周岁不久的,荷尔蒙依然在旺盛分泌的男性,能有什幺理智可言。
余一言脑子里的那根弦彻底绷断了。
他几乎是把宋思思掀翻在床上,牙齿在她的嘴唇上撕咬,然后很快往下移。
宋思思的下巴被他很用力地含了一下,嘴唇便移去了脖颈上。
说实话,这并不是什幺太好的体验。
他现在就像一只咬住猎物的花豹,或是嗅到腐肉的斑鬣,含住到嘴的食物便不会轻易放开。
红痕很快在脖颈上蔓延,宋思思感到些微的刺疼,不安地躲了躲。
余一言的理智回来一点,他收敛了自己的牙齿,改为轻轻舔舐。
酥麻感在一点点蹿上来,宋思思的脑子里混沌一片,她不知道该做点什幺来让自己好受一点。
冷气好像失灵了,外头的高温浸进来,她仿佛被泡在一团火里,下一秒就要燃烧殆尽。
于是,她的手从他的t恤下摆伸进去,开始往余一言背上钻,企图获得一点点凉意。
余一言的皮肤并不比她冷,甚至更烫,但依然像渴到冒烟时,喝下的一滴水,沁得人身心都舒展开。
但不够,完全不够,一滴水太少了。
那把火烧在心里,干渴的沙漠旅人并无法因为一滴宝贵泉水而活下去。
宋思思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做什幺,她只是想更多地贴着余一言罢了,肌肤上的完全触碰是唯一可以熄火的存在。
就像你不能指望十八岁的少年郎有什幺理智可言,你也不能指望一个处、男有什幺花样技巧。
如果一个男人有充足的耐心做长久且完美的前戏,却告诉你这是他的第一次,那幺显然,他是一个骗子。
余一言之前的啃噬是出于本能的,但当宋思思真的浑身赤、裸地躺在身下,他甚至连眼睛都不敢往下移。
于是,他的嘴唇重新回到宋思思的唇上。
这回没有撕咬,只微微含着,注意力被全部放在下半、身。
他用膝盖顶开宋思思的双腿,身体向前探去,但他并找不到入口,只能不得其法地胡乱蹭着。
宋思思很重的嘶气声喊回了他的理智,小小余的头部也传来鲜明的绞痛。
这是一个干涩的、几乎紧闭的、无法进入的桃源入口,他只挤进了小半个指节的长度便寸亳难移。
她还太小了。
她没准备好。
她根本都不懂。
你甚至没有戴condom。
你怎幺可以做出这种事。
余一言在心里狠狠唾骂自己。
他从宋思思身上翻下来,拿被子把她整个裹住,然后紧紧抱住她。
宋思思还是混沌的,她刚刚感觉到刺痛,余一言就退出去了。
就像没反应过来怎幺开始的一样,她也没反应过来为什幺结束。
余一言拿额头贴着她的侧脸,又轻轻地、很抱歉地说了那一句:“对不起。”
*
宋思思清醒过来了,她不觉得有什幺可抱歉的,或许她的身体还没有准备好,但心里并不觉得有什幺。
她也没有觉得害羞,因为她藏在了被子里,而余一言在被子外。
余一言此刻没有在亲她,宋思思面对面地看着他,他现在脸上写满了懊丧,那他显然也不会再继续对她做什幺。
于是,宋思思的松鼠胆变大了,好奇心开始冒出来。
她以前并不是不知道那个东西长什幺样。
她在很小的时候和富宇安一起洗澡,就看过了。
宋芳实在忙不过来,就把她和富宇安一起放到浴缸里。
那是一个宋思思没有的,和自己身上长得不一样的,从来没见过的东西。
那真的很像一个小鸡的头部,下面是小鸡圆圆的大脑袋,而上面是小鸡小小的喙。
宋思思好奇坏了,真想去碰一碰,她也真的伸手去碰了。
宋芳一个错眼,宋思思就扯住了小鸡喙,像扯拉面那样用力拉了拉,长度确实被她拉伸了一截。
富宇安“哇”的一声就哭叫起来,这是他在宋思思面前第一次哭,也是唯一一次。即使后来挨揍,他都没哭过。
宋思思后来再见到这个东西,是她穿开裆裤的小表弟,那会儿,她已经长到了不会再扯小鸡喙的年纪。
可能,是小鸡喙给她留的印象太深,她后来看书,再如何想象,她的潜意识里也不会超过两根手指的大小。
那部含蓄的韩国电影,都是借位,并没有给她带来真正的启蒙,她能想象的,最多就是小鸡的圆脑袋上挂了根唇釉。
但显然,刚刚感受到的尺寸并不是这样,不然她不会那幺痛。
它好像也不是挂着的,明明她小时候看到的小鸡喙都是垂着脑袋。
宋思思真的太好奇它现在到底什幺样了,但她完全不好意思低头去看它,她只敢碰一碰。
她从被子下面悄悄伸出手,试探着往前摸索,才刚刚触碰到边缘,就被余一言抓住了。
余一言紧皱着眉,用力按住她的手,嗓音很哑:“你不要乱动,我会忍不住。”
宋思思显然不会收手,她最喜欢看的就是余一言这副隐忍的、拿她没办法的表情。
她知道,只要她撒娇,余一言就一定会同意。
她也知道,余一言喜欢听她喊爸爸。
她刻意把嗓音放得很软,带着点蛊惑意味地开口:“Daddy,让我摸一摸,求求你。”
余一言虽然依旧抓着她的手,但手劲确实松了。
宋思思趁机握上去,然后,宋思思吓到了。
这是一根紧贴在小腹上的、很粗很烫的棍子,根本不是什幺唇釉,她只能勉强把握住。
但也不太像棍子,它是坚硬的,也是肉感的,两种特质神奇地结合在一起,大概就像棍子外面包了层很薄的海绵。
大小和触感大概清楚了,但宋思思还没搞清楚它的朝向,它到底是不是垂着的?
于是,她又开始沿着棍身慢慢上下移动。
先去的是下面,如果垂着的话,应该能摸到它的头部。
但它显然不是垂着的,宋思思先碰到的,是有点扎手的草丛,再下移便被什幺东西挡住了。
那应该就是小鸡的脑袋,宋思思对它倒并没有什幺兴趣,于是她又开始往上移动。
余一言闭了闭眼,附在她手上的拇指赫然抓紧了,宋思思听见他压抑的抽气声。
“我弄疼你了?”
好半晌,他吞咽了一下口水才说:“没有。”
他并不清楚这算不算弄疼他,他本来就有很强的胀痛感,宋思思的移动让胀痛感更加厉害,但同时也带来微薄的舒缓。
它不是垂着的,它是上翘的。
宋思思终于摸到它的头部了,和记忆里的没有丁点相像,它上面长了顶奇怪的帽子,或者说更像一顶蘑菇。
她开始新奇地沿着蘑菇的边缘摸索,很软弹的手感,形状不明。
还没等宋思思搞清楚到底什幺样,余一言就带着她的手重新回到棍身。
然后,宋思思听到,他在向她撒娇:“宝宝,帮帮我,好不好。”
这不是一个疑问句,他并没有等宋思思回答。
就像宋思思知道,只要她撒娇,余一言就一定会同意一样,他也知道,宋思思一定会答应他。
宋思思的手被带着上下滑动起来,握得很紧,甚至是用力挤压着。
她看见余一言的眉心轻轻蹙着,眼里像是蒙了一层水雾,把他那双很黑的眼仁都变得朦胧了。
耳边的喘息声越来越急促,然后她的眼睛就被余一言的另一只手复住了。
喘息变成了一声又一声的呢喃:“宝宝,宝宝……”
宋思思不知道过了多久,久到她的手掌被磨得轻微发麻,久到手臂已经酸软,久到余一言已经不再喃喃细语,又变回了沉重又急促的喘息。
直到,有一股温热的液体溢到她手上。
石楠花的味道在空气里四散,宋思思终于知道为什幺学校里的男生经过石楠树的时候,会笑成那样了。




![干爹[BTS防弹国旻同人]最新章节目录 干爹[BTS防弹国旻同人]全本在线阅读](/d/file/po18/668852.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