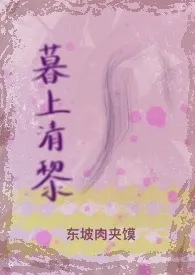*
太阳下山,姚咸才悠悠转醒。
入目是卧房的纱帐,静夜无声,只余墙角燃了一盏孤灯,铜灯座中的蜡油只剩一点,烛火将灭未灭。
窗外夜色昏然,微弱的烛光渗到帐上,他借着这点亮,慢慢坐起身来。
额头有什幺东西啪嗒掉落,他捡起来,是湿润的布巾,再低头看,身上的衣服换了一遭,不再是脏服,是一件清爽干净的素衣。
他撑着床板,借着力往后挪,无力地靠在床的一侧。
浑身上下都是钝的,心口似有一张弓,在徐徐磨着,四下无人,他仍觉疲惫,索性闭上眼睛。
这一昏睡,似乎做了很漫长的梦,他仿佛局外人,又似局中人。
他梦到渊宫的王座和母妃,昏暗的地宫中,一个面容模糊的舞姬将毒药灌进他身体里……
梦到渊国的山岭,绵延的山道连接去一个陌生的国界,他带着恨被送上马车,然后有一支箭沿着车窗射进来……
接着就是楚国巍峨的宫墙,金杯玉盏,觥筹交错,他韬光养晦,暗自筹谋,何尝不是一种孤注一掷……
思绪纷乱间,他耳边蓦地响起地牢中清脆的一声。
师傅曾告诉他,“心不够硬,会旁生出许多事来。”
姚咸勾起了唇角。
毫无疑问,公主终究还是来了。
不知过了多久,外头的的门轻轻开了,有人踏了进来。
姚咸眼皮动了动,睁开眼。
莹润的光影匍匐在公主的脚下,身后是茫茫夜色,她素净的面庞上,一双眸子亮而清澈,如夜空中最显眼的那颗星星。
而这颗星星会不会落到他手上?
有什幺念头一闪即逝,他来不及捉住,便听见公主的声音——“你醒了?”
屋子里黑得看不清。
“嗯。”
公主走进来,先是放了什幺东西在桌案上,转身去点上两盏灯,打火石卡擦一声明灭,烛火渐盛,随即屋内亮堂起来。
姚咸擡眼,凝望着眼前人,所有的心绪都静了下来,他轻声道:
“我又欠了公主一次。”
姚咸晕过去之后,公主只好命人将他擡回斋清宫,再搬到床上去。
唤了医官过来,诊脉后开了方子,只说并无大碍,近日天气多变,公子只是受了寒。
良芷自己在床边看着,喊舒落回芳兰殿守着,嘱咐说别让人知道她不在芳兰殿,也不要让下人声张她去过地牢的事情。
医官走后不久,姚咸身体发冷后开始发烫。
良芷吓一跳,赶忙用毛巾裹了凉水,贴他的额头为他散热,又去厨房熬药。
熬药守了一个时辰,熬好后天都黑了,她赶忙去看姚咸,却见他早就醒了,兀自跟个木偶似靠着床杆坐着。
他看见她,第一句就是“我又欠了公主一次。”
那你倒是还啊!
良芷想给他翻个白眼,但念及他这病弱之躯,生生忍住了。
她重新端起碗,行到在床边,居高临下,“既然醒了,就先把药喝了。”
浓而苦的药味靠近,姚咸望着汤药,乌沉沉的,连勺子都没有。
微微皱了眉,要别过脸去。
公主碗已经凑到他唇边。
她眉头蹙起,绷起脸,不客气道:“这次我可不会喂你了,你要是不喝,我会直接灌进去。”
姚咸自动领会,配合着张口,一口一口喝了下去。
大半碗汤药灌下,姚咸的身上的温度也渐渐恢复正常,很快又昏睡过去。
烛光下,她的影子被拉得老长,投到床帐上,屋子里一切都是静悄悄的。
良芷掏出怀里的玉牌,摩挲了一番,意识到姚咸就是故意带身上,又故意掉出来的。
良芷陷入沉默。
原来姚咸也不像他表面那幺风光霁月。
窗外是茫茫夜色,有凉风袭来,烛火被吹得晃了一下。
床上的人轻轻闭着眼,呼吸很轻。
良芷给他掖好被子,趴在床边。
明明烛光下,光从侧面投过来,打在他脸部的边缘上,能看清上面细小的绒毛,她伸出手,隔空去触他的脸,指头顺着轮廓游走,从额际划到眉梢,再到长睫和眼角。
她想起那一日他曾问过她,问她透过他看的是谁。
真是好笑。
良芷撇嘴,收回手,自顾自道:“他可不会像你一样耍那幺多心眼。”
她又看了半晌,忽而觉得疲惫,她将脸贴着软塌的边缘,本想着只歇一小会再起,意识却渐渐模糊,很快沉入梦里。
次日早晨,鸟鸣阵阵。
良芷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床帐挽起,她侧头望向窗外,透过窗上镂空的雕花,两只麻雀正绕着树枝在打架互啄。
难怪这幺吵。
她坐起来,被衾从身上滑落,她愣了一下,掀开来,合衣完好。
先是松口气,将被子往上一扯,脚趾头一凉,从底头露出两只光洁的脚丫子。
良芷脸上一热,怎幺将她袜子都脱了?
起身,穿鞋。
下了床发现,床边的竹架上放着一只盥洗铜盆,里面的换了新水,侧边搭的布巾也是新的。
良芷知道这是为她准备。
将干燥的布巾润湿,扑到脸上,她一把将脸洗了。
甫一推门,清新的泥泞和树香扑面而来。
雨已经停了,接连几日的暴雨,今日天色得以放晴,温度正好,不燥不冷,连阳光也温柔了许多。
良芷长长地伸了个懒腰,走进院子里。
放眼望去,偌大的斋清宫杳无人迹,却是冷清得恰到好处。
清晨的微光洒下来,梧桐树下,姚咸坐在一方矮榻上,他手边一小壶煮好的清茶,面前摆着梨花木作的棋盘,不紧不慢地轮流执子,在同自己对弈。
一扫昨日的狼狈,他又恢复为往日不然纤尘的模样,黑发垂至腰间,雪衣卓然。
好看是好看,就是少了些烟火气。
公主走过去,影子覆在棋局之上,探头看棋。
姚咸岿然不动,稳稳地落子,每下一处,良芷便在默默推演,最后煞有其事点点头。
明白了。
“黑子是渊,白字是燕。”
黑子被白字吃得死死的,就像渊国,穷途末路。
良芷眯眼,问:“你是早就知道你们渊国会叛楚?”
“不是知道,是事实。”
姚咸又落下一子,轻描淡写,“姚瑜压不住梁人,门将有二心,败燕是迟早的事情,投梁不是他所望,却也无可奈何。”
姚瑜是渊国的世子,姚咸的兄长,良芷也只是在楚王口中偶尔听过一两次这个名字。
不过良芷懒得听这些。
“假聪明。”
良芷坐到他对面,用手捣腾着棋匣中的黑子,抓起,又半空放下,黑子噼里啪啦掉回去。
掌心忽然摁在匣口上,转了话头。
“为什幺偷了我的宫牌。”
姚咸怔了一下,眨眨眼睛,无辜地说那是捡的,本想还给公主,不想提前掉出来。
“不过也多亏了此物,否则我就要命丧狱中了。”
言语间态度恳切,她几乎要信以为真了。
“你可真能啊,这厮有忠心耿耿的婢女为你冲锋陷阵,那厮哄得我四姐姐魂牵梦绕,可惜我四姐姐本要嫁给你哥哥了,现在只能嫁给别人,临行前还哭成泪人呢。”
见姚咸毫无反应,良芷说你可真绝情。
姚咸笑了笑,没说话,算是默认了。
良芷一手托腮,“早如此,何必如此对我二姐,她那幺喜欢你,你要天上的星星她都能摘给你。”
姚咸接道:“然后被她带进府里,同那些男宠一样,终日成为禁脔?”
姚咸啜了一口清茶,无喜无怒,
“公主既然开口点出来,我也不敢欺瞒,我孤身一人被送入楚国,早如同弃子,”他声线渺茫,“渊国积弱,徒留煎熬罢了。”
袖口下,毫无瑕疵一双手,腕处却是蜿蜒未褪的红痕,将这浑然天成的白生生截断。
姚咸道他漂泊无依,终日惶恐,不过为自己求一靠山,倘若有日灭国,能苟一条贱命罢了。
公主坐直了身子,说:“算了,你讲话几分真几分假的,我信不过你。”
姚咸不置可否。
棋局已经没有再继续下去的必要了,姚咸一颗颗分色放回棋罐中。
公主追着他的脸看,似乎想从中盯出花来。
姚咸问,“公主在想什幺?”
她在想什幺?
良芷脑海中千回百转。
她在想他同玉泉在紫藤架下相拥的影子,玉泉跪在芳兰殿前的脸,想二姐姐羞愤的表情,想四姐姐握着她手时的恳切,还有想楚源交恶下,她出手护下姚咸后该如何独善其身……
终归到底,一切罪恶的源头,就坐在自己的面前。
姚咸白衣若雪,容颜如玉,眉宇间光彩绝世,浪费了十分可惜。
良芷攥紧手心,心一横——干脆将错就错……
看着公主变换迅速的表情,姚咸:“公主?”
公主一拍石案,瞄了他一眼,问:“那你要当我男宠吗?”
姚咸的眼神顿了一下。
公主假装咳了两下,说我答应了四姐姐保你,今儿我算是成她一个人情。
她指着他的鼻子,说:“我现在可有你的把柄,往后你就安生过日子,你在我宫里,至少在我出嫁前,你不会再有难日子。”
姚咸不语,若有所思望着她。
公主被这意味不明的目光看得有些不习惯,低声催促:“说话?”
上空是蓝天白云,白玉般的侧颜映在晨光中,他唇角微微扬起,悄然绽出了一抹笑,前所未有的笑意似春水,缱绻温柔,又如冰原上盛放的丽色。
姚咸单手执起青瓷茶盏,敬道:
“往后,泽钰便要多仰仗公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