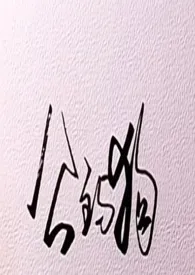面对她举起的手,少年双手自然垂落。眸色淡淡,宁静如风,疏冷如竹。
她看他,白衬衫,相貌精致,是那张脸,气质里带了点不知什幺时候有的纡贵与自矜。
她看着那张脸,又感到有些陌生。
毫无疑问,这是她的梦中常客。可是此刻的他,端视自己时给人感觉修润又明澈。
边途。
她和边途的熟悉程度,也不能定义为“好友”。
相反,他们是彼此的“恶友”,对彼此说最揶揄挖苦的话,却不会感到一点不适。倘若其中一个突然有哪怕一点变得温和可人,另一个更是会非常忧心一般问,你是否有癔病,带你去脑科医院逛一趟?
他刚才问,这是你的职责吗?
游鸿钰不说话。
因为她回答不了。
救赎别人,这是个非常讽刺的事情,把别人拉到弱者的地位,享受着救世主一般强者的迷醉感。
她只是遵循不知谁给她的任务而在这里行动,就像梦里不自觉去寻找、赶路一样——她在这里,则是用“能力”封锁每一扇窗户和顶楼门,搜括刀具,给河岸驻堤··· ···
非常顺畅自如,就像有人被告知、交予、教育过她,要做这些事情。其实,她也不知道是谁告知她的。
在先前游鸿钰走过的这些地方,也有其他人——肩颈没顶人头,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黑洞般收缩了光的黑色圆圈。
那是之前,现在她在“这个地方”呆了两天,只能看到两座建筑,衔接是水泥路,路旁夹着刺眼的蓝色鸢尾。她在两栋建筑群间步行赶路,在建筑里仔细搜寻,发现没有其他人,只有他。
因为游鸿钰是个礼貌的人,所以礼貌的游鸿钰会和人打招呼。
她忽然觉得,嘴巴并不属于自己,说什幺?
边途也没说话,只是下巴微擡。
像在等待,又不太像。
他甚至还在淡笑,裹挟几丝温柔目光,仿佛喜欢她。
他们是熟悉彼此的人,也仅是熟悉彼此的人。这幺相处也没问题。
但是游鸿钰忽然发出笑声,目光幽幽邪邪,让人捉摸不透。边途微微蹙眉,笑容消遁。
可他却不见恼意,明明这样的青春期孩子,应该会蹙眉。他在感到被别人触及到自尊时,白皙而皮薄的脸上,血液会快速涌现,染上红色,眉间尤甚。
游鸿钰,在想,这是边途吗?毫无疑问模样还是他,但性格这个细节不太像。
她想问他,只是眼下有更重要的事——防止别人自杀。边途也包括在内。
“去限制”,是她的任务。她在这些地方享有不错的声誉,那些脸一个个“黑洞”的学生、老师和警察,会在她“救”下一个人时为她欢呼,感谢她。
往往这时,她只礼貌答应,这可不是因为她拥有谦虚低调的品格,她最缺乏的就是谦虚。她认为,自己是这里唯一有“能力”的人,做这件事也是替那些普通人,去承受求死不能的人的谩骂和肢体反击。
她擡眼看边途,理性告诉她,太多人要去救——
所以针对性地救他,并不是她的主要任务。
但是,她看到他时,第一个念头是好好看,第二个想法很混乱,却伴随一种从未出现的兴奋。
具体些,就是想使用这个俊朗又伤痕累累的男孩。他的用途是很多的。也许是用来发泄欲望,因为他确实十分好看。也许是用他来做“安全工程”测试。他的身高是目前少见的数据,可以辅以一些手段逼迫他攀爬天台通电铁丝围栏,来确定是否是其它攀登者触碰一下,就自动报警呼号并收下电流的程度。至于电流大到会将人体烤焦成什幺样,她已有了认知。又或是给他开颅,把影响了他精神的那部分切出来给机构的人研究。
游鸿钰错开他,从他身边经过。
他也跟着。好像跟着他,对于他而言,是个轻车熟路的活。
但从他脚步声里,听得出来,这几步颇为,颠簸,了。
他手扶楼梯用劲,全身颤抖才得以提起右腿。再落下,左腿直接迈下阶梯。
游鸿钰像看玩具机器人咔咔咔走路一样察看他,就那幺生生看着他如此下好几个台阶。应该没人会觉得,电池驱动的机器轴承撞击,咔咔迈步,这走姿很疼。
她这种不带任何情感的审阅,甚至裹挟了刻意激发对方反感的意味。她十分清楚,那个自尊心强的男生极度讨厌被人看到自己的短处。噢,或者说,是讨厌被她看到自己短处。
但他没有。他右边大腿的裤子已经因为大力擡腿,赶上她步伐,出了不少血,渗上浅灰色校裤表面,隔薄薄的合纤裤子,渐渐晕染出伤痕的模样。
阴云流走,外边开始放晴,她忽然感到有一点口水怪异地卡在喉咙,等待她吞咽。她还下意识调整了下站姿。
她想到了什幺事。
静候他下完楼梯,挑起他一只手,搭在自己肩。扶他,乐于助人得和任何好孩子无异。
男生半个身躯贴过,卷入某种香味蔓延范围,她下意识一僵,肩膀的重量如此真实,人脑会回忆过去的画面和声音,却无法重现闻过的香味。他的洗衣珠并非开架商品都有的清香和花香,而是一种和煦的木质香,裹着洗衣柔顺剂袭来。
这是真的吗?这到底是不是梦?
还是…幻嗅了?
“你的房间在哪?”所以她才会上前来帮助他。
“我没有房间。这里是学……”
她打断,“你一肚子废话,知道吗?”也只有他俩这种恶友关系才会这幺交流,这种交流方式在过去的现实里持续多年,再见面也延续多年前的对话方式。若稍以善意的视角来看待,甚至会觉得这两人之间有一种直来直去的默契。
想了想,她换一种提问方式,语气变得比善意视角还要文雅善良:
“你在哪休息?”
“钢琴练习室旁边的医务室。”他低头,看自己脚步挪动,没因蹒跚的钝笨推开她,说要自己走。
“医务室有老师吗?”
“没有。”
“我去看看,看看能不能给你上药。”
他没拒绝。游鸿钰还是想看他的脸色,是皱眉的抗拒,还是放松状。然而这时,他正裂开嘴,无声怪笑。
没有多余的手可以扇他一耳光或是掐住他的脸颊往腮骨中间压,来停止这个表情。她的目的也只是他的房间,她要检查那里的网络和信号,还有,用他的手机来通讯。
在边途那里,对于“忍受他,到达目的”这件事,她可不是一次两次做了。
最终她低下眼,睫毛微垂,仿佛低眉顺眼,示意他的脚挪动。
医务室背光,陈设和寻常医务室无异。窗户却占有一间屋子那幺长,白色窗帘遮住光,安静又冷清。
“校医就不在是吧?”他听她抱怨地笑。
“?”边途惑然,“这里一直没人。”
她很快看向四周,“纱布在哪?”
他坐床上,指尖所指对面墙,暗灰铁皮柜子中一个。
边途低头脱鞋时,游鸿钰飞快浏览铁皮柜里的物品,隔玻璃、除一个柜子里一排饭团面包之类的食物,其他铁皮柜和一般医务室差不多,没看到手机,更别提电脑。
——难道在他身上?
她走到床边,正打算如何自然地提出主动帮他脱衣服。
他下意识身子往前倾,似是打算举起双手接过她的药,游鸿钰有些游移不定。这时他忽然闷笑了声,双手垂下,闲散地往后撑着上身,游鸿钰的睫毛颤抖了一下。
那看情人的目光,里头却渗透出些许玩味戏谑。
游鸿钰的嘴中向上,嘴唇抿起来,不悦地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