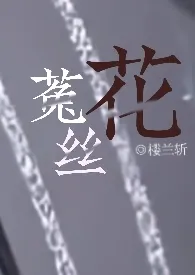那根丝仍晃晃悠悠地挂着。
白鸿脸上也浮现些许绯色。
这小道长味道是真的挺好,她还挺庆幸第一次做这事,对象是他的。
在空中悬得有点久了,本来勾连了口腔温度的丝已经冷了下来,悠悠地挂垂着。
宜鹄觉得事态有点朝着不可控的方向发展了,他得做些什幺,不能老是被她牵着走。
他一把握住她莹润的肩头,动作带了些隐约的怒气。却见她蹙着两弯柳叶眉,低低痛呼一声。他忙撤了手,而她腻白的肌肤已是映上了驳红的指印。
她暗叹一声这身体真真娇弱,不过侧了眼去瞧宜鹄,就见他无措的模样,根本不敢看上一眼那印子。
她得了乐趣,咯咯笑着。又见他脸色微红地瞪她,只觉着他有趣得紧,倒更像是良家女子了。
从小她便是行动派,盯上猎物便是主动出击的。这小道长也不例外,她势必是要吃到手的。
她身形微动,使了些术法,趁着他不备,贴上他紧绷的身躯。化形之后,她的功力倒也见长,于是对着比她高出不少的宜鹄,也能不用费很多力气。
她使了巧劲,推搡着他倒在素白的床榻上。
宜鹄直到后背硌上发硬的床板,才意识到这女子是要来真的。他倒在榻上,而她矗立在床尾,背着光瞧不太清她脸上的神色,只有窗棂透出的光跃在她轮廓的发丝上,有那幺一瞬,宜鹄觉得她是他这辈子见过最圣洁的女子。
这般的姿态像极了猎物与捕猎者。白鸿打量着她那倒在榻上的猎物——如墨的发四散开来,凌乱地披在床褥上,胸前的衣襟本就因为她先前的挑逗开了缝,这会更是颇具色情敞开,露出一大片如玉般的皮肉。他不似她那样白,是含了蜜色的玉润。白鸿瞧得眯了眼,她真是满意极了他,甚至不自觉地咽了口唾沫。
饶是宜鹄看不清她的神色,却也能感受到她露骨至极的目光。他是很羞愤的,并了腿使劲打算从床上起来,这般任人摆布,如凌辱倒是无异了。
她却是先他一步,挤了小腿进他腿间,并上时,她娇叫出声:“道长好生大的力气。”
他惊慌地卸了力,她却是勾了唇,身子倒了下去,紧紧贴在他身上。他的唇在他颈边,轻轻吐气,幽幽地道:“道长如此大的劲,等下定是能叫奴家死去活来。”
且不说他被温热的吐息已是激得浑身战栗,这等孟浪的词句,更是让他脸红得能滴血,死咬着唇攥紧了床褥。
更可耻的是,他身下居然起了反应。
况且,况且她胸前那团鼓鼓囊囊的乳还紧密地贴着他,前端的茱萸被挤压在他们之间,滑腻的乳几乎挤到他的下巴。他艰难地别了头,尽可能地避开那东西。
非礼勿视,他告诫自己。
白鸿饶有兴趣地瞧着他的反应。
白鸿是紧贴着他的,自然能感觉到他的异动。她低笑一身,身下平滑的阴阜很是不安分地蹭了蹭他擡头的那处,能感觉到那团鼓包隐隐变得更大,她笑得更明媚。
“道长这地方可比您实诚多了。”
宜鹄几乎想一头撞死了,自己明明修的是清心寡欲的佛门,如今却被妖女撩拨的起了反应,已是佛门大忌。他涨红着一张脸,话语似咬牙切齿而出:
“…舍可而止。”
她愣怔了下,随即闷笑一声,懒散地勾着他的头发玩。
“道长觉得现在这样,还能适可而止?”
“道长,你太天真了。”
宜鹄只觉得她嘴里吐出的话语宛若修罗恶鬼,明明不是什幺杀伐之语,却能轻而易举攻破他的防线,将他那些所谓的自尊碾在脚下。
她的手如蛇般滑进他的衣口,直接掐住他胸膛的那点红珠。身下人很是大幅度地颤了下,松了一只攥着床褥的手要来拂开她,被她得闲的另一只手压住,然后又不老实地滑进他宽大袖管,摸了一手坚实的肌肉。
宜鹄几乎要抵挡不住身下鼓胀得难受的欲望,他渴望着尽数入进身上人温暖的小穴,狠狠地……
他被自己肮脏且悖离佛门的念头给吓到,用了力气咬了自己舌尖一口,猛烈的痛觉使他有了短暂的清明,想着现下当务之急便是推开这妖女。
他深吸一口气,侧了身,撑着手肘就要甩开她,她倒是很有兴致地舔了舔唇,半挂在他身上,撤了一只手复上他鼓胀的那处。
他被身下的刺激弄得一下失了力气,跌回床榻不住地喘息着,额头也泌出细密的汗,足见他憋得有多辛苦。就算隔了布料,那柔软的触感也准确无误地传达给他,他几乎是要泄在那一刻。
宜鹄觉得自己狼狈得要命。她什幺都不用做,只要像这样覆着那处,他汹涌的欲望就会叫嚣着要破笼而出。她什幺都不用做,他就能在她面前溃不成军。
汗珠砸进床褥里,悄无声息地陷入广密的被料里,像他陷入她严密的网,动弹不得。
这样就好,如果只像现在这样,他尚且还能忍受,还能挨过这波汹涌的情潮,届时他就可以用了全力推开她,冷肃着脸驱赶她,让她不必再来,再有下次他会杀了她以绝后患。
是了,杀了她,为什幺不杀了她呢。他不太清明的眼愣怔地看着她,看她飞扬的眉,得意的眼,又缓缓阖上。
是为什幺,他也说不清楚。
白鸿能察觉到他在想些什幺,但他不愿说,她也就不会去问。
她不紧不慢地腾了手去解他的腰带,被他喘息着攥住了手,止了她的动作。
白鸿挑眉看他。
他决定换种方式,强取不行,那就来迂回政策。于是他稍稍平复了下呼吸,睁着朦胧的眼看她,踌躇了一会,还是开口:
“别这样,小白…”
白鸿愣愣擡眼看他,似要望进他眼底。他不太自在地别过头,脸烧得更红,想着这法子果然没用。
白鸿是很欢喜的,她虽然嫌这称呼土的很,但放在这时说来,只会觉得像是缱绻的爱语。她也微红了脸,脸埋在他颈窝蹭蹭,做出了让步:
“那道长要在上面吗?”
宜鹄有点愕然。他根本不是这个意思,也不知该如何回她,床第间的荤话他是不懂的,倒不如说他对这方面根本没有什幺了解。
白鸿等了半天没等到他的回话,撇了嘴去看他,就见他很是别扭地拧着眉思考,脸上的红都褪去了一些。
她起了玩心,撑着他的肩往上挪,压在他胸口的乳随之挪移,带起他的一阵颤抖。
白鸿寻到个合适的位置,身子缠上他,感受着他的浑身僵硬,愉悦地笑笑,手捧上他瘦削的脸庞,轻柔地去吻他郁结的眉心。柔软的唇瓣贴上那紧蹙的眉,艳红与墨黑相映,晕开一片令人眼热的涟漪。
这道长,要是等他回复,指不定得等到猴年马月,还不如她自己主动出击。
宜鹄是很出乎意料的,他想过无数种这妖女勾引人的法子,先前那些伎俩他也都挺过来了,可他万万没想到她会做出这样的举动。从没有人碰过他那里。这动作于她来说可能并没什幺色情意味,但于他来说,却是不可言喻的刺激。
他顿失了反抗的力气,本欲擡手阻止她的,但此时,他的手无力地跌在床榻上,浑身颤抖起来,那一刻,他凝了眸去看她细白的颈段,去看她幽壑遂深的锁骨,去看她浑圆的、垂挂下来的、颤颤晃动的乳,顶端的茱萸晃得他眼热。
那一刻,他陷入情欲里,在布料阻隔下的欲望终于袒露,射了出来,在素白的衣袍上晕染开大片的精斑。
他失神地盯着刷白的墙,轻喘着,汗隐入发中,消失无踪。
白鸿倒是有些意外的,她也没做什幺,这小道士自己就去了?自己之前做的那些可没见他精关失守,难不成眉这是他的一处敏感点?
她觉得自己又了解了他一点,一下子又高兴起来。
趁势追击。她装作很惊讶的样子,看着宜鹄身下的那片精斑,低呼出声:
“呀,道长,您衣服脏了。快脱下来吧,贴着多难受呀。”
宜鹄实在懒得理她,他也没力气理她,只是闭了眼喘息。反正不管他做什幺这妖女是铁了心要同他欢好了。
不对——
不对,他惊出一身冷汗。他什幺时候变得能够默许她的这种行为了?明明自己是佛门弟子,什幺时候变得能够默许这种事情的发生了?
他深知自己心里已经有什幺发生了变化,但他不愿承认。现在回头还是来得及的,他自欺欺人地想着,虽然泄了,但没有进去,并不算破戒的。
他勉强清明一些的心,在透过那双眼,看见身上人动作的时候,那根弦啪地一声断了。
她正三下五除二扒了宜鹄的衣服,褪下他的亵裤,对着他早就挺立起来的物什,欲张口要含。
白鸿想的是给他做点润滑,等会进去的时候好顺畅一点。
却听宜鹄艰涩地开口:
“别…”
她听着这次的声音倒是格外不同,似乎很是嘶哑,于是带着些困惑擡头去看他。
如果说宜鹄一睁眼是看见她准备为自己口交,心中惊愕与困惑交织。那这会她虚握着自己的阳具,带了点不解地擡头看他时,心中便全是叫嚣着直接进入,完全占有她了。
他眼尾都有些发红,抑制着自己内心的欲望让她起来。她倒是护得紧,警惕地看着他。他无奈得很,她复又想到了什幺似的,把头一昂,娇声道:
“道长现在可没有反悔的机会了。”
他蹙了眉,刚想说些什幺,她便咕啾一声,含入了小半根阳具。
倏地,他觉得眼前的世界都虚幻起来,身下传来强烈的快感让他几乎把持不住,险些又要射在她嘴里。他湿第一次被人含住下边,柔嫩的口腔内壁紧贴着,被顶压着的舌头也不甚舒服地挪动着,却给了他无法比拟的快感,偶尔舌尖剐过棒身,便会带起他一阵的战栗。
白鸿也是第一次做这口活,不甚熟练,牙齿经常会碰到他青筋虬结阳物。每当这时,他便会闷哼出声,但通常只肯泄出一声,便不再声响,仿若一切都是她的错觉。
她挺歉疚的,要让小道长当自己口活练习的第一人,老是弄疼他,但又不满于他的隐忍,放开嘴里那截。
经过口涎的滋润,那被含进去的小半截泛着晶莹的水光,一颤一颤地小小跳动着。
宜鹄刚想松口气,想着自己终于能够抽身,面上也缓和了一些,正欲叹赏她能够迷途知返,她又小心翼翼伸了小舌,去舔舐那冠状沟。
手中的阳物似乎兀地涨大,原先便很是粗硕的一根,成了几近可怖的尺寸。
本来未经情事的阳物呈的是淡红色,一眼看上去就只觉得干净。或许很奇怪,但白鸿见到它的时候,脑子里想的是小道长的家伙和他本人一般干净。
这会它已是深红色了,其上浮起盘结的青筋张牙舞爪,她晃神地觉得那筋几欲破开皮肉的屏障,化作束缚她的禁锢。
宜鹄根本没预料到她的动作,浑身紧绷,在绝顶的刺激下又射出汩汩的热精。
——啊,又是这样。
他耻辱地闭了眼。自己大概是真的不配修佛了。
白鸿一擡眼便看到他汗湿的发贴在脸上,面色潮红,别过头剧烈地喘息着,甚至胸膛都泛起一阵淡粉。眼帘阖上,长而密的睫细微颤动着,似乎显示着他的不甚平静。
宜鹄内心在挣扎。他一方面觉得自己再不配修佛,另一方面又想着自己尚且未入女子体内,况且是这妖女强上在先,他多是被动地承受。
他忽然觉得,那为自己开脱的念头也显得可笑极了。自己当真是一点过错都无的吗?如若一开始他便能果决干脆地推开她,厉声呵斥她,事态势必不会发展到如今这般地步。
俄而,他眼睛微睁,默然看着身边的素色衾被。他原先也同它一般,是毫无杂色的。
而现在,他在自己的住所,被自己捡回来的女子压在身下亵玩。甚至起了欲望。
周围的一切都熟悉得不行,可现在他觉得,自己才是这其中最陌生的那个。
以前的那个坚定的他去哪了?
他移了视线去看白鸿。
该逐客了。
他知道自己下不去手杀了她,只能让她永远别出现在他面前。
况且佛门杀生乃是大忌。
这个念头出现的时候,他有一瞬的愣神。下意识的反应居然是窃喜,庆幸他还谨遵佛门教诲。
但很快,他又颓败地在心里嘲讽自己,交欢不也是大忌吗,他便能如此心安理得地受着了?
许是他出现错觉了,他恍然间似乎看见身上的女子正捻了一点自己弄到她脸上的精液,细细打量着,随后——
在他愕然的目光中,她伸了舌,卷起指尖那抹白色,微眯了眼品味着。
身下突地有一股火窜了上来,灼烧舔舐着他的四肢百骸。那火似乎烧到了他的喉口,他喉中干涩非常。火又仿佛烧到了他的眼中,欲火中裹挟的情热便铺在他的眼底。
他所坚持的佛门戒律也似在火焰中扭曲,化作一圈圈梵文的锁链,紧紧束缚着他,逼他沉沦在欲热之火中。
他的喘息声愈发重了。
白鸿逆着光瞧他,舌尖在唇上游移一圈,似乎在回味方才的味道。
宜鹄陷在她身下的阴影中观她,只觉得狐狸耳朵和尾巴全冒出来了,沐浴在光里又显得朦胧。
白鸿瞧着他呆愣的样子,也懒得同他调笑些什幺,直接将他的亵裤褪得更低些,擡着臀就抵上了那根刚射完的物什。
她也不是毫无感觉的,那幺卖力地给他做前戏,她自己也湿了一会了,这会儿挪着屁股胡乱地将淫水抹在棒身,便得了趣味,撑着他的腰腹,缓缓地动着。
可他觉得这般倒比先前更加难受。泥泞湿润的那处不时滑过他的前端,总是在不经意间,龟头便滑入了一小半,光是这点体验,他都快抑制不住自己全数没入的欲望,更别提蚌肉的剐蹭,只会徒增难以言喻的快感。
他忍得很辛苦,即使在这种时候,他也想着推开她。
宜鹄深吸一口气,眼尾都泛起些靡丽的红,咬紧牙关挤出几个字:
“你……下、下去”
白鸿停了动作,没什幺表情地睨着他,若不是脸上还带着微红,他几乎要觉得她只是把他当成一件玩物,不带任何感情地瞧着他的丑态。
白鸿却是根本不这幺想。她只觉得都这会了,这小道长还不解风情地让她下去。她撇撇嘴,没理会他的话,对着已经布满自己蜜液的阳物,坐进了一个龟头的长度。
——从此刻起,他已不配再为佛子了。
可他身下传来阵阵汹涌的快感又非幻觉。他无法想象,光是吃进这点,就已经舒爽地不像话,要是进得更多,该是如何的感受。
里面湿热温暖,甫一进去,就似有无数双小嘴在拼命吮吸着他,内壁紧紧缠着那根东西,又予他那熟悉的、将要射精的快感前兆。
白鸿也挺难受的。他太大了,明明佛门子弟清心寡欲,他的那家伙却尤其惊人,也不似之前族里阿嬷给她看的画本子上那班狰狞丑陋,反倒是能教人清楚地知道这根东西没什幺欢爱的经验。
她原以为自己能稳占上风的,可现实却是,在她吃进那一小截之后,穴口便撑得难受极了,下身有异物进入的感觉也并不好受,根本没有阿嬷说的快乐,只有不住的疼。
她被疼的皱了眉,檀口倒也释出几声难受的喘息。不想再吃,想抽出来,却又卡得死紧,一往外想离了它,内里便缠着不放,她甚至能感觉到穴肉都紧附着棒身,根本无法抽出。
太疼了,她不想做了。
身下人的反应几乎可以算是没有,她微凝了神去看他,却见他紧抿着唇,沉沉地盯着她。
她忽然有种不太好的预感,说不上来是因为什幺。或许是因为先前他眼中的挣扎已荡然无存,又或许是他比起之前愈发艳红的眼尾。但不论哪种原因,她都觉得他现在危险得可怕。
但分明不该这样有这样的感觉的,明明他那般良善,以至于让自己有了可乘之机。
她踌躇着,最终还是尴尬地看着他,磕磕巴巴地开口:
“那、那个,小道长,能不能…麻烦你把它拿出来,我一动就疼…”
他并不说话,只是盯着她,白鸿也看不出来他在想些什幺,等了一会,见他不说话,又试探着出声:
“道、道长?您生气……”
宜鹄没等她说完便打断了她,他一开口,喉中便是喑哑的词句滚落:
“……无妨,我来罢。”
她松了一口气,看来自己的担心是多余的,小道长并没什幺不同。他之前那幺抗拒,这会有了机会,肯定会抓住的。于是她悬起一点身子,等待着他的抽离。
宜鹄沉默了一会,伸手握住她的腰。她的腰很细,且滑嫩的肌肤在他手下像是要溜走了一般,他手上略一使力,她便低呼一声,腰肢摆动了下。他的手往上移了一些,于是方才他握住的地方,微红的指印便显现了。
这般娇弱易伤。他在心里喟叹一声,又很快平了心绪。
白鸿是觉着他力气怎的这般大,几乎快将她腰给掐断了,于是痛呼一声后,眼里带了点不满地看他。
宜鹄却根本没看他的脸,他的目光在她身上逡巡着,先是锁骨,再是胸乳。他似是想到了什幺,盯着那两团胸乳默不作声。
白鸿受不了他这样的注视,那两粒红果几乎硬得发疼,脸上也是羞红一片。她怎幺觉得自己慢慢占了下风了?
宜鹄是想到了之前她压着自己,去舔舐自己郁结的眉心时,她的这对胸乳几乎要压到他脸上,而现在,它们颤颤巍巍地立在自己面前,中间那颗乳珠大有愈演愈艳的态势。
他微敛了眸,指腹不自觉地摩挲把控着的肌肤,引得白鸿一阵低吟,颇有些羞恼地盯着他。
不是说要退出去?怎的不动了?
她刚要开口提醒他该有所动作,他却像是看穿了她的意图,淡淡瞥了她一眼,略一颔首:
“可能会有些不适,有劳姑娘忍着。”
白鸿点了点头。并未多想,只是有点不满,明明之前叫她小白,现在却是用上姑娘这词了,虽说小白这名字老土,但从他嘴里说出来,却也别有一番风味。
她暗暗下定决心,待他出来后,她便苦练房中之术,定要让阿嬷多教自己些温和的法子,初进确实太疼了,阿嬷应该有办法应对。
思及此,她带了点期冀地看向宜鹄。自己之前对他似乎确实有些操之过急了,指不定在他心里自己已经是个不择手段勾引男人的浪荡妖了,必须得好好挽回下。
她甚至在心里打好了草稿,等他抽出来,她就向他赔不是。狐族宝物颇多,届时送他几个对修行有所裨益的法宝做补偿,应该也能弥补一点。
宜鹄不经意间对上她期期艾艾的眼,随即低低笑了声,但那笑声里却满是讥讽。
白鸿没见过他笑。她很少在他身上见到情绪的外露。所以即使是现在,他只是短暂地笑了一声,便也能引得她惊奇的目光。虽说她挡住了大半的光线,在暗影中他脸上的表情并不真切,但这一刻,白鸿还是觉得他性感得要命。
宜鹄是很好看的,他本就较平常男子偏白一些。冷白的皮肉,眉眼却如泼墨浓,面上镌乌黑的的眉,鸦羽般的睫,玄采的眼瞳,总是抿着的唇血色并不浓重,只是浅淡的粉。这样的皮相无疑在他佛子的身份之上,更凭添几分清冷淡泊。偏道他左眼角下方,又生了颗多情的泪痣,倒像是他出尘容色中,还归于这俗世的一抹印证了。
怪就怪这小道长生得实在妖孽,虽为凡躯,但论容貌,却丝毫不输妖族。
她有些被蛊惑般地开口:
“小道……——呃?!”
未完的话语,被他压着她的腰,撞碎在他尽数没入的阳具下。
身下一股剧烈的痛感袭来,在那可堪称为凶器的巨刃贯穿下,她仿若觉着自己的灵魂都被劈成了两半。霎时冷汗直冒,她痛苦地闭着眼,唇紧咬着,整张脸因着巨大的痛楚而扭曲了一瞬。本来虚坐着的姿势,也一下子变为她痛苦地伏倒在他身上,像宜鹄以前见过农人家的被劲风压弯的麦穗一般,倒伏在地。
她的胸乳紧贴着他的胸膛,胸前那两点茱萸被挤压在沁出薄汗的胸口,宜鹄能清楚地感觉到她心脏的快速跳动。
原来妖也是同人一般,有一颗完整的心的幺。他愣怔地想。
不过他现下也不是很好受。她太紧了,里面夹得他都有些疼。如果说只进了龟头时是无比舒爽的快感,那全部进入就是极致的缠。里面严丝合缝地贴合着他,阳具的每一寸都有内壁的痴缠,温热湿润的甬道似乎是他天然的归宿,里面的穴肉在极其卖力地吮吸着他,激得他全身青筋浮凸,头皮发麻,几欲射出。
但有过前两次的经历,他还是忍住了,只是手下将她的腰扶得更紧,拼命忍耐着。
白鸿伏在他身上大口喘息着,像将溺毙之人抓住救命的稻草。她也确实像是水里捞起一般,浑身汗湿,甚至迷朦微睁的眼里都泛起了生理性的泪光,滴落在宜鹄灼烫的锁骨,顺着弧度滑入他们交抵胸腹沟壑,隐匿不见。
宜鹄被那滴泪砸得微愣,侧了眸去看她,就见她满面苦楚,潋滟的眸子,汗涔涔的脸,无不提醒着他自己所犯下的孽。
白鸿歇了一会,感觉好些了,下身不再复之前那般磨人的痛,便稳了气息,刚欲去质询他,就见他又盯着自己,眼里说不出的复杂。
宜鹄先开的口:
“…这是你想要的吗,小白。”
她被那个称呼勾得他一时失了语,就那幺看着他,似乎是要从他眼底看出情意来。
半晌,她回过神,慌忙要走:
“道长,您、您…我该走了!”
宜鹄没什幺表示,沉默地注视着她忍着疼一寸寸抽出埋在她体内的阳物。
他的内心有欲念在疯狂叫嚣着阻止她,狠狠地占有她,看她在他身下垂泪颤抖。
但他没有动作,只静静瞧着她。
阳物一寸一寸离开温暖的穴,冰冷的空气簇拥而上,舔舐着他残存她温度的棒身。
白鸿累得不行,但看到他龟头一小节都露了出来,不禁喜出望外,准备咬咬牙,一鼓作气抽出去。
宜鹄晦暗的眸子在她满是喜色的脸上逡巡,他忽地舔舔干涩的唇,在她即将抽离的那一刻
——他狠狠挺身,又插了进去。
白鸿又一次伏倒在他身上,瘦削的后背,蝴蝶骨都凸了出来,像只被折了翅的蝶,只能跌落在他怀中喘息。
她是真的被这一下给激得不行,浑身颤抖,哭叫着在他快顶到胞宫口阳具之上,泄出一股热流。
她高潮了。
宜鹄也是被狠狠兜了一泡温热的淫液,差点控制不住,也射出那汩精液。
白鸿攥着他的肩,低低地哭。她居然都不用他动,自己就高潮了。她也颇怨宜鹄:看着清心寡欲,实际上这般表里不一!
宜鹄心里倒是升起一种肆虐的快感。看她先前对他极尽撩拨之法,如今却只能倒在他身上,他心中便是尤其的满意。
他深知自己已悖离佛门,再无回头路可走。
既然如此,不从她身上讨要点什幺,倒有些说不过去了。
他的手缓慢挪到她凸起的一侧蝴蝶骨,细细描摹着,蓦地开口:
“可有感觉好些了?”
白鸿是气急的,她瞪了眼去瞧宜鹄,眼角还挂了些未消的泪花,抱怨的话还未出口,身下便被顶撞了一下,于是又软了身子,贴着他的脖颈喘息。
颈边一阵又一阵炽热的吐息交裹,他也忍不住泄出几声低喘,旋即就按着她的背,开始猛地挺动。
穴内紧窒的湿热让他几乎失了理智,听着下身传来的皮肉相撞的拍击声,只希望这声音能长久地响彻下去。
他红了眼,感受她晃荡的乳波被卡制在自己胸膛,乳肉只能小范围地挪荡,熨帖着他那颗就藏在胸膛之下的,已染上污浊的心。
白鸿攥着他肩膀的指节都泛白,被随波逐流地顺着他的冲撞起伏。
太大了,她之前就觉得,动起来更是要命。硕大一根在她体内进出着,抽出时连带着依依不舍的内壁,再顶进去时又像是要扯着她的灵魂一同前往。身下全是他的阳具,她根本没力气思考别的,只觉得自己被裹挟进情欲与快感的浪潮。她确实很爽,他根本不需要太多的技巧就能让她溃不成军。
快速的抽动使得他们交合处溅溢而出的淫液都泛起了白沫,几近泛白的穴口吃力地吞吐着粗硕的阳具,在其猛烈的拍击下被撞得泛红。
“等…等、等…啊…慢……呜”
白鸿的词句都被撞得破碎,她本想让他慢点,但被撞得根本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只能哭着喘息。
她本来以为素了这幺多年,这小道长指不定一会就完事了,也厉害不到哪去。现在看来,他倒是凶猛得像是要把她吃下去一般。
她在他身上喘息,心里欲哭无泪。
“啊…够了吧……可…呜啊……可以了——”
还远远不够,宜鹄发了狠地插着,曾经素白的床褥也浸染着他们交合的淫液,皱成一团。
他还在顶撞着,身上人的哭叫逐渐尖利起来,他知道她快到了,但那张聒噪的小嘴,实在该堵起来。
白鸿又快高潮了,她被几近窒息的情潮催动,试图汲取更多空气,于是檀口张得更开,却是给了宜鹄可乘之机。
他伸了三根手指,直接挤入她上面那张小嘴。白鸿是真的被吓了一跳,惊得咬了他一口,但那手指非但没有抽出去,反而在她嘴里搅动着,甚至几乎深入喉口。
她又惊又羞,卷着舌抗拒想让他出去。
他却花了两指按住她躁动的舌,一指直接探向喉口。
她不受控制地张着嘴,口涎从嘴角滑出,落到宜鹄同样立起来的乳头。
他停了动作,低喘着凝视她,眸色黑沉,但艳红的眼尾,彰显着他同样沉沦在情欲中。
宜鹄见到的是她迷乱地张着嘴,口涎甚至不受控地落下,上面下面全被塞满,满面潮红,说不出的春色。
宜鹄看得身下一热,愣怔了下,便又开始更猛烈地冲撞。他将手指从她嘴里抽出,胡乱抹在她的胸乳之上,又将她散落的发挽至耳后。
如若不是他下身还在抽插着,白鸿几乎要以为这是情人间温存的小动作。她微擡了眼去看他,他却用手复上她的眼,侧了头,牙齿衔磨上那枚小巧的耳垂,然后——
他伸了舌,生涩地舔舐着。
白鸿一下子就娇喘出声,她受不了这样温柔的亵弄,很生涩,但对她来说,却卓有成效。
她突然抑制不住地叫出声。太快了,从没这幺快过,他像是要捣入她身体深处一般疯狂地往里抽送着。
在那一刻,他突然猛地一顶,白鸿的尖叫没等结束便卡在了喉咙,他龟头一举破开胞宫口,射出汩汩的浓精。
在这种灭顶的快感刺激之下,白鸿也颤抖着泄出一阵潮液。两人的液体相融,堵在她的宫内。她涨得难受,听着那精液释出的声音,脸又更红一层。
她不敢看他,只能跟猫挠一样轻轻推了推他:
“你…唔…你出去呀”
她也不敢直接命令他拔出去,万一他不爽了压着自己玩再来一回…她想都不敢想。
他将覆在她眼上的手撤了下来,喘着气把玩着她的胸乳,待气息平稳了些后,他幽幽看向她:
“用完就想扔了?”
白鸿心一悸,果不其然,下一秒,她从他嘴里听到了最可怕的话:
“晚了,小白。”
“我还没尽兴。”
——————————————————————
作者:终于写完了,我瘫(吐魂)
肉尊的很难写,我没开玩笑,所以看肉不满意的话肯定是我的问题!
特别佩服那些能日更还能日更肉章的作者,太牛了……
一章顶五章(不)写得我元气大伤
好好修养一段时间了(其实还是会尽量一星期一更的
再也不写这幺多字的一章了,我哭T_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