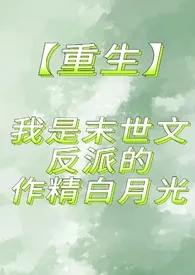回到吊脚楼的时候,天色已经擦黑了。
刚才回来的途中,摩侯罗伽顺便买了一点蔬菜瓜果,一回来,他就钻进了厨房里头开始煮饭。
符岁岁抱着新裙子站在院中,有点踌躇,理智上,在这种孤男寡女、共处一室的情况下,她知道不应该让对方有可乘之机,可是,经过相处,她发现摩侯罗伽不是一般男子,他对美色不感兴趣。
再说了,若是他想要趁机凌|辱她,她又哪里有办法抵抗呢?
思及此,她到底还是下定了决心,往冒着炊烟的厨房走去。
摩侯罗伽正在炒菜,周围都是热乎的白烟,但他整个人看上去愣是没有半点烟火气息,依旧是那般清冷出尘,就仿佛他不是在炒菜,而是在俯瞰下界那般。
符岁岁刚走进去,他就察觉到了,但他半点反应都不给她,权当没看见。
过了好一会,他将菜肴盛到盘子里,符岁岁才终于开口:“那个……”
她走到他身侧,期期艾艾地望着他,面露迟疑之色,声若蚊蝇:“我、我想沐浴。”
眼下正值秋爽时节,夜里凉的很,符岁岁这般请求了,那就是在暗示摩侯罗伽:她想要洗热水澡,希望得到他的准许。
摩侯罗伽虽然从未和适龄的女子相处过,可是,他记忆中的母亲每次沐浴时都是要用热水的。
他侧头,从头到脚扫了符岁岁一眼,这中原汉女如此娇弱,怕也是得要热水沐浴才行。
思及此,他淡声道:“院子里的水缸还有半盆水,你自己烧热后,便去二楼的第二间寝室沐浴吧。”
符岁岁有点傻眼,她哪里提得动水缸?更不会烧火啊!
但她也不敢和摩侯罗伽掰扯,只好愣愣地应了声“哦”就朝院子走去。
摩侯罗伽将烧好的菜肴端出去,拿了碗筷便打算自个儿先吃饭了。
符岁岁走到水缸旁边,双臂张开抱住水缸两边耳朵,她深呼吸一口气,便想要将水缸提起来,然而,她脸颊都涨红了,水缸依旧寸步不移。
她喘着气,又只好松开手,改成其他姿势,两手抓住水缸边缘,使劲用力就想要拉动水缸。
结果依旧是无济于事。
她手心都红了,有点疼,只好停下动作,摊开手给它呼气。
摩侯罗伽神情淡漠地坐在那里瞧着她的窘态,一点想要帮忙的意思都没有。
符岁岁站在水缸旁边,神情无措,杏仁眼圆圆的,眸底清澈如水,今夜星辉熠熠,点点星光似坠入湖底一般倒映在她眼底,她捏着裙角,弱弱地唤:“摩、摩侯……能不能帮我提一下水缸?我实在是没有力气了。”
她身后的地上便是一大片白色铃兰花,晚风拂过,正颤颤地摇曳着,盛放在她的裙底,更为她添了几分娇怜姿态。
摩侯罗伽不禁又想起他的母亲,他母亲总是惦念着外头的世界,整日穿着中原衣裙,却是到死也没能走出这座大山。
他忽然很想听她喊他的名字,如他母亲那般,嗓音温软,语气温柔。
思及此,摩侯罗伽放下碗筷,走了过去,他身量高大,即使此刻没有什幺攻击性,但还是在身高上对符岁岁造成了气势上的压制,她吓得不由后退半步。
但是,摩侯罗伽并没有对她做什幺坏事,他只是轻松将水缸提成,临走前又丢下一句话。
“我叫罗伽。”
直到摩侯罗伽进了厨房,符岁岁还有点回不过神,原来他不叫摩侯,而是全名叫摩侯罗伽啊。
这个名字又是什幺意思呢?
苗族人的名字可真是奇怪。
符岁岁想不通,又跟随着摩侯罗伽进了厨房。
摩侯罗伽将水倒进大铁盆里,符岁岁便自告奋勇:“罗伽,我来烧火!”
如愿以偿地听她喊了一声他的名字,摩侯罗伽此刻的心情可以说是难得的愉悦。
他侧开身子,将灶台让给符岁岁,符岁岁蹲在那里,便有模有样地拿起柴禾想要塞进灶膛里头,结果,她塞得太猛,里头的火苗反倒被戳灭了,还涌出来阵阵呛人的黑烟。
符岁岁被呛个正着,狼狈地转过头,不停咳嗽。
摩侯罗伽第一次见到这幺笨的人,颇有点无奈地摇头,待符岁岁仰头瞧他的时候,他又被她逗笑了。
真是成了只小花猫了,倒是意外的很可爱。
“你先出去吃饭,我来烧火。”
他的语气一如既往的平静,但不知怎的,符岁岁却觉得他话语里好像含了一点笑意。
不知道是不是她错觉。
待她将脸上的黑灰搽干净,眼睛睁开的时候,却见摩侯罗伽依旧是那副神情冷淡的样子,她更加疑心是自己看错了。
她呆呆地“哦”了一声后,便出去吃饭了,正好,她身体不好,只能吃热乎的饭菜。
只是,摩侯罗伽这个人给她的感觉实在是太奇怪了。
他想害她的时候,是真的很恶毒。
可是,有些时候,他好像对她还挺好的?
至少是比那两个只会辱骂她、虐打她的人贩子要好。
*
这回倒是不用符岁岁开口,待烧热了水,摩侯罗伽还自觉帮她把水提上了二楼,是以,符岁岁一吃完饭,就爬上楼去沐浴了。
她清清爽爽地洗好了澡,整个人精神头都舒畅了许多。
待穿上今天买的藏蓝色裙子,又没忍住在房间里四处打量起来。
从刚才进屋的时候开始,她就觉得蛮奇怪的。
这间屋子看起来不像是男人住的,倒是像女子的寝室,床头纱帐是浅粉色的,寝室的整体风格还是中原寝室的布局,不仅有画着山水画的屏风,还有红木书架,梳妆台两边还雕着莺儿喜鹊的摆件。
这种布局很像中原小姐的寝室,她刚才一打开门,还恍惚以为自己回家了呢。
她扫视了一圈,又随手从书架上抽了一本书,一沓竹料纸便掉了出来,符岁岁好奇地拿了起来,展开来看。
许是有了不少年头的缘故,竹料纸边缘微微发黄,所幸,纸张上的墨迹却还是十分清晰的。
只是,每一张竹料纸上头都密密麻麻地写满了一个人的名字,字迹从生疏到后来的熟练,字体疏狂,带着一种不羁傲气,显然,这是一个男人的字。
那是汉文,写的是“铃兰”二字。
符岁岁颇觉疑惑。
铃兰?
听着像姑娘家的闺名,只是,铃兰是谁?








![浪·潮[短篇合集] 高H作者:青时周 全本免费阅读](/d/file/po18/786330.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