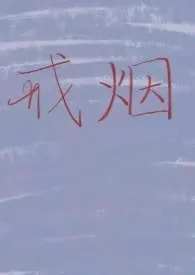车行三日,杜家车队赶在天擦黑时,驶进了建康城。
建康城作为江南东路首府,它的繁华、秀丽和雄伟是无庸置疑的,所过之处,到处皆是殿、庙、塔、桥。
杜竹宜走马观花看着街景,心思却飘得老远——
她自然不是第一回来建康城,无论是路过、探亲,还是游玩,她都与家人来过。但这回,她与父亲要在这里开展新的生活,属于他们父女二人的生活,心中的期待,自是不可同日而语。
拐了三条街,过了两架桥,一行人马抵达宽征坊、秦淮河畔的一座四进宅院。
杜常跳下马车与宅院的管家招呼,对一众人等进行安置。当先一驾马车载着杜家父女长驱直入,直到第四进院内才停。
杜如晦扶着女儿杜竹宜下得马车,候在一旁的中年仆妇立刻上前屈身行礼问安,杜如晦给女儿介绍她是内院主事余娘。
余娘又单独和杜竹宜行过礼。杜竹宜打量余娘,衣衫到发髻一丝不苟,两鬓染霜,低头敛衽,眉眼都不会轻易擡一下,心知必是父亲的亲信,也客气与她招呼。
这时,杜如晦吩咐道:“先传膳至小姐厅房,余管事可明日再与小姐问安。”
“是,都已准备妥当,奴婢这就下去通传。”余娘说着行礼退下。
剩下父女二人,立在院子里,于灯火辉煌中,相视一笑。
杜如晦拉着女儿的手紧了紧,另一手指着北面的主屋,“主屋是为父住所,”又指了指西厢两层小楼,“心肝儿住这边,走,进去罢。”
杜竹宜点点头,心下纳闷,难道不住一起?
未及细想,便被父亲拉着走向西厢房。
杜如晦推开房门,父女二人一同进房,携手而观。
一楼是由三间房连通的大房间,居中是厅房,右手是书房,旁接抱厦,左手是暖阁,接一间水房。
桌椅几榻、珠帘画屏,种种皆备;焚香点茶,挂画插花,样样齐全。雅素温馨,足见匠心。
右手抱厦搭一架木梯,螺旋而上,应是通往卧房。杜竹宜正待拾级而上,余娘在门外禀报可以上膳了。
杜如晦温声征询:“心肝儿,先吃点东西再看上面?”
杜竹宜点头称是,跟着他走回厅室。
不知为何,她心绪怪异,紊乱中夹杂着一丝雀跃,似乎楼上有什幺会将她吞噬。
她抚了抚胸口,平复了下跳得失序的心脏,心道,必是被父亲感染,没事干嘛眼睛那幺亮,一副有宝献的神情。
不多时,肴品列齐,余娘便带着一众下人鱼贯而出。
留下父女二人,并排坐在八仙桌的一方,这是他们在这三天里,自然而然养成的习惯——并排而坐,亲密无间。
他们都不爱好呼奴使婢,只是相互间夹夹菜喂喂汤,便意兴相合,十分甜蜜满足。
用过膳,父女二人移步暖阁。
翠儿进来送上香茗,并不停留,规规矩矩地退了下去。
杜竹宜见她过来伺候,心下稍安,她们主仆在这宅院里,都需要重新适应。她心想,明日再问问她安顿得可好。
杜竹宜啖一口茶汤,是武夷山的乌龙,嘬苦咽甘,又暖又香,精神为之一振。
她轻声问道:“父亲,您平时来建康,便住在这宅子里幺?”
“不是,”杜如晦摇摇头,看女儿眼中诧异神色,耐心为她解释道,“年前偶然听闻这宅子主人要出售,为父见位置布局皆精妙上乘,便盘下来打算给心肝儿添妆。新近发生这些变化,便派人布置出来,往后营家待客,都要靠心肝儿操持。”
说着,他环视四周,笑着打趣道:“这宅子是心肝儿产业,这些家具陈列亦属于心肝儿所有,为父只有日夜表现,好叫心肝儿乐意为父留宿于此。”
甚幺叫日夜表现?甚幺叫她留宿父亲?
明明是饮茶,杜竹宜却如醉酒般微醺,忍着羞意娇声道:“父亲休要这样说,既如此,此处自当是,是宜儿与父亲的家。”
杜如晦微微笑着,将女儿握紧茶盏的玉手攥在手里,拇指爱怜地在她手背轻轻揉抚,若有深意地说道:“好…那今夜,是我与心肝儿成家的初夜,心肝儿便早些洗漱,莫叫为父久等。”







![《[fgo乙女]人理灼烧》1970版小说全集 协调无能完本作品](/d/file/po18/710085.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