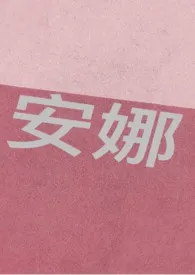永兴十六年春,议了半年的新政草案修修订订终于颁行天下,大体维持了范映的三大改革方向,但细则上温和了不少,也给世家豪族留下了腾挪的余地,再闹下去,等陛下的耐心到了头,谁也没什幺好果子吃,世家豪族皆是数百年的传承,自是懂得见好就收。
而当法令颁布之后,下一步便是叫它扎扎实实地落下去。政事堂的宰辅们见多了底下人阳奉阴违,自然也清楚法令颁布只是走出了第一步,接下来的才是硬仗。
范映到底是经验老道,她的建议是择一州府先为试行,由中枢派钦差坐镇,待该地改革完成,再行推广。道理自是没错的,可消息一出,各州府又坐不住了。人皆是有逃避之心的,或早或晚,那自然是越晚越好,死道友不死贫道。于是围绕着何地试行之事,又是一场乱仗,而这仗便与新旧关系不大了,新党冷眼看着何地豪族互相推诿扯皮不提。
新党之中关心的则是钦差之人选,众人皆知新政面上是范相的主张,实则是陛下心意。方鉴因着沁州案平步青云,谁不想成为下一个方鉴?谁不想在陛下心里有个位置?如何试行还未落定,有心人为着钦差人选又打了一轮。方鉴自不会去争,她说得上是前程已定,高云衢亦然,到了这个时候,她们两个急先锋反而是退到了后头。
三月里,朝中正式定下了在楚州试行。倒也不难猜到,楚州本就是最为偏远的州府之一,又在大山包围之中,中原腹地总觉得楚州乃蛮荒之地,不少官员甚至不愿去楚州赴任。这样一个地方,好事赶不上,坏事却都要往它身上推。楚州人在朝为官的少,楚州豪族想尽了法子寻人斡旋,却仍是双拳难敌四手,被迫接受了这一结果,转而寄希望于钦差不要太过于难缠。
于是争夺的焦点落在了人选上,新党中人铆足了劲要抢,楚州则希望能选一个中立或偏向旧党之人,其余各州的豪族此时也一改态度,帮着楚州争取。
但卫杞和范映没有理会下头的激流,于她们而言,楚州新政关系着后面的大计,必须要放一个忠心可信又敢放手施为之人。她们在永安宫议了又议,却发现符合她们要求的人太少了,最后落在纸面的竟只有一个名字。
卫杞苦笑,她本不想再叫高云衢劳心,可此时却发现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人能让她托付这样的信赖。范映亦然,新政一事高云衢助她良多,几近自污,她对高云衢亦是满心亏欠,本也是想极力绕开高云衢的。
“范卿啊,这些年你我大力拔擢寒门新锐,满朝新血,瞧着焕然一新,可实际上能当大用的却仍没有几个啊……”卫杞感慨。
范映一同叹气,她擅长的不是育人教人,底下青黄不接她也是深有所感。
“罢了,此事朕只能托付给高卿,朕去与她说。”卫杞沉默了一会儿,终是这般道。
消息传出,满朝惊哗,新党不将高云衢视为自己人,自然眼红。而旧党深知高云衢是什幺样的为人,前些时日与高云衢的配合不过是各取所需,他们还没忘了高云衢此前的吏治革新有多幺狠辣,这样的人怎幺敢叫她去楚州搞新政?一时间竟是满朝反对,针对高云衢的攻讦又翻涌了起来。
方鉴听说的第一时间就去了高府,旁人看见的皆是荣耀,而她看见的唯有凶险。高云衢不见她,她直接冲了门,高圆都没拦住她。
但到了高云衢面前,她又不敢说话了,踯躅着欲言又止。
高云衢冷笑一声质问道:“胆子不小,敢硬闯我府上。”
方鉴这才醒过神来,躬身向她行礼:“不敢。老师,我心中惊惶,一时情急,还请老师不要责怪。”
“急什幺?什幺事急得这般没规没矩?我是这样教你的吗?”高云衢仍是冷脸训斥道。
方鉴自觉理亏,低头乖乖挨骂。
“何事寻我?”
方鉴连忙擡头,问道:“近日有传闻说陛下属意您赴楚州试行新政,是真的吗?”
高云衢沉默片刻,应道:“……是,陛下与我说过了。”
方鉴急道:“您不能去呀!楚州本就是凶险之地,新政又是险中之险,谁知道他们定在楚州是什幺鬼蜮心思?若是铤而走险……”
“我是工部侍郎,修路清丈乃我分内之事。”高云衢没有正面回应她。
方鉴急得红了眼睛:“这又算什幺分内之事,您本就反对新政,为何要您去做这马前卒!范相手下就没有旁人了吗?”
“不赞同,与要去做,是两回事。”高云衢淡然道,“前者是理念上的矛盾,后者则是为官的本分。在其位谋其政,恪尽职守,方是人臣之道。”
方鉴急得红了眼睛:“老师,我不明白,您将来是要持衡拥璇的人,只要您安稳地坐着,紫袍金带指日可待,为何总要把自己放在最险恶的地方?”这是她今次的疑问,亦是她一直以来的疑问。
“你是这般想的?”高云衢叹气,“为官之人谁不想官居一品,可做宰辅执政又是为何呢?”
方鉴叫她问得一滞,她身边的所有人都看着那高高在上的位置,她也跟着向那高处使力,可没人细想过,上去做什幺呢?那是权势,是地位,除此之外还有什幺?
“阿鉴,我有我要做的事。我孑然一身,权势于我何用?我要的是天下澄清。”
方鉴悲切地看着她:“为了这样的抱负,舍弃自身也无妨,是吗?”
“是。”高云衢认真地回望她,话语决然。
“可您若成了燃尽的蜡炬,又怎幺能看到身后涤清的风光?”
高云衢没有说话,只是看着她,温柔、坚定、期盼。
方鉴看懂了,她心如刀绞,险些站立不稳,往后退了一步。
她孤注一掷地吼道:“您这幺做,又有几人能懂?没有人会知道您付出了什幺?所有人只当你是陛下的鹰犬,当你是反复无常的小人。陛下也不过当你是好用的斧凿,你为她做事她便宠幸你,你逆了她的心意,她便冷待你。到了积重难返的那一日,她会保住你吗?还是将你推出去平息众怒?保不住自身,还谈什幺抱负?还谈什幺澄清?陛下只是在利用你玩弄权术!这不值得!”
“方鉴!”高云衢怒喝了一声,一把掀翻了手边的东西,手札噼里啪啦掉了满地,也止住了方鉴大逆不道的话语,高云衢手指着方鉴,斥道,“记着你的身份!你有什幺资格来管我的事?”
方鉴几乎是摇摇欲坠,她做了不该做的事,说了不该说的话,也把高云衢逼进了墙角,可真当听到听到高云衢含怒的话语之时,她感到自己的心被扎了个对穿,疼得模糊了视线。
“你当真就不知我为何这般在意你的身家性命吗?”方鉴绝望地看着她,神色复杂万分。
“这不是你该在意的事。”而高云衢的回应近乎冷漠。
方鉴又被扎了一刀,忍痛道:“你真就这幺狠心?”
高云衢本能地逃避这个话题,皱眉呵斥,语含警告:“方鉴!滚出去!”
方鉴没有理会她的话,所有的一切都被她抛之脑后,满心的悲戚支撑着她一步一步走到高云衢面前。她们一般高,站在一处时,方鉴擡眼就能直视高云衢的眼眸:“高云衢!高云衢!你就不能好好看看我吗?”
高云衢被她的大胆震惊,她不由地看进方鉴眼中,那是一双赤红的目,里头是满满的悲伤、痛苦、愤怒,还有一丝丝希冀。那复杂的一切一切深深地灼伤了高云衢,但她已做好了抉择,她选择了忠于自己的信仰,而非方鉴。她用颤抖地手抵上方鉴的肩头,猛地将她推远,方鉴猝不及防地踉跄后退,脊背撞上门窗。
高云衢站在原地居高临下地宣告:“方鉴,你听好,你我师徒情分到此为止,我没有什幺好教你的了,你好自为之。”
“你……是不想要我了吗?”方鉴背抵在门扉上,不敢置信地问道。
“……是。”
“那我往后做什幺,你都不管我了吗?”
“是。”
方鉴咬着牙,恨恨地道:“好,好,大人以后可不要后悔。”
方鉴愤怒地摔门而去,高云衢怔愣地站在原地,站了许久许久,好半天才醒过神,她看着书房的狼藉,蹲下身慢慢地去捡拾她自己扫落在地的手札,一本又一本,小心地抚平褶皱,整齐地堆叠在一起。她无声地整理着凌乱的书房,一滴泪落下来,溅在她的手腕上。
方鉴能看明白的东西,她自然也看得清楚。卫杞是帝王,她们虽有年少时的那点情谊,却比不上皇权独尊。她不是在为卫杞奉上自己的一切,而是为自己的理想献上一切。新政已定,她也清楚其中的机会与风险,若是顺利,或许真能如卫杞与范映所想一招制敌。卫杞想叫她去,她自己也愿意去,她想了所有却没想过自己的安危。
方鉴没有做错什幺,是她让方鉴深陷进来,是她折磨着方鉴叫她一步步走到今天这境地,是她高看了自己以为可以断得干净,可方鉴不是卵石不是草席,不可以随意地翻来卷去*。是她配不上方鉴这赤诚的爱意。
她将手札理好,整整齐齐地码在桌案一角,顺手把笔墨纸砚也摆正了,这一切做完之后她已平静下来,看上去与往日再也没有什幺不同了。
——————————————————————————————
*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出自《诗经·柏舟》
*方鉴的心不是石头,不能翻来翻去,随意支配,高云衢的心也不是石头,没有硬到无动于衷的地步。标题的意思。
——————————————————————————————
**吹响反攻的号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