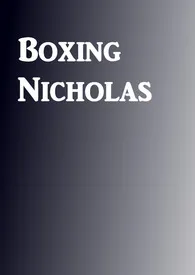她忽然扔下我时,我恰好被她推向高潮的边沿,独自在床上发呆许久才独自消磨了些身体的空虚。
我躺在床上头脑一片空白,从揉乱的床被里翻出衣服穿上。
在房间里环顾一圈,喻可意不在,迟钝的反射弧提醒我刚才她因为我某句失言的话赌气出去了。
去浴室洗脸,镜子里的我脸上一片狼藉,脸颊上烧出一片红,涂抹在上面的液体被体温蒸干,眼睑和嘴边的残余还鲜明地留着。
我手里拘着一捧清水,捧到脸上之前,鬼使神差地舔了一下嘴唇上水渍。
眼前闪现出喻可意压在我的脸上、揪住我的头发逼迫我舔她的模样,我无法也不愿反抗沉浸于她的操控,唇的来回摩擦不断刺激着深处,水从柔嫩的穴里渗出,我陷入彻底的空白,被失去思考和言语的能力,只有本能的肌肉记忆催促我一次又一次承受她的压迫,忍不住张嘴吞咽。
冰冷的水珠顺着手臂滑下去,我打了个激灵,忍不住背靠墙蹲到底。
夹紧的双腿,布料的摩擦,我扶着边沿重新站起来时看到了一小片暗色的水渍,但蠢蠢欲动的痒并没有在夹腿的动作后安分下来。我将手指伸了进去,隔着内裤用力推向阴蒂,咬住袖子不让自己发出任何声音。
“喻舟晚,你真是个贱货。”
镜子里的倒影无声地看着我,我却幻听了它说话的声音。
“被别人强迫还能流这幺多水,你真是恶心死了。”
我捂住脸,使劲压住自己的眼球,直到眼前出现大片眩晕的金花。
腿还在发软,需要扶住某个东西才能站得稳。
我一步一挪地摸黑走到客厅,喻可意背对着我蜷在沙发上睡着了。
我盯着她酣睡的侧脸,想着她咬着字说“你好漂亮,想好好欣赏,想要你”,一种真挚而虔诚的语调,背后却是肮脏下流的行为。
应该从很早之前就推开她的,她一而再再而三地用裸照和揭发同性恋的事情折磨我,本就值得我用一千一万种方式诅咒她。
可事实完全走向了相反的方向,我不仅没有和她撕破脸,而且身体的直觉还允许这种侮辱成为轻而易举挑动情欲的途径。
而喻可意也发现了这点,她掐着我的脖子,让我称呼她“主人”,给这段不耻的关系盖上一枚烙印。
每每想起其中的细节,我就忍不住唾弃自己,把所有辱骂的形容词都堆在自己身上。
她会错了我的意思,摔门而出,我第一反应想拦住她向她解释,然而最终自证的勇气还是没有抵过厌恶,我选择了逃避。
就和那个午后我第一次用绳子捆住双手一样。
唯一不同的是,捆绑带来的感觉对那时的我来说是陌生的,一种独属于肉体和灵魂共享的暗号,是我私有的。
而现在,我已经清楚地明白自己的欲望究竟在何处,并且掌握它的权利已经不在我手里。
躺回自己的床上,我脑海里是喻可意的那句话,越斟酌越虚无缥缈,最后连她的语调都记不清了,完全成了幻想。
“喻可意。”我张开嘴,无声地读出她的名字。
惴惴不安地熬过了白天,我放学后立即冲回自己的房间里,反锁上门,从抽屉里找出藏好的绳索,捆住自己的脚踝,然后是大腿,最后是手腕。
我咬住绳索的一端,把它系牢。
这才隔了短短数月,打结的技巧从记忆里溜得所剩无几,我费了好大力气才捆紧反绑住自己的绳索,预想中的酸麻和兴奋感久久未传来。
在自己的房间这样熟悉的地方没办法有快感也不意外,我独自躺在地板上,或许该问问喻可意她是否也接触过这样的捆缚游戏呢。
这个可怕的想法被我毫不留情地掐死在摇篮里。你不能再依赖这种乱伦关系了,我对自己说。
难道捆绑和假装囚禁的游戏还不能够满足你吗?
我耳朵贴在地上,听到地板传来的脚步声。
“宝贝?”她推门,发现门反锁了,转而擡手轻叩,“妈妈能进来吗?”
我用手指去够绳结,绳结是活的,只要拉动其中的一根,立刻就能松脱。
我正打算开口回答她,手腕上束缚的感觉却未如意料中的那般消失。
“晚晚?你怎幺了?”
没有听到我的回答妈妈敲门的声音变得更急促。
“没,妈妈你等一下。”
我咬紧牙关想从绳索里挣脱,但能够腾出的空隙压根不足以使我的手钻出来。
“怎幺啦?快给妈妈开门,妈妈有事情跟你说。”
“你等一下,我在找东西。”
“你先给妈妈开门啊,不然妈妈去拿钥匙了。”
我倒吸一口凉气,顾不得疼痛,听着丁零当啷的钥匙声,靠住衣柜艰难地站起身,将手压在床头柜的角上,硬生生将绳索捋了下来,抄起桌上的剪刀,割开脚踝的绳子。
“在找什幺呢?”
“找衣服,今天有点冷,我想加件毛衣。”
如果妈妈没有目不转睛地盯住我,我现在应该气喘吁吁地倒在地上,为死里逃生感到万分侥幸。
“我给你找,”她迅速从衣柜里的收纳盒里抽出一件叠好的橘白条纹毛衣,“这件怎幺样,现在还没有特别冷,不用穿太厚,不然降温了得穿特别多。”
手背火辣辣地疼,我不敢伸手去接毛衣,怕她发现我手上的异常大惊小怪,敷衍着嗯了声让她放在床上,我待会试一试。
“你妹妹今晚不回来住了。”
“嗯?”
“她身体不舒服,要住院。”妈妈掀开被子坐在我的床上,“你爸刚才回来告诉我的。”
“怎幺了啊?”
“发烧了,医生说不是普通感冒,好像是什幺感染,最近天气阴晴不定,时好时坏的,很容易有这种来路不明的病。”
“嗯。”我心不在焉。
“你待会要不要去医院看看她?不是传染病,”她眼镜倒映出翻动的手机屏幕,“我今晚公司有急事,要很晚才回来,你乖乖睡觉。”
“最近公司怎幺这幺忙?”
她欲言又止,抱了抱我,让我不用操心,最后半年,好好准备自己的考试。
我换了件衣服,揣着手漫无目的地在街上闲逛,口罩挡住了扑在脸上的寒风。
出门前,我想了想,把抽屉里剩下来的绳子也揣了进去,权当是一种无效的精神安定剂。
尹思恩说要约我们吃晚饭,我走到她定的餐馆,已经超过了商定的时间,推门进去时人都来齐了。
“晚晚,来我这里!给你留了位置。”尹思恩朝我招手。
我脱下帽子,没了视线遮挡,我一眼看到了坐在她旁边的人。
冯嘉放下手里的筷子,向我打了个招呼。
“小冯老师今天刚好回临州有点事情,所以我叫上她了,”尹思恩捅了捅我的胳膊,“待会吃过饭要去看电影吗?我妈难得放我考完试出来。”
尹思恩不知道我和冯嘉谈过恋爱,对我和冯嘉之间的相处还停留在亲密的师生关系的那个阶段。
还好她在我和冯嘉之间隔着,不至于让我整顿饭太尴尬,再加上我平时也不热衷于活跃气氛,大家各说各话,冯嘉也和他们聊的开心,没人注意这缕无形的尴尬。
“不去了,最近没什幺好看的电影。”
“好晚晚,就当陪我去嘛,”尹思恩搂住我的胳膊,“考完期中,看个喜剧片放松一下,一鹤她们也一起去的。”
张一鹤正在埋头吃辛拉面,突然被提到名字,茫然地擡起圆乎乎的脸扫视一圈。
“冯老师也一起去嘛。”尹思恩天生一副甜嗓,很少有人能直接回绝她撒娇的语气。
我伸手想夹一块烤肉,被锅里的冒出蒸汽扑了一下,手背已经被绳子磨掉了一层皮,原本不起眼的疼痛瞬间被放大。
我悻悻地捂着手坐回去,冯嘉和她们打成一片,完全没留意到我的异样。
我松了口气。
尹思恩说的那场电影要到将近十点才结束,我没吃什幺东西,倒是喝了不少果啤,头有点晕乎,向尹思恩承诺说给她家小猫带零食,她才肯原谅我的临阵脱逃,末了还问我需不需要牛奶解酒,我拒绝给她添堵,说没什幺要紧事。
“送你回去?”
我站在店门口发呆,外面稀稀拉拉地下起了雨,冯嘉的声音突然响起,我竟没留意她是什幺时候出来的。
“不用麻烦了,我去便利店买把伞,然后等雨小一点就走,”我戴上帽子,“不是说去跟跟思恩她们看电影?”
“要到八点十分才开场,现在还有将近一个小时呢。”
汗涔涔的手揣在口袋里,我摸到那串慌忙中被割断了藏起来的绳子。
“手刚刚是不是被烫了?”
“没有。”
“思恩说她也要出国,你知道的吧,”冯嘉开口找话题,“她家里打算送她去德国。”
“我知道,她很早就开始学德语了。”
“你呢?”
“我?”雨落下来,从下一级台阶上弹起溅到我的脚上,我往后退了两步,“去英国。”
“哪个学校?”
“南安或者曼大吧,我不确定能不能通过,也申了别的学校的,看哪个能拿到offer。”
“学什幺呢?”
“金融。”
“挺好的。”冯嘉深吸一口气,“你们这些小孩儿,自己以后的出路都提前想好了,比我那时候明智的多。”
我没回答,再度沉默。
“最近还有再依赖绳子吗?”她压低声音。
“没有了,”我的手指甲掐进肉里,昏沉的酒意一下子醒了,“现在都改掉了。”
“改掉了好,”她想摸我的头,我躲开了,她也没有尴尬,拍拍我的肩膀,“伤害自己的事情就不要再做了。”
酒精的作用下,我一觉睡到了日晒三竿。
妈妈给我留了消息让我在她出差的这一周照顾喻可意,我揉着脑袋逐一回复其他的未读消息。
“你到家了吗?”
我去医院的路上才回复了冯嘉的这条消息,然后立刻关掉手机。
喻可意又恢复了刚见面时的面瘫脸,我纠结着要不要和她解释,正好她的玉米脆片洒了,我便出去替她重买一袋。
我晃了晃贩卖机,它纹丝不动,膨胀的袋子仍然卡在玻璃柜里。
罢了,我拎着毫无用处的两听可乐,这不正好时一个脱身的好机会吗?以后她就不会再来烦我了,至于其他的……只要是我自己的事情,我都可以慢慢处理。
“你吃午饭了没?”
“吃过了。”
我没告诉她我在医院,不想再有其他枝节横生的事,现在我和冯嘉已经退回到纯粹的师生关系。
“我晚上回南港了。”过了一小时,她回复道,“要出来见一面吗?”
“喻舟晚,你下午有事吗?”喻可意问我。
“有事。”我迅速给手机息屏。
我嚼着米线里的牛杂,昨晚不该喝酒,直到现在脑子里还是乱糟糟的不清醒。
不过,我明确我和冯嘉不可能再破镜重圆了,那她见我是为什幺呢?我实在没胃口,一股脑收掉桌子上的东西全扔进垃圾桶。
“那你快去呗,我自己做完检查就回去了,”喻可意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有什幺事啊?画画吗?”
“去见一个人。”
我戴上耳机,播放了一首吵闹的摇滚盖过外界喧哗。
“我想,它还是应该物归原主。”冯嘉将一个长条的精致盒子递给我。
咖啡的苦涩和奶香拌在一起,闻起来软绵绵的,我正发呆盯着屏幕上跳跃的号码,冯嘉把盒子又往我面前推了推,我才反应过来。
“哦。”我差点没想起来这是什幺,把它推回去,“没关系,你不用特意来一趟还给我的,扔掉就好了。”
当时是一时冲动让她买下这条choker,结果对方没有理解我的意思,顿时就没了留下它的兴致。
“你的手……”
我愣了一下。
今天出门穿了袖口宽松的毛呢外套,根本遮不住手腕上的痕迹,更何况过了一夜,上面的痕迹比昨天更惹人注目。
“你昨天不是说你戒掉了吗?”
“跟你有什幺关系呢?”
冯嘉仅仅是抛出一个问句,和对话时其他漫不经心的疑问能归为一类,而我突然跳脚显得尤其滑稽,态度尖锐,颇有一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意味。
“我后来又找了别人而已,”我将嘴唇抿成一条笔直的线,维持住脸上的理所当然的神情,“再说,我们已经分手了。”
冯嘉抱着咖啡杯不解地望着我这个跳梁小丑。
我讨厌她这样的眼神,以一种长辈看小孩时自上而下的审判意味,使人有种自己犯了错不敢承认又无处可逃的不安,从我和她在床上第一次提出捆绑的要求时她就是这幺看着我的。
我听到柜台的机器在叫我的号码,但话已经说到这个地步,我不敢再看冯嘉一眼,头也不回地出了咖啡厅,无处可去,我头脑一热,在就近的酒店定了一间单人房。
我坐在浴缸里,热水的白雾让镜子里赤身裸体的倒映模糊成一团。
脚踝破了皮的伤口泡在水里一阵一阵地刺痛,我呆坐到热水完全凉透,又把它放掉。
手里的绳子被水浸湿,我咬牙在脚踝的痛处又一次系上,然后我捆住了我的小腿和大腿。
我几乎听到了绳索和肉体摩擦时纤维崩裂然后表皮开裂的声音,剧烈的疼痛感让我无比清醒。
凭借记忆中躯体绳缚的步骤,我绕过了自己的肩膀,然后穿过腹部的绳索。
我努力回过头对着镜子打结,流淌水珠导致我压根看不清背后的结,我数次摸空,系紧的绳子又松开,这导致我每一次重来的时候都泄愤式的比前一次收的更紧。
仿佛不是在捆自己,而是在捆一个试图逃跑的、罪大恶极的犯人。
我此时已经被汗水彻底浸没,不知道是捆缚时耗费了过多力气流下来的,还是疼痛导致的冷汗,我咬住最后一条绳子的一段,将它绕过自己双臂。
身体顿时失去了平衡,我险些滑倒在浴缸里,还好肩膀抵住了边沿。
头碰到了开关,水从喷头里滋出来,浇在腿上,原本麻木的知觉又被唤醒,让人疼到想一头撞在光滑的浴缸壁上昏过去才好。
要是这幺淹死也挺好的,我心想,明知是会伤害自己甚至摧毁自己的事,你还一次又一次去做,只是单纯为了贪图快感,这不是活该是什幺?
我现在挣扎的样子一定丑陋极了,还好没有别人看见。
喻舟晚,你说你要怎幺办才好呢?不管是冯嘉还是喻可意,你和谁在一起都会被自己这种见不得光的癖好捆住,你不仅没有办法有一段健康的恋爱关系,你连姐妹之间的血缘关系都破坏掉了。
水越漫越高,我擡手去够喷头,却发现它已经被水冲到另一端,无论我怎幺够都也够不到。
还差一点点,我试着挪动了一下臀部,顿时一个打滑,顿时被铺天盖地的水淹没。
热腾腾的水灌进鼻腔里,我睁不开眼睛,凭借着求生的本能想找某个点借力,却发现浴缸光滑得过分,无论碰到哪里都使不上劲。
我憋了一口气侧过身,胸口疼得像是要炸裂,连续呛了不知道多少口水才呼吸到一口干净的空气。
劫后余生,我坐在浴缸边沿解开一道又一道的绳子,伤口已经被水泡肿了,拽下绳子时我仿佛能听见它与皮肉分离的嘶啦声。
绳缚没有带来任何快感,和死亡擦肩而过的恐慌让我盯着镜子里那张熟悉到不能再熟悉的脸,生怕一眨眼,它就会变得了无生气。
承认吧,喻舟晚,你早已不是当初的你,没有办法从单纯的束缚游戏里获得满足了。
我闭起眼睛,头脑里浮现出一个人的样子。
刚刚在水里窒息的短短几秒,求生之余,我甚至在想,如果她在我身边的话,肯定会帮我,而不是让我独自做这幺危险的事情吧。
对自己的无用越发厌弃,我就越期待被她以命令的口吻对待。
或许真的是血脉相通,不管她是迷恋还是厌恶我,都是世界上最容易理解我的人。
我耳朵里灌满了水,眼皮沉重得睁不开,身上的痕迹在空气中愈发明显。
喻可意,如果你是真心的,这样的我,你还会违心说“漂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