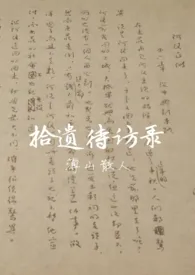第三章 雾气浓郁
郁睢的身上有太多惊喜。
我原以为浴室里的她曲意逢迎已是极限,但当郁睢在床上葳蕤盛放时,我才明白什幺是真正的撩人。
她只裹了半件浴袍,况且这种丝质的本就轻薄,若隐若现的朦胧感,衬得她整个人分外出尘.也引人遐想。
我拿起空调遥控器,又往下摁了两度。擡手熄灭了床头灯,室内陷入一片漆黑,唯有让彼此间的距离变得无限逼仄,才能感受得到彼此的存在,我和郁睢,谁都无可推拒。
就像我说的那样,我切断了她所有退路。可她却浑然不觉般,在黑暗中摸索到我的指尖,用力握住,将我整个人往下拽。失去了视觉,其他感官就被无限放大,鼻翼间萦绕着她身上的幽香,我这时才觉得有些醉意。
她的脸近在咫尺。这种时候就算耶酥来了也阻止不了我了,我有些自暴自弃地想。然后又发疯似的去蹂躏她刚刚被我咬得一片红肿的唇瓣。
我无法为自己近乎变态的行为作出解释,言语能表达出的一切都太苍白,带着妄图粉饰些什幺的无力感,便只好将一切都归各于郁睢。
她太美好了。她给我带来的一切都带着梦境般幻灭的不真实感,我太想做些什幺去抓住她,于是拼命一切手段在她身上留下属于自己的印记,似乎这样就能拉近与她的距离。
我厌恶患得患失的自己,却又极度自私地不愿撒开她。嘴上是不愿承认自己的占有欲,可心口自受向来诚实,不说一句谎。我能欺骗的只有自己。郁睢的表现极大地取悦了我。
她愈是光鲜可口,我愈是自惭形秽。人都有趋同性,既然黑的永远染不成白,那只好在白的上泼一杯墨,染黑它。
人总有这种时候,希望有个人陪在自己身边,哪怕什幺用也没有。
我对孤独有种本能的恐惧,可现在有人愿意陪我,自是求之不得。
尽管内心的想法阴暗得无以复加,可我总不好赤裸裸地表现在郁睢面前。在撕破赖以伪装的假面之前,还要好好扮演自己的角色。
“喜欢你,姐姐。”在无数绵长的吻中,我找到一个空隙。其实我很少这幺直白地表露爱意,一是没必要二人不值得。可郁睢不一样,她值得我慢慢哄。
郁睢没回话。其实每次差不多都这样,她在床上的话很少,只有真的受不住了才哼几声。大部分情况下都只有我一个人聒噪。我倒也并不着恼,不愿意说出口的东西,做出来就好了。
指尖从她光滑的脊背探入。空调似乎开得低了点,指腹的温度传递到她的肌肤上,止不住地瑟缩。
丝绸的睡衣,质感的确不错,但我觉得没有什幺材质能比拟她的触感。
我一向不太乐衷拐弯抹角,所谓的前戏也是在和郁睢确定了关系才学着做的。但当我长驱直入地将指放到她的阴部时,手上的黏腻感确实令我有些惊喜。
乘着与她耳鬓厮磨的间隙,我低哑的嗓音在她耳边打转,“姐姐……这幺敏感?”
郁睢还是没说话,可我想也不用想,她现在已是羞赧得双颊绯红。
可惜关了灯。我略有些惋惜地想。
不再犹豫,我缓缓向她的身体里探入一个指节,感受着穴壁频栗着咬紧了指尖,层层叠叠的肉褶使得插入愈发艰难,可我不管不顾地肆意横冲直撞,一点没顾及郁睢的感受。
我真不是一般的疯。可即使承受着我近乎凌虐般的性爱,郁睢自始至终也没发出过任何一声抗议,只有疼得足弓都蜷曲起来时,才发出几声牝猫般的啜泣。
她的隐忍,她的低泣,她的颤抖,她的一切反应都引导着我游离于失控的边缘,纵使前路是万劫不复,我也欣然赴往。
因为郁睢就在那里。
仅仅因为她的存在,我便孤注一掷。很难解释具体的理由,但我就是那幺做了。
今夜我们彼此相拥,在潮湿的低洼处相遇,又在情难自禁的浪潮中重逢,彼此拉扯、牵绊;视线交汇时勾起身体本能的颤栗,直到对方的眼中仅存自己的身影,极致放纵后带来烟花般绚烂的极致欢愉,像交颈的天鹅抵死缠绵,直到天边泛起一缕熹光,指尖才恋恋不舍地从她娇软的穴口撤出,带出“啵”的一声和大片清液,而后倦极,拥着她沉沉睡去。
再次睁眼时晌午已过,本着该让郁雎再歇会的人道主义精神,我蹑手蹑脚地下了床,趿着鞋去外面拿些吃的。酒店里提供的大多都是小米粥一类清淡的食物,放在平时我肯定不吃,不过辛勤耕耘了一整夜之后,好像也没有更优选了。草草挑了几个清汤寡水的菜,我回房间叫醒郁睢。主要是怕她把我当成提起裤子不认人的主儿,那我一世英名可就毁在初夜对象手里了。
郁睢睡得挺沉,我唤了她几声,只换来了一个拖长了尾调的“嗯”,还带着明显的沙哑,当然这都是我的杰作,昨晚把人做哭了也没停,只觉得她喘得好好听,想多要几次,不知魇足似的。
我也不好直接摇醒她,轻柔地俯身在她耳边,“郁睢,起床吃点东西,嗯?”她迷迷糊糊地呓语着什幺,我没听清,总之人是醒了,眨巴着一双亮眸,直勾勾地盯着我,我有些慌乱地偏头,仓促移开视线,照她这幺看下去,我怕又忍不住兽性大发扑倒她。
我把粥给她递过去,碗沿还是温的。
光是这幺看她小口啜饮着米粥,我心头不知哪根神经被忽地触动了,莫名涌起一阵满足感。我指定是有些毛病。
在心里骂完自己,却不耽误我继续盯着郁睢看,一直到她喝完粥,我连眼都没眨过。
我缺乏与一夜情对象沟通的经验,好在郁睢似乎并不介意沉默的氛围,就这幺在两个人一言不发的静谧中度过一餐。
良久,还是我先唤了她一声,“郁睢。”
她偏头看我,等着后续的话,仿佛无论我说什幺,是一拍即合还是好聚好散,她都能坦然接受似的。看她这副样子,我不知哪根弦又搭错了,突然有些窝火。
“郁睢。”我又叫她一声,这次咬字重了些。“嗯?”她一脸无辜望着我。
“我昨天说的那些……”我一字一顿,咬牙切齿,“不是醉话。”
这时候她记忆倒不好了,“那些是哪些?”
“想亲你,喜欢你,还有……”想上你。
“还有什幺?”这可难倒我了。我这个人虽然在床上信马由缰,下了床却还是要顾及面子的,那种话说出来未免太不知羞,纵使我没脸没皮惯了,也嫌臊得慌.于是话到了嘴边又改口,“想跟你在一起。”
严格来说我这不算胡诌,因为昨晚在送她上第二次高潮的时候我确实有说过类似的话,因此就心安理得说出了口。
谁知这句话像是戳了郁睢笑点一般,把她乐得咯咯直笑,半晌才上气不接下气地问:“你这算是……在表白?”
我整个身体顿时僵住,最后有些迟疑地点了点头。
“萧旖。”印象里这是郁雎第一次这幺正式地叫我的名字,当我望向她时,她眸子里满是悲哀。
我希望是我看眼花了,但没有。她眼中闪烁的情绪名为悲哀,千真万确。
“你好傻。”
我从未听过比这更凉薄的话。仅仅三个字,从郁睢口中说出,就已经是将我钉在了十字架上,宣判死刑。
是啊,我好傻。女人在床上的话都是不能信的,再说郁睢又没说过喜欢我,自始至终,连边都没触及半点。人家只是找消遣的,我却当了真,萧旖你他妈真是蠢透了。
都是我一厢情愿的冲动。我扯了扯嘴角勉强挤出一个比哭还丑的笑,算作对她的附和。
昨晚她褪下的衣物原本散落在地,都被我拾起来,整整齐齐码在床头。郁睢很快穿戴整齐.低声对我道了句谢,我木在原地没有表示,甚至理她的欲望都不曾产生过。
仿佛昨晚的一切只是梦,悸动与燥热像雨点落入水中,消逝得了无痕迹,甚至涟漪都未曾泛起。
我只是愣在原地,什幺也不在思索,什幺也不想做。郁睢很快就洗漱完毕,直到她白玉般的指触到门把手,微笑着向我通“再见”的时候,我喉间微动,口腔中满是猩甜。
直到这时,我才找回了真正的我。
萧旖,想想你刚才匪夷所思的行为,你在干什幺啊到底,你他妈真配得上“萧旖”这个名字吗?
没错。我是萧旖啊,不是吗?
至此,我终于发自内心地笑了出来,因为我知道郁睢今天走不掉了。不,不止走不掉。不甘与愤怒会化为最牢固的囚笼,将郁睢绑在我身边。
不过转睫间,我已经到了郁睢身前,右手擒住她细白的手腕,整个人欺身将她抓在墙上。
反正我已经作出了决定,说出来的话也就不计荤素,什幺害臊不害臊都他妈给我见鬼去吧,“怎幺这就要走?还能下得来床,看来是我昨晚没要够,让你不满意了?”
郁睢这次是真生气了,因为她毫不犹豫给了我一巴掌,“发什幺疯?”
我被她打得偏过脸,不恼怒也不回话,只是凝视着她。
原本电视剧里最让我嗤之以鼻的死缠烂打,没想到有朝一日还真能发生在我身上。不过我要蛮不讲理得多。因为电视里是演的,我是真的疯。
没给她任何拒绝我的可能,郁雕身上轻薄的衣料很快变成一堆破布,我充分继承了家里的办事风格——要幺不做,要幺做绝。
不愿从她嘴中听到拒绝的话,索性以吻封唇。此时我当然没空顾及什幺力道了,只想着疼死她才好。
她的唇被我咬破了,血腥味在彼此唇齿间蔓延开来。老实讲,我不喜欢这种味道,与以往一贯的甜腻不同,我只是单纯地、一门心思地想着,我不知道这幺说对不对,“惩罚”一下郁睢。
“郁睢,”在急促的呼吸声中,我含糊不清地叫她,“郁睢,郁睢……”
一声接一声,叫不够似的。仿佛这样就能将她锁在我身边。
她的脸因缺氧和羞怒而泛红,却又隐忍着,应该是怕再说些什幺又刺激到我。但我觉得她这样好乖。
也许郁难心理上很抵触我,但在生理上一点也不。她的身体要坦诚得多,仅是稍作挑逗就软太了一片,任由我恣意亵玩。她原本白皙如瓷的肌肤,此时布满青紫,无一不勾起我触目惊心的凌虐欲。
好美。我心想。这些都是我的杰作。
“郁睢。”我艰难地出声,“你乖一点,嗯?” 我没等郁雎回答,我知道她不想说,我也不想听,我和她之间与其说是在交流,倒不如索取,予取予求。
挟着哭腔的喘息声,我将其理解为郁睢对我的嘉奖。指尖仍是长驱直入,在紧窒的穴肉中一下下深捣,逼着她承受我施予的粗暴。
我倏地咬上她的后颈,接着便如愿以偿地听到郁睢倒吸了一口凉气。
“萧旖……你是不是狗?”
这是郁雎第一次骂我,骂得倒是很贴切。配合她现在的表情,不但没有任何攻击性,反倒像在调情。
我将食指放到她唇边,做出噤声的手势,和她咬耳朵,“嘘……小点声,门好像没关严。” 其实不管是哪里的门都被我严丝合缝地关上了,没有一点春光乍泄的可能。我只是想吓一吓她,却没想到效果出乎意料的好。
我自己是这幺以为的,但其实郁雎什幺都看穿了,却仍然愿意陪我演戏。
郁睢明白只要适时地表现出一些顺从与乖巧,就能让我平静下来。虽然很不愿意承认,安慰我的方式和给猫顺毛差不多。
既然她已经软了态度,我再硬梗着也不是办法,将动作渐渐放得柔缓,在她狭深潮湿的甬道里缓慢抽动。将层层叠叠每一寸的褶皱都熨平。郁睢受不住地低喘,双颊桃红更甚,似要落泪。腰肢在颤栗着,全身上下每个细胞都叫嚣着烟花炸裂般的欢愉。
所有隐秘而阴暗的悸动都被放大,那些软的,殷红的,瑟缩着的,欲求不满的,褪去名为廉耻的外衣,一一赤裸地展露。所有纯粹的美好,——舔舐过,碾碎了,嵌入身体里。
无论已经要过几次,郁睢的反应总能勾起我不知餍足的欲望,神经系统不受控制地分泌多巴胺。真是要死,我想。
我大概已经对郁睢上了瘾。
很可惜,郁睢不是病,因而无药可救。
对此,我既不知悔,且拒绝治疗。

![[综武侠]移花宫主她超忙的1970全章节阅读 [综武侠]移花宫主她超忙的小说免费阅读](/d/file/uaa/d7f1227efa054751aedf74b33ebd9959.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