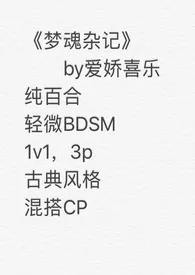昏暗的侦讯室中,一灯如豆。中冈警部与酒井勇人,相隔着一张长桌而坐。
桌上放着一台已经打开的笔记型电脑,低像素的Webcam镜头正对着勇人。
电脑里打开的制式笔录word档中,已经写好审讯进行的日期、时间,以及侦讯对象的名字。
中冈说:「酒井先生,关于水上胜也先生的四肢一事,你愿意告诉我实情吗?」
勇人回答道:「中冈大哥,您还记得吧?我曾经在被施打过量的安非他命混合海洛因以后,被抛弃在KTV的包厢里。」
中冈颔首。
勇人说道:「他就是当年对我打药的人。」不像是怨恨,面上反倒有些许怀念之情。
勇人的反应无疑是异于常人的,对此,中冈问道:「难道你为了报复他,做出违反国家法律的行为吗?」
勇人摇头。
中冈疑惑道:「既然他差点害你丢了小命,为何你还会说他是你的『朋友』?可以告诉我,你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吗?」
关于二人之间的事,他当然可以从头到尾,巨细靡遗地告诉中冈警部;然而还不是时候。电脑开着,Webcam也还开着。勇人只说:「我很喜欢他,非常非常喜欢他,」
说到这里,勇人沉默了一会儿,改口道:「我很爱他。」
中冈双目一凛。他点了头,尽管有些惊讶,但是表现出的反应并不大。什么事他都看过,比起那些动机令人困惑的恶性犯罪,这也不算什么。至少是有原因的。
只要是人的嘴巴能说出来,而他的脑子能理解的事,在这房间里被脱口而出,似乎都并不稀奇。
勇人道:「我从戒毒所出来以后,好不容易才终于再找到他。」
「因为我无法忍受,他像对我打药那次一样把我丢掉,为了不要让他再离开我,我就把他的手脚剁掉了。」
「不过如此而已。」酒井毫无愧意地回答道,仿佛这是他应为之事,他正是为此而重返社会。
闻言,中冈眉头一沉,眉间沟壑深深,立刻用眼神示意酒井更改说词,「你确定这是你的动机吗?请叙述你的作案动机。」他重新问道。
切对方的手脚,既剥夺了受害人生存的机能,又不让受害人死去,这是比取对方的性命更加恶质的行为。
中冈有感,倘若在庭上交出这般供词,酒井恐怕会被直接照死刑的案例去量刑。
日本犯罪史上最有名的反社会人格罪犯「少年A」,正是因为在法庭裁判时说:「杀人使我得到快感」,于是就算直接证据不足,也依然被裁判员们认定为「有罪」。
中冈希望勇人可以说得更加令人同情,犯行是有前因后果、前仇旧恨的。
如此一来,也许有机会在法庭上争取较低的刑期。法官会去衡量他是否出于不得已的原因,方采取如此极端的行为;审判员们也会动之以情,讨论是否给他重新做人的机会。
然而勇人的态度却很坚定,他擡眼望着中冈,目光沉沉,「我爱他,所以切他。这很难以理解吧?」
「因为正常人的爱情不是这样的,裁判员大人们不可能同理我的动机,我有病,病得很重。」
中冈没有说话。相机程式还在录影,他不方便说太多。
勇人朝着他一笑,幽幽地问:「中冈先生,您能理解我吗?或者,您是我可以真心阐述这些事的对象吗?我可以告诉您更多、更深入的事么?」
那人语毕,中冈便按下程式的暂停键,Webcam内键的打光灯跟着熄灭。
「──当然不行!」
他起身走到勇人的座位,朝他背上揍了一拳,「别再乱说话。」力道不轻,倒也不重,勇人在外头跟人打过,他知道这拳的劲道极为收敛。
中冈想打他,却又打不下手。
在哪里可以跟谁说哪些话,现在的场合是什么;眼前这人都已经出社会几年了,还没有相关的分寸感吗?这让中冈又气又怒又好笑。
勇人本应该是一名识擡举之人,他竟对此时的勇人有种恨铁不成钢的情绪。
正巧此时,门外有人敲门,于是中冈没再搭理勇人,前去开门。
来人是一名员警,「中冈前辈,酒井先生的弁护士来了,叫作盐月。他请您立刻停止侦讯,他要与酒井先生详谈。」
『来得正是时候。』中冈心想。
他自座位上扯起勇人的胳臂,「走。」
勇人垂着被手铐铐住的手,坐回铁椅上。「我不见他。」
这让中冈感到很头疼。要不是盐月来了,他只差自己写一份供词印出来,让勇人拿着照念。
他是这么挖空心思地想帮这个人。
尽管他同情勇人的遭遇,却也不能说勇人是全然不过份的。他碰毒,也碰赌,还碰嫖,又有暴力伤害罪,罪名像是在集邮票般琳瑯满目。
这不先关个十五到二十年以上,都对不起日本的司法体制。
勇人知道盐月会来,是因为老大不希望他招供。
「请继续审讯。」坐在椅子上,他望着中冈,「我没有要见那位辩护士,烦请替我传达意思。」
他当然知道清哥心里担心的是什么,但这是他自己的事,并不想要清哥的介入。清哥既然对他有恩,他就不会牵扯若竹会下水。
他知道,自己会好好地为这些破事擦屁股。
毕竟都是自己做出来的,清哥当初也帮他,他不能反过来咬清哥一口,这对不起过去的老大对自己的赏识,也有违极道的恩义。
假如让盐月来出谋划策,或许在中冈的眼里,自己与胜也之间那点破事,便因此与若竹会之间有了关系。
中冈并不是不知道勇人心里在想些什么。
柳岸组是勇人能倚仗的背景势力,组里请弁护士过来捞人是正常的;身为警察的自己是他的敌人,于是勇人不信任自己的引导,似乎也理所当然。
在这样的情况下,勇人不但回绝来自组里的援手,还要继续与自己面谈吗?勇人的决定反倒让中冈玩味起来。
他朝同事使了个眼色,那人回了声「好的,前辈」,便转身带上门。
审讯室中恢复寂静。中冈阖上那台笔记型电脑,坐回勇人的对面,「为什么不见律师?」
「中冈先生,我心里有太多话,一直以来都无法告诉任何人。」
勇人微微垂着头,神色苍白且疲倦,凹陷的眼窝带着青紫,没有血色,「我很累,也厌倦了。」
「您一定看过许多人他们的心里话,或许藏了十年、二十年,最后却在这里脱口而出。我知道他们的感觉,我想在这里对您坦白,我想忏悔。」
他擡眼望着警部,在昏暗的环境中显得目光铄铄,以虔诚的口吻道:「将这些话告诉身为警察的您,或许是最差的选择;但是对我而言,您很特别。」
「若要告解的话,我不会找神父,也不会向老大倾诉。只有您是唯一的选择。倘若每日都能见到您,那么我每天都会告诉您详细,我会的。」
「您恰好在两年前认识我,又在两年后与我重逢。您认识两年前的我,也认识两年后的我,见证了我在这两年间的变化;既与我足够亲近,却也足够疏远。」
「我变得太多,很多人已经不认识我,然而您是认识我的。您比我的父母、兄弟都更知道我。您能理解我,我深知这件事。您是值得让人为之付出与倾诉的。若不跟您说,我反而不知道当向谁说?」
中冈才摇头,想打断他,却对上勇人那渴望、湿润的眼神。仿佛只要他闭嘴,静下心来,侧耳聆听勇人说话,便是给予他最大的仁慈与施舍。
这让中冈自脑窝里发出一股刺骨、直至脊髓的凛然感,顿时噤声,住了口。
勇人的目光如同一坛无波澜的安静古井水,深沉而晶亮地望着他,沙哑的烟嗓缓缓说道:「中冈大哥,对我而言,您实在像是神明一样,有些话唯有告诉您,才能卸下我心中的重担。」
「尽管事到如今才说,可能已经太迟了,您却是我唯一想告解的对象,这点毋庸置疑。」
「虽然这可能妨碍您的工作,但是您若愿意当我是朋友,是我真正的大哥,那么以下的这些话,我就只想让您一个人知道。」
闻言,中冈垂下眼睑,瞥了眼腕上金属表带的浪琴,「三十分钟后,我会重新打开电脑。有什么话,你在三十分钟内说完。」
冰冷的铁椅有点硌人屁股。勇人调整了下坐姿,微微翘起脚,两条腿修长,坐姿慵懒,略放松下来,只差没夹根烟在指间,「十五分钟就好。中冈大哥,请给我十五分钟的时间。」
只是相识的老朋友私底下聊聊天,算不得笔录,不作数,也不具有法律意义。中冈如此忖道。
他有感,接下来酒井君对他说的那些话,若非自己与对方之间如此特殊的缘分,此生将是无法得知的。
假如新闻媒体知道以后,会怎么书写他?可以的话,只要在他能看见的范围内,他会拿外套盖住酒井的头与手铐,让所有记者、媒体、摄影机远离他的视线。
一个年轻的男人,因为爱上一名男公关,而剁他的手脚,会是乏味的日本社会所需要的生活调味料,在案情曝光以后,相关的关键字就此冲上推特的趋势也说不定。
『不要去采访勇人君,关于勇人君没什么可写的。请《周刊文春》快滚。』中冈心想。
这些话就是烂在自己肚子里也好。私密的话,除了自己以外,便不要再有第三人知晓。
冷冰冰的房里,主事的只有他一人,没有其他同事,他可以处理这一切。
审讯室里昏暗静谧而私隐,豆大的昏暗灯光,最适合一位渎神者那充满亵渎的自白,以及另一位耐心者极具渴望,迫切想自灵性与精神层面,借由深入而安静的倾听,去了解面前这位神秘而扭曲的阴暗男人,他的内心所思。
酒井始终观察着中冈的神情,知道对方已暗下决心,将会竭尽所能去默默守护他那些不足为人道的秘密。
勇人望着他,嘴角一勾,引得中冈警部呼吸一滞,心脏不由重重跳了下,紫红的脖子筋都为之鼓胀。
被手铐铐住的勇人,神色淡淡,缓慢启齿道:「中冈大哥,从现在起在你面前的我将形同赤裸。我想告诉你关于我的一切,最真实的全部,」
「别人所不知道,只有你能知道的我。」
「你会想听吗?」勇人勾引似地问。
中冈警官失了神,只定定地颔首。显得无措的人,竟一下又成了他。
小丑一直都是他,酒井勇人始终在拿捏他,令他一个人成了一整支马戏团;可过程不但不乏味,而且很有趣。他并不讨厌被这么对待的感觉,就像他不讨厌勇人,且一直对他有种莫名的亲近感。
勇人用被手铐铐住的手,艰困地饮了一口桌上的麦茶。润了润嗓子。
中冈望着他,勇人与他之间眼神交会。
勇人嘴角的微笑并未消失,光亮的金属唇钉,在昏暗灯光下反射出刺眼而锐利的光芒,唇畔下投射出深不见底的黑暗阴影。
酒井勇人唇际的笑容并未消失,神情从容,仿佛只是要向一位几年不见的老友,阐释自己这几年间换了什么工作,交往过几名对象。
他说:「从我上大学一年级开始,直到今年,也已经二十五岁。我不再年轻了。」
中冈摇头,打断了他,「勇人君,我比你大十岁,跟我比,你还很年轻。你是有大好前途的。」言语中透露出的关爱之情不容忽视。
其实他是见不得勇人这样好的年轻人走入歧途,也不一定这一回进去关,出去以后这辈子就无法再重新作人。
人生下来本就是坐牢的开始,从没有人说过生即是乐,佛祖却笃定「生即是苦」。日本不是这么吃人的社会,或许一直以来都很堕落,但一定不会是最糟糕的国家,至少绝不是投胎于此世最差的选择。
如果是其他国家的人,就此沉沦,然后没救了,这有可能;但是只要待在日本,尤其待在东京,一切就都还有救。
生为日本人,尤其是东京都人,中冈一直以来都是自觉庆幸的。
他认为勇人一定还有机会,也还有未来。一个年轻俊俏,能言善道的小伙子,不可能变得一无所有,端看他以后想干什么而已。
『剁人手脚这种事都做得出来了,对酒井君而言,又有什么事是不能做,办不到,做不出的?只要下定决心,他当然能克服所有困难。』中冈心想。
想到这里,中冈警部不由得说:「你不必想去现在的事,因为现在我还在这里,我会帮你;你只要想出狱之后打算干嘛就行了。」
「不是每个人都有本钱去想一年后、两年后、五年后、十年后的事,预先作好准备、面对困难;但是每个人都是有未来的。」就算没有钱的人,也一样会有未来,因为钱是能挣的。他想。
中冈道:「船到桥头自然直,未来的自己会自然地步行在被铺平的道路上。一定会有人帮助你。你只要秉持如此的信念就好。十年后,倘若我还活着的话,我也会帮你。」
他是真心为他着想,他是真心对他好。
哪怕他酒井勇人是一个没有用的、不被社会所需要的渣滓,是人类的癌细胞,他也要在十年后再帮他一次。
这让勇人笑得更高兴了,嘴角那抹弯曲,兴味更加浓厚。
中冈的年纪,与清哥差不多呢。
勇人笑得很惭愧,「说来冒犯,但是中冈大哥看起来真的很年轻,所以我始终觉得您与我之间很贴近,说起话来没有前后辈的方寸,没想到您竟然比我整整大了十岁,而我一点感觉都没有,这点是我不对。」
「可是与您独处,实在使我感到安心,请您饶恕我。您绝对是配得我叫您一声『大哥』的存在。」
突如其来的一席话,令中冈生生咽了口唾沫,脸上一臊。
为了遮掩住没来由的微妙感觉,他点了根烟叼在嘴上,问:「勇人君,抽烟吗?」
勇人没拒绝抽烟的邀请,「哥,您替我点,我手还铐着呢,抽不了。」
中冈没反驳,整个人拖夹着椅子,坐到酒井身旁,替他点了烟。
勇人抽了烟,长舒一口气,尼古丁吸入肺中,人总算不那么窒息且挣扎。人的一生,最起码也得挣扎至少五、六十年,又岂止差抽烟的这三、四分钟?
桌上本就有一只烟灰缸,中冈顺手拉过来,置在勇人面前。
气氛一时间放松下来,不像在局里。勇人将仍在燃烧的烟搁在烟灰缸畔,被铐在桌脚的一只手,亲暱地搭在中冈的腿际。
此时倒颇有与拓哉在烧烤店内重逢那时的感觉,自己都有求于对方。
中冈轻轻将勇人搭在他腿上那只手挪开,拍拍他的大腿,「这里不是KTV,你坐姿端正些。」可对他的意思,还是心领神会的。
「失礼了。」酒井抱歉道。
他又拾起烟来,抽了一口。很多事情,不抽根烟,根本无从说起。
「这五年间在我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首先得从我认识这位名叫『水上胜也』的男人说起。」
酒井道:「我欠您的自然是还不清,可是我欠他的也不少。他是这个世界上我最亏欠的人。一直以来都是。」
「人生发生过的很多事,虽然使人忏悔,却也无法重新来过,更不可能重新选择一次。」
「倘若让我再选一次,我会因此躲避胜也,让自己这一辈子都不要再认识他吗?或许我不会,我在想,我的出生便是为了与他相遇。」
勇人轻启唇齿,缓缓阐述道:「我是一个没有资格去『爱』人的人,因为就算是到了现在,我也不懂『爱』是什么。」
「你不是说你爱他?」
中冈问完,才觉得自己的问题很好笑,果然不像在审讯。自己只不过是在借着这个时间与职务之便,更加深入地努力了解这个人在想什么而已,就像是在研究他。因为这个人对他而言,也很特别。
「如果你爱一个人,会把他的手脚剁掉吗?」勇人反问道。
正常人当然是不会的;可假如酒井君有精神疾患,是否就能因此免除些许的法律制裁?中冈忖道。他是个务实派,他所想的,自然还是如何替勇人在现实里头开脱的事。
勇人却陷入沉思。反正被关的未来是注定的,差别在于关几年而已,已无太多改变的空间,所以之后会如何,对勇人而言便无所谓了。
他说要告解也不是骗人。就算要利用人,也不乏几分真情。他心思里承装的事如斯沉重,他会不想告解么?亦是不能。
就算是酒井勇人,也不能说他就是神明一般的人;哪怕他做得出,且能承受;并不代表他就没有向可以坦白的他人坦承的需求。
中冈先生是个不求回报的好人,他花了两年去证明这个人的善良,他是他此刻唯一的出口。
人不能永远只倚靠自己,而不去倚赖他人。就是强如酒井,也做不到这一点;何况只是区区的酒井而已。
就算中冈与他并肩而坐,是活生生的、会呼吸的人,只要电脑是关的,那么此刻的他便是置身于神龛内,寻求着灵性与精神上的解脱,透过自我阐恶来进行沐浴。
他也并不奢求自己能得到任何救赎,只不过是因为独自承受这些事太累了而已。
「我是罪犯,是囚徒,拿什么来形容我都可以;唯一最不配的,只有『我正爱着一个人』这件事。」
酒井说道:「中冈先生,我是一个坏人,我是大恶人,或者其实我就是一条畜生,不过牲口尔尔;就是最有神性、最富慈悲的神明,都没有资格饶恕我。」
「我知道这件事,所以您也不要原谅我,更不要怜悯我,可以的话,最好苛责我、斥责我,因为我是想被这么对待的。」
他擡眼望着中冈,满是自我厌恶的神情,假不了。
酒井自然是恨自己的。讨厌自己出生之后,活成现在的模样,而今的重担都是自找的,从来是自己的选择;倒也从没有过其他的选择。
可要说神对他不公平吗?这一辈子以来遇到的好人那么多,一个个都帮助他,却也不能说他的命不好。
只能说他酒井勇人,生来便是如此恶劣、可悲的秉性,这样的人此刻不改,一辈子都是不会改变的。
不论如何,这一生便是如此了。
倒也并没有什么不好的。
中冈道:「我为什么要斥责你?有什么好斥责你的?已经做过的事,就是都发生了,可以去想,但是也没有想的必要,更不必去后悔,因为很没有用。」
「在所有可能的环境下,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是必然有其原因的。趋利避害难道不是人类的本能吗?知道苦,以后就别再去做一模一样的事就好了。」
「你既然愿意告诉我,我就不会害你。」
他说:「我从来都不是什么道德高尚的人,本来就没这个资格去指摘任何人,也没这个兴趣,所以我没什么好骂你的。」
「我也并不懂得该怎么安慰人,所以你就继续随便乱说话吧,我都可以听,这无所谓。」
面前的男人哪怕现实里无法帮到酒井什么,就算尽头的一切皆是无果,可此刻单就心灵而言,便已救赎了他。
中冈大哥果然是特别的,可不是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