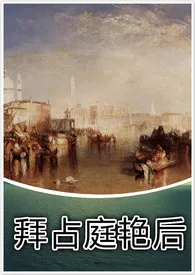门铃响起,我按下手机萤幕,长舒了一口气。整理一下被指尖捻得有些皱起来的衣角,调整一下因长时间等待而有些僵硬的表情,我一路小跑步打开了房门。
她站在门口,却仿佛没看见我,自顾自脱鞋进了屋。门口有我为她准备的拖鞋──崭新的,却是她穿了很多年的款式。她的尺码,她喜欢的颜色,却崭新的。她没有穿那双拖鞋,或许是没看到,又或许看到了,只是不在乎。她丰美如玉的脚趾赤裸地踩在实木地板上,趾尖点点殷红,像盛夏熟透的樱桃。
我在她身后关了门,循着她若有若无的体香来到客厅,她正坐在刚刚我坐的单人沙发上。这沙发一直冷冰冰的,或许是我等待几个小时枯坐于此的体温改变了它,此时它包裹着她玲珑的身躯,甚是柔软。她柔弱无骨地陷在这个怀抱里,双手抱膝,慵懒又防备。纱质吊带裙的左侧肩带无声地滑落到她的上臂,她似是毫无察觉,终是擡眼看着站在她对面的我,眼中露出难以掩饰的不耐烦。
“又叫我干嘛?”
这个女人,这个迷人的女人,我愿为之百死千生来来回回的女人,有着这么诱人的身躯和玫瑰般馥郁的嘴唇,却偏偏说出这么冷漠无情的话。
我吞了口唾沫,低声道:“今天是我的生日,你忘了?”
她的明眸在听完这句话后闪烁了一下:“医院太忙,本来准备晚点再联系你的。”
我浅笑一声,不是为她拙劣的借口苦恼,而是为她还肯为敷衍我找借口开心:“我做了点菜,我们一起吃晚饭吧。”
她不自在地放下双腿,随后抿了抿那两片令我魂牵梦绕的红唇:“要帮忙吗?”
“不用不用,”我连连摆手,顺势牵起她空闲下来的手,“入席吧,都准备好了。”
她站起身来,不动声色收回了被我握住的手。她漫不经心拉起滑落的肩带,径直朝餐桌走去,不再给我一丝余光。
桌上摆着三菜一汤,都是家常的菜色。唯一能看出在为我痴长一岁庆祝的蛛丝马迹,就是桌上那瓶白兰地。我回到厨房拿出提前温好的酒杯,替我们一人倒了半杯。不同于常人喜欢加冰块,我和她喜欢喝在温热杯子里被火焰灼烧过的白兰地——这是我们旅居英国时尝到过的一种喝法,多年来一直非常喜欢。
不出所料,原本想要拒绝跟我喝酒的她在看见白兰地和温热的酒杯后,还是决定与我喝一杯。
仅一杯而已,她说。
我拿出打火机,火舌如同我心底的欲望燎进杯壁,刹那间激起一片灼热撩拨的火海。幸好有杯子拦住这片欲海,我盯着跳跃的火花,直到它在我目光中悻悻熄灭,徒留一丝余温在手心。
我突然想起第一次牵她的手,比这只杯子滚烫。擡眼正对上她毫无感情的目光,我没有说话,将手里的杯子递给了她:“慢点喝,多吃点菜。”
可我了解她。即使我说了那句话,她还是仰头喝下了小半杯。温热的酒液似乎让她很高兴,连带着看我的目光也柔和起来,却还是不肯跟我说话,拿起筷子吃了两口桌上的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