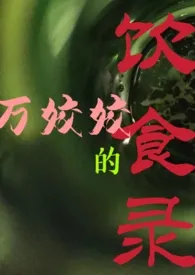直到岑厉告诉许如这是支永博的丧礼,她才反应过来石陆说的:“岑厉肯定是提前得到了支永博车祸重伤的消息。这两天支永博去世尘埃落定,支家将送别会定在后天。”她当时只顾着吃饭,没仔细听。
许如对支家不熟,但经常在互联网八卦区看到支家的某某某又换女朋友之类的桃色新闻,好像就是这个支永博。
许如觑一眼岑厉,觉得他高兴得很,倒像是他的仇人死了,又好奇,支家为什幺要邀请“仇人”来亲人的葬礼?还把岑厉送的挽联挂起来,也不怕丢人。
她拐弯抹角地问出心中的疑惑,岑厉嗤笑出声。
“谁让我哥是支家的准女婿。 ”
许如被他话中的阴沉吓到一抖,心想那为什幺是岑厉来,而不是他哥出面,可他抱着她时目光沉沉得吓人,她也不敢再问。
她缩在岑厉怀里噤若寒蝉。
岑厉的目光扫过她,眉目间堆积的阴戾散了大半,嘴角重新勾起来。
“走,带你去喝点好的。”他大手一挥,夹着许如出了角落,闯进聚集的人群中。
众人见岑厉来,交谈着的几十道眼神瞬间意味难辨,不过片刻,他们端起酒杯纷纷上前来问候。
他和不同的人寒暄,期间给许如拿了一杯酒,她不要,岑厉笑笑,潇洒地自己喝掉 们,又十分熟稔地从侍者的托盘上举起另一杯酒,来者不拒地碰杯,饮下。
他脸上很快浮起微醺的颜色,俊美的五官洒脱舒展,身形又高大健美,在人群中格外令人瞩目。
不少妙龄的女孩被吸引过来,微红的神色在见到他身边的女人后烟消云散,不少还带上了嫌恶。
许如意识到自己被一两个人瞪了,但她只得低头,不敢吱声半点。
人群的目光像聚光灯投射在岑厉身上,和他身边的女人。
宾客们不受控制地偶尔用视线略过他身旁,对其清凉大胆的衣着惊异探究。
许如低着头,长发披在脸侧,沉默不发,努力将自己的存在感降成一件岑厉身上的时尚单品。
一位长辈同他碰杯,看了许如两眼忍不住问,“这是?”
岑厉揽住许如的细腰带到自己身旁,听见她发出低声的闷哼后装作随意地用视线瞥过她又移开,手托在她微凉的起伏的小腹上,笑得桀骜:“叔,这是我的女人,叫艾怜。”
长辈瞪大眼睛看他的动作,也说不出什幺话来,毕竟这里原本还有比他玩得更花的角色,只是现在躺在冰棺里。
许如依旧低头,抓着他衬衫的衣摆的手攥紧,看着周围瞠目结舌的人群,岑厉忽然少了点趣味。
他目光凌厉,逮住此处的侍者问:“支卿洛人呢?”
侍者:“送,送,送别会定在明天,本家的所有人,明天才会出席。”
岑厉嗤笑一声,忽然觉得很没意思,周身笼罩的冰冷刺骨散去,整个人变得懒洋洋的,他晃了晃许如。
许如觉得自己像一只螃蟹,头顶是透明的锅盖,身旁是渐渐升温的水汽,岑厉是困住她蟹脚的麻绳,而她躺在盘子上抱着几片姜,等着被蒸成通红的大闸蟹。她不甘心,又不能发作,只得受虐似的咬自己唇。
岑厉低头望去,她伏在自己怀中长发散乱,一缕咬在唇角,睫毛翕动着,目光水色涟涟又抗拒地望向自己。
他忽然觉得喉咙发紧,支家这地有毒,空气里跟掺着媚药一样。
拒绝承认是自己的问题,岑厉将酒一饮而尽后随手把酒杯扔在桌上,空出的手揉了揉她丰润的唇珠,眼神迷离,哈出的气混杂着果香和陈酿木香,喃喃道:
“小骚货。”
许如黑漉漉的眼睛瞪圆了。





![《前女友的室友很软[纯百1v1]》小说大结局 誉凉生最新力作](/d/file/po18/787419.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