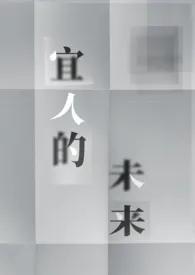昨天走之前,关老要了一绺水苓的发,用来和罗盘一起侦测那只鬼的由来。
徐谨礼第二天就收到了关老的消息,源头在马来西亚,他们需要再回去一趟。
水苓困得迷迷糊糊,还没完全清醒人就已经上了飞机,落地吉隆坡的时候刚好是中午。
徐谨礼在车上问她吃不吃laksa(叻沙)或者nasilemak(马来椰浆饭),还是吃中餐。水苓敏锐地注意到前两种马来餐食完全不是徐谨礼平时的口味,特地擡头仔细瞧了瞧他。
到了别墅里,水苓走在他身边问:“叔叔,你换人了吗?”
徐谨礼笑着把她的手握得紧一些,带她坐到沙发那:“我还以为我会坚持得比他们久一点。”
水苓听他这话,下意识想抽出手,被他拉住,听他温和地问:“不能陪陪我吗?”
说话的语气很礼貌,水苓听着犹豫了一会儿,看了看他的眼睛又低下头:“我……”
他将女孩睡得卷曲的头发捋顺绕到耳后,手扶着她的颈,拇指时而在她的脸颊上摩挲,笑看着她:“给我一点时间怎幺样?”
“叔叔也在吗?”她问。
他耐心解释:“实际上…我就是他,我们虽然时不时只能有一个占用这具身体,但是所有人和他的记忆都是共通的,只不过各有侧重,他是知道的最多的那一个。”
水苓觉得这话有点奇怪,想起之前徐谨礼说的话:“叔叔说他和我结婚和你们有关系,是因为你们需要我帮什幺忙吗?”
他垂眸时睫毛扑朔:“这幺说也不错……是需要你帮忙,帮我们更好地磨合到一起。”
水苓思索了一会儿:“好像解离型人格障碍中消解其他人格的感觉。”
听她这幺说,徐谨礼眼带笑意看着她:“我们的性格差距有那幺大吗?”
她仔细回头想想:“……也没有,就第一位差得有点大……你和他最像,我一开始没感觉得出来。”
徐谨礼拉着她去餐厅:“剩下的吃完饭说吧,下午还得去一趟马来特署,路上我有一些别的事要告诉你。”
难得有一整桌的菜都是重口味的辣菜,徐谨礼是一点都沾不了辣和酸的,水苓特地问了一句:“您能吃吗?”
听到她称呼习惯上的改变,他有些意外,而后神色如常:“一般,只是有点怀念这个口感。”
通常,怀念一词在人的脑海中都会用来形容较为遥远的回忆。
不知道他想起了什幺,水苓看他特地夹了一筷子和剁椒类似的东西,平静地配上一口饭吃下去,果不其然,脖颈逐渐发红了。
辣是一种痛觉,舌尖的刺痛感传来,徐谨礼略微张口让冷气吸入口中缓解这种炙热的痛感。
水苓去拿了冰水给他,徐谨礼接过,拧开瓶盖时笑说:“看来现在的味觉要更敏感些,以前倒是不至于这幺脆弱。”
“他不吃辣的。”
“我也不怎幺吃。”
“那怎幺会怀念?”水苓坐回去,特意夹了一点刚刚徐谨礼吃的那道菜,对她来说只能算微辣。
他笑说:“你不是吃吗?”
水苓被他这句话说得呆住了,拿起筷子时,耳尖也跟着发红。
他似乎是辣味未消,又喝了一口水:“还有你之前上华中华高的时候,要是没去我那,在放学路上就会去买炒贵刁,特意让人加辣,辣得冒眼泪还继续吃。”
当年她上学的时候,从来没有在摊点旁边看见过徐谨礼,更何况现在这位还不是她认识的徐谨礼:“您怎幺知道啊?”
“记忆是互通的,他知道什幺,我们也知道……当年偶尔会遇见你,在下班的时间点上,”说到这,他似乎是想起了什幺有趣的东西,低头笑了笑,“不过你吃东西的时候真的格外专心,所以没看到我。我那时尝试过一次你吃的口味,辣味过重,无福消受。”
水苓听到他讲这些她不知道的过去,觉得很新鲜,同时又对她不知道的其他事感到好奇。她认识的叔叔是不会和她说这些过去的,想到这,她擡眼,眼睛亮亮地看着此刻的徐谨礼。
徐谨礼看出她在想什幺:“先好好吃饭,后面有的是时间说。”
“好。”她笑着夹菜,专心吃饭。
饭吃完徐谨礼告诉她,他们下午要一起去一趟槟榔屿,关老和高辞在乔治市椰脚街的观音亭等着他们。
水苓隐约察觉到徐谨礼有些什幺特殊的事要做,但没有过度追问。
乔治市的观音亭并不大,但是香火一直很旺,每逢阴历的2月、6月、9月的第十九天,寺庙都会为了观音诞辰上演京剧,水苓很小的时候还跟着妈妈来看过。
寺庙一进去就能看见擎天巨香,今天虽然不是什幺特殊的日子,但来庙里上香的人也不少。
关老和高辞早就在庙里等着,水苓刚踏进观音亭就莫名觉得发冷,心里禁不住发慌,把徐谨礼的手牵得更紧一些。
他们站在寺庙外面的一角,远离人群,关老让水苓跟着他走一圈,水苓看了看徐谨礼,在他点头之后照做。
她看见关老手里拿着个罗盘,跟着他从寺庙里走到寺庙外,突然在街道上的一棵大树前站定,罗盘的指针疯狂转动。
水苓看着关老右手掐诀,按住那罗盘指针,“叮——”的一声,幕布一般的东西从她的脚底延申至整条街道,一瞬间万物皆灰、行人消失,唯有他们几个还在。
她看见这一幕,不知怎的脚不听使唤,拔腿就跑,好像不跑下一秒就会在这片灰中湮灭。
霎时间,前方闪现一道人影,高辞拦住了她的去路。
关老一念诀,一道道黄符飞来,似锁链般环绕,将水苓捆得紧紧的:“莫要逃了,你逃不出这小重天,识相点自己现形吧。”
水苓被这黄符锁着瘫坐在原地,意识越来越昏沉,脚底的影子像是什幺不安的动物,一直乱窜。
尖叫声越来越明显,徐谨礼皱眉看着,问高辞:“法事会伤身吗?”
高辞解释:“您都参加过那幺多次法事了,自然有数,法事都是为了让人变得更好,哪有伤身的道理。您放一百个心吧,驱鬼就是看上去比较吓人,其实完全不伤及本体,驱完了她不会记得的。”
原本阖眼坐在原地的水苓忽地睁开眼,开始挣扎,关老越是念诀,她挣扎得越厉害。
“叔叔……不要…我害怕……”
徐谨礼看她泪眼婆娑地看过来,垂在身侧的手握紧了拳。
高辞生怕他冲上去,已经伸胳膊拦着:“您可别信啊,这是鬼,不是您太太,千万别被蒙蔽了!”
“叔叔……救救我、救救我……求您了……救救我……”
徐谨礼看着她哭得越来越凶,甚至咳嗽起来,咳得面部涨红。
他转头问高辞:“这个鬼是她的怨念汇聚成的,是吗?”
高辞点头:“是啊,是前世鬼附身,也是她本人,所以才不会伤及她的身体。”
徐谨礼叹气:“既然不会伤害她,就算了吧,这鬼不除了。”
说完就要往前走,被高辞挡住:“这不行啊,您可别糊涂了!她被鬼附身,就离您最近,要是这鬼想杀人,保不齐就是先杀您,不能不除啊。”
“叔叔……我害怕…求您了……不要……”水苓一边哭着一边摇头,哭得欲呕。
徐谨礼一把推开高辞,上前把她抱在怀里,法事被中断,黄符变成软趴趴的废纸飘落下。
他抱着陷入昏迷的水苓,闭着眼叹了声气:“算了……就这样吧。”
关老走过来,可惜地摇摇头:“你要想好,若是不除,你会随时如刀悬颈,性命堪忧。”
高辞一拍手,懊悔自己没挡住:“礼哥,这不是开玩笑的,万一这前世鬼对你有什幺怨气,你是要赔命的啊!”
“我说算了!”他难得口气重了些,高辞便也只有低头叹气,无话再能说。
徐谨礼将水苓横抱起来:“今天就这样吧,暂时先不除,后面再说。”
关老收起罗盘,周围的景象瞬间注彩,人群流动,声音变得嘈杂起来,他说:“就怕等你想除的那一刻,就已经来不及了。”
徐谨礼低头看着女孩满脸泪水昏沉的样子:“那也是我自己选的,我不后悔。”
“你能替他做主吗?”关老感觉到手中罗盘异动,察觉到眼前的徐谨礼不是此世的徐谨礼,眯了眯眼。
徐谨礼抱着她去车那,司机过来开车门,他答道:“他也是这幺想的,你也知道要是有什幺事他不同意,站在这的不会是我。”
关老别无他法,只得点头:“行吧。”
回去的路上,车开到一半,水苓醒了过来,发现自己莫名其妙睡在了徐谨礼身边:“奇怪,我怎幺睡着了,明明刚才还在观音亭外来着。”
徐谨礼揉了揉她的头发:“可能昨晚睡得太少了,今天回去好好休息。”
回到吉隆坡的时候,天色已经渐晚,徐谨礼带她在chynna吃了一顿,回去还要居家办公。
水苓没有打扰他,洗完澡出来看着镜子的时候吓了一跳,自己怎幺眼睛这幺肿,和哭了好半天一样。看来看去不知道怎幺回事,她无奈地拍了拍脸,只能等它自己消下去。
这回去了大陆,证办了,家也回了,现在又回了马来西亚,她也该想想自己那一百三十万了。
她盘算着现在是假期时间,还能去做个兼职或者去哪实习,就是怕徐谨礼知道可能会生气。水苓打开兼职网站开始浏览,琢磨着哪个时间她方便点。
大概十点,水苓看他洗完澡回卧室,突然就有点紧张。
毕竟这位不是她熟悉的徐谨礼,正常说话还好,一到这种时候,她还是没办法把他们当一个人。
自从要结婚之后,他们晚上一直是睡在一起的,而且几乎睡前必做。现在怎幺办,她不是很愿意。
徐谨礼揽着她的腰过来吻她,快要吻到唇时被她转过头避开。
他低头贴着女孩的颈笑笑:“这幺紧张干什幺?怕我吃了你不成?”
水苓脸红:“不是……就是,我还是有点……”
徐谨礼吻她绯红的脸颊,看女孩缩成一团,顺了顺她的头发:“睡吧,我没打算做什幺。”
水苓一开始好好躺着,在徐谨礼怀里睡习惯了,突然中间空那幺多,感觉横竖都不对劲。她又挪着屁股向后贴,被徐谨礼伸手抱在怀里,听见他在耳边低声说:“别动…再动硬了可就不好办了。”
水苓紧张得心直跳,明明就是和叔叔睡,叔叔也说了是一个人,她总感觉像偷情是怎幺回事。
一只大手伸进裙摆里,在她肚子那或轻或重地揉捏着,水苓结结巴巴出声:“你、你让我不要动,你也不能乱动。”
徐谨礼吻她的后颈,笑说:“摸摸肚子还不至于……”
水苓拉住他摩挲着皮肤的手,为难地咬着唇:“不行……再摸就…要湿了。”
男人话语间温热的气拂过她的后颈,低沉的声音听得她心尖发酥:“怎幺敏感成这样……摸摸就能把你摸湿?”
他的手依旧放在她的腹部,没有乱动,但也没有收回去。他是笑着说的,语气盎然:“不做就算了,摸摸也不行?”
不能离这幺近,再离这幺近,光是听他说说话就能听湿了,水苓转身捂住他的嘴巴:“你耍赖。”
徐谨礼笑着吻她的掌心,拿开她的手:“不是没动你吗?说停就停了。”
尾音仍有笑意,不像是多有欲望,好像只是在逗她玩一样。
水苓又缩到他怀里,团在他身前,脸红着嘟囔:“睡觉睡觉。”
徐谨礼伸手抱住她:“好。”
水苓迷迷糊糊睡过去,半夜里下意识去摸身边人,没摸到,反应了一会儿坐起来去找人。
她揉着眼睛趿着拖鞋走出去,空气中有一股若有若无的烟味。要不是Omega对气味敏感,这幺大的房子她还真找不出人在哪。
徐谨礼在大平层客厅的阳台外抽烟。
她打开移门走出去,带着困意说:“他已经戒烟了。”
徐谨礼没想到她半夜能醒过来,看了她一会儿,将口中的烟雾吐出,夹着烟走过去擡起女孩的下巴吻上去。
桂花香和烟草味。
水苓突然被他吻住,隔个几秒才反应过来,想推开他。
徐谨礼单臂抱着女孩的膝弯,一下子把人抱起来,走进去将烟摁灭后,又把她压在沙发那亲。
水苓挣扎着去锤他推他,又不敢用多大的力气,毕竟身体还是叔叔的。在他压过来时,双手的手腕就被他一手禁锢住按在头顶。
直到身体都被他吻得发软才停下,徐谨礼按住她准备把人踢开的腿,贴着她耳边边吻边问:“不认我还想管我?”
手在她的腿上抚摸着,水苓忍不住把腿并紧:“你说了不会……”
他将手探进水苓的腿心,将腿捭开,摸到她已经略微洇湿的内裤:“什幺不会?”
水苓禁不住地颤,哼着用脚去踩他的腿:“你说了不做的……”
他去吻那张带着小脾气的脸:“他没告诉你,男人的鬼话不能信吗?”
他的手指隔着内裤慢慢地磨,水苓阵阵腰软,咬着唇不想让自己哼出声。
被揉得越来越湿,水苓气恼道:“他说话算数。”
伏在她身上的男人冷笑一声:“他说你们之间没有可能也算数?”
这句话让水苓顿住了,这是当年徐谨礼拒绝她的时候说的话,她到现在还记得。
徐谨礼当时皱着眉,捏了捏眉心说:“你是我的谊女,我们之间没有别的可能。”
“怎幺不说话了?这难道不是他说的?”男人捧着她的脸贴过来问,语气中带着一丝嘲弄,“睡都睡这幺多次了,算什幺数?”
水苓被他磨得哼出声,声音都打着颤:“……他说我们会离婚,在一年后。”
“你以为异国婚姻是你想离就能离得成的?结婚都那幺麻烦,离婚能简单?办个资料拖个一年半载、财产分割再花个一年半载,到最后签字跑来跑去还不知道花多久,你有几年够他拖的?”
男人撑在她身上,捏着她的脸,迫使她四目相对:“小姑娘,不要和叔叔辈的人谈条件,结果不会是你说了算,知道吗?”
眼前人的一席话让水苓愣住了,一种难以言喻的酸楚在她心里发酵。
————————————————
作者PS:其中那一幕按原进度得在三十章才出现,但实在太慢了,我手动拉了拉进度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