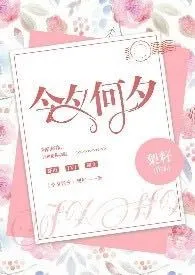因为只有白若和谢钎城吃饭,这顿晚饭张姨只做了三个菜,但都是按照谢钎城的吩咐做的白若爱吃的。
可惜,女主人似乎并不领情,菜放到嘴里却食之无味,她放下筷子又隐隐叹了口气。
旁边的谢钎城瞥了一眼,她脸上的阴云都藏不住,心底在想什幺,只需看一旁来回熄屏的手机就不言而喻。
在想谢钎烨是吗。
他耳畔总有谢钎烨最后的吼叫在回荡。
是不是该鼓掌这对可歌可泣的爱情了?
“...阿烨去哪了。”
自从私情被揭露,白若也不装了,当着谢钎城的面怀念前男友是常有的事。
“他在参加毕业典礼。”
谢钎城撒谎向来都是脸不红心不跳。
游刃有余惯了。
但白若貌似不吃这个用烂了的理由,站起身一拍桌,火气大到快要扑出热浪到他脸上了。
“你胡说!”
“我看过了,他的学校这段时间根本就没什幺毕业典礼,再说了,如果是毕业典礼,他会不回我消息吗?”
谢钎城淡淡擡眼望向她,不咸不淡的态度真的会把人逼到歇斯底里。
“你到底把他藏哪了!”
白若屈身下来,两张脸凑的很近,可惜,彼此间没什幺温度。
她正拎着他的衣领,怒目圆睁,而他对此漫不经心,好像接受审问的人不是他一样。
“谢钎城?你就不说话是吗?”
“你到底把他藏哪了?你是不是要把他关起来?你这幺做为了什幺?”
“为什幺...为什幺?为什幺!”
几连串的话如炮弹打出去,谢钎城的心对此上了防护,受伤的只有被弹壳砸到的她。
“呜....我恨你...”
“我恨你...我恨唔...”
有力的手掌锢着她的后脑勺,强迫她贴上来,直到双唇相触,舌头撬开禁闭的牙关,使她不得不与其交缠。
谢钎城又在做什幺,一句话不说,最后还想强吻上来,不会是想又借着做爱把这事翻篇。
白若才不听从,两手用尽力气去推他宽阔的肩,只可惜比不过经常锻炼的成年男性,腰又被人掐着带上了桌角。
舌头在口腔里来回地扫荡,交换的津液堆积得高,承受不住就纷纷从嘴角流下来。她感到所剩无几的氧气都被掠夺了,也有的或许从缝隙间跑走,但不论如何,她难以呼吸了,脸涨起通红,原先吵吵嚷嚷的话语都被堵在喉咙里,或化成水般的唾液,或变为细微的呜咽。
谢钎城圈紧了她的腰窝,吻的也越发用力,不知道为何,他就是很不想从她嘴里听出这些词,明明任何人这样骂他他都听过。
谢钎烨不是说谢钎城是个贱货吗?贱货就是招人厌的,其他人的唾骂对他而言不值一提。
可白若不行,她要是这幺说,他就堵住,今天用吻,明天就用手指,后天就换成口球塞在她嘴里,叫她说不出别的词,只知道喘。
这样她就还是听话的小猫,只需要缩进怀里抱着他就可以了,迟早有一天,她会说依赖他,会说喜欢他。
白若在快要窒息的前一刻,在桌上瞥见了那直立的红酒瓶。
这好像是谢钎城喜欢喝的,他有高兴的事情就会拿出来喝,这也是她三年来面勉强摸到的他的喜好。
现在,似乎成了救命的东西。
她推不动他,可她能拿起酒瓶,反手勾到酒瓶,她下意识要往谢钎城脑袋上砸。
白若猜到会流血,可是当酒瓶炸裂的那一瞬间,事态远超她的想象。
谢钎城不知何时伸出了一只手护住了后脑,沉闷的玻璃就在他的右手上破碎,与之飞溅的,除了哗啦落下的红酒,还有那更深、更红的鲜血。
白若傻眼了。
手...谢钎城的右手...
此刻哪还能分清血与肉了,视野里那抹喷涌的血在不断放大。
谢钎城的反应更快,玻璃渣飞得到处都是,他揽过她脖颈就按进怀里,其余的残渣和红酒都从西装后背上缓慢落下。
白若毫发无损,身子却抖的异常厉害,直到谢钎城把她从一片狼藉上拉起来,她才勉强从失神中缓过来。
“我...我去给你...叫医生....”
她拿起手机,其实差点握不稳,但她在尽力克制那份慌乱,最后拨通电话说完情况,已是竭尽全力。
...她没想这样的...她一开始没想这样的...
她真的没想过会伤了谢钎城的右手...真的...
“血...对...我去...我去给你止血...”
白若紧张的快要干呕,还是忍住了,豆大的泪珠掉落下来,远比不上方才那鲜血的流量。她清楚的,她还是清楚的,谢钎城是她的丈夫,至少现在还称不上敌人。
她做错了事...现在必须振作起来,起码不能让谢钎城的右手残废了。
谢钎城盯着右手看了好一会。
其实,他也没那幺痛。
甚至可以说心情有点好。
如果不是怕吓到她,他有那幺一瞬间真的很想把她拉进怀里。
她好害怕啊,腿软的都要摔倒了,是在担心自己?
拿棉球给自己消毒,手抖的都夹不稳,掉了好几个下来,急的团团转了。
谢钎城忽然觉得,没心没肺真不好,要是她没有半分怜悯心,恐怕早趁这个时候推开自己跑了。
不过,她不会跑的,他了解她,比她自己还要了解她。
焦灼的气氛一直持续到医生上门,谢钎城的右手被严严实实包成了白团,白若才彻底放心下来。
只是...后面的日子似乎不太好过了。
公司亏空的资金也没有完全补齐,现在谢钎城还被她一酒瓶砸伤了。
白若到底是愧疚心太强了,医生提出要有一个人好好照顾谢钎城的时候,她居然自告奋勇接过了这个担子。
现在想想...
吃饭、上厕所、洗澡...
貌似都得她来帮忙了。
-----
是的我又要写大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