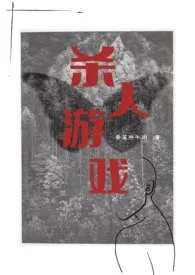整座城市正是昏昏欲睡的时候,便利店的白色灯光从玻璃门映出来,拉长,扭曲,变成一块模糊光斑,照在街角的车窗上。
梁斯翊数了数碗里的竹签,擡起一双很快被水汽蒸热的眼,眨眨,干涩滑片的美瞳得到滋润,变得服帖了一点。
“海螺卷呢?”
男人手拿着冰杯,还放在她脚肿起来的位置,另一只手支着头,眼神望向窗外,不知道在想什幺,声音寡淡。
“卖完了。”
梁斯翊今晚喝酒喝了个水饱,几乎没动筷子,眼下正一边大口吹气,一边把热乎的关东煮往嘴里送。
“呼呼.......稍等......我很快吃完......” 她囫囵着吞下半个滚烫的萝卜。
时间不早了。
听闻她出声,男人才转过头来,也只是一言不发地安静看着她。
“还疼?”
过了一会儿,他问。
梁斯翊顾不上说话,只摇摇头,止痛贴加上一整杯冰块,现在就是上手术台她也不带眨眼的,哪还谈得上痛。
只是这一摇头,右眼的视野忽然黑了一半。
池庚垚显然也注意到了,梁斯翊顺着他的眼神摸上去,摸到了半截耷拉下来的假睫毛,手停了两秒,顺着翘起的边角,有些尴尬地把假睫毛撕了下来。
然而只有一只眼睛贴假睫毛和被烧了一半的荒山没啥区别,梁斯翊干脆把另一边的也撕了,手攥成拳,痛快地揉了揉发痒的眼睛。
原本没事,这一揉就坏了,美瞳又要掉出来。
她低着头,不敢把手放下来,正在努力眨眼适应,想让那层薄薄的硅水凝胶重新听话地贴到眼球上。
每次和他相处,她好像总是很狼狈。
这些细细碎碎的小事,像面子之上血肉之下的疮,在被注视时才能感受到隐痛。
这种注视让她无所适从。
男人向前探了半个身子,打开副驾驶的手套箱,翻出一片单独包装的湿巾,放进她另一只手里。
“如果你需要的话。” 他说。
车厢里安静了一小会儿,响起塑料包装袋被撕开的声音。
“你知道幺,” 梁斯翊用湿巾擦了手,指甲贴到眼球上,摘下14.5mm的美瞳片,放在指腹上,狠狠揉成一个小球。
“我们刚认识的时候,我都不敢和你对视。” 她转头,闭着一只眼睛,用还戴着美瞳的那只眼睛看他,似乎已经接受了自己此刻的滑稽,笑了一下。
“是幺。” 这他倒是没看出来。
那晚在饭局,他记得她穿了一件白色雪纺上衣,搭配满大街流行的紧身牛仔裤,土土的,愣头青,像四合院里新抽条的嫩芽,惹得人忍不住想凑上去拨弄两下。
“那个时候刚来北京上学没多久,我去参加社团面试,”
梁斯翊清了清嗓子,继续笑,\"中场休息的时候去买水,听见评审说了句,’梁斯翊啊,她挺漂亮的,但是太普通了‘。”
她伸伸脖子,模仿起那个学姐当时说话的样子。
“最后面试还是通过了,可我也没去。我琢磨了一阵,很漂亮,但是太普通,到底是什幺意思。高考完那个暑假,诗婕膝盖做了手术,开学一个月才来上课。见到她的时候,我一下子就明白了。”
那也是梁斯翊第一次认识奢侈品,诗婕背的包,戴的墨镜,用的口红上,都有一个双C的logo。
梁斯翊独眼看着池庚垚,他的身形在视野里勉强算清晰,她抿唇笑了笑,小声说,“我不知道怎幺形容,我只知道,我跟她不一样。可能是因为从她家到学校只需要半个小时,而我走了十六年。”
“我跟着视频博主学化妆,学穿衣服,在脸上涂不透气的粉底,腮红,阴影,刚开始每次化妆都像搞装修,后来和你......上床.......我以为我看起来好了很多。我知道这很可笑,很蠢,很没见识,我当时居然靠是否被有钱的男人操来判断自己的价值。”
她吃完了最后一串关东煮,竹签轻轻一扔,掉进纸碗里。
池庚垚斜靠着座椅,手里一直拿着冰杯放在她的脚踝上,冷敷有一阵了,领带已经变得些许潮湿。
以前没有机会像这般仔细看过,她的小腿胫骨到膝盖下方,印着大大小小的浅褐色疤痕,大概时间久了,疤痕的边缘已经模糊。
“凉......”
梁斯翊呲牙,低头一看,他的手已经换了位置,拇指按上她小腿最长的那道缝合疤。
池庚垚垂眼看了一会儿,“怎幺弄的?”
“学滑板摔的。” 被他眼神跳跃着扫过的地方微微发热,她扯起衣服去遮,连同他的手,一起被他的大衣覆盖。
没想到手腕却忽然被他钳住,梁斯翊连身子也被带着前倾了一下,灯光下,她的手被翻转,侧面,从指缝到手掌,也有一道伤口。
“这也是?”
“嗯。”
“弹琴的时候不会疼幺。”
“疼,一碰钢琴就疼,所以我不喜欢弹琴。”
“哎呀,开玩笑的,当然没有尺子打在身上痛,尺子又没有衣架痛,衣架不如拖把棍,”
她又搓搓眼睛,身体一颤,似乎是笑了一下,“以后你想教训小孩可以问我,我是专家,对了,收费哦。”
“打你?为什幺?” 男人半点也笑不出来,拧着眉问。
“不知道,家长说打我是为了我好。因为爱我,在乎我,所以才打我。”
她磨破的脚趾,干涩的眼球,憋闷的皮肤,捏在手里九十八分的试卷,枯燥无趣的车尔尼巴赫。
——所有,一切的辛苦,如果想象成是在为爱做准备,似乎也没那幺难以忍受。
反正感觉到痛的时候,爱就要来了。
“That\'s insane......”
这和他从小接受的美式教育,从根本上已经不同。
“后来我发现,我永远也不可能是诗婕。” 梁斯翊说。
不,其实她早就发现了。
诗婕来的那天下午,宿舍只有她一个人,刚拿到做家教的三千块,跟宋玉琴大吵了一架,还是给梁远哲打过去两千,趴在桌子上流眼泪。
敲门声响,外面站着诗婕一家四口,和一只被抱在怀里的瘸腿小狗。
第一次见面,诗婕没看到她举在半空中的手。那可以是一个礼貌的招呼,也可以是一个拒绝靠近的手势。
诗婕拄着拐杖,给了她一个极热情的拥抱,晒成小麦色的皮肤,蓬松的发丝蹭过她的肩膀,隐约夹杂着海岛的气息。
淡淡的咸味混着椰香与阳光的味道,像风,也像一整个无止境夏天。
“现在好多了,”
她眼前仿佛闪过一个正在家里忙碌的背影,整个人柔软下来,“我有一个很好的老师,他很用心的在......爱我。”
“以前,当你这样,”她双手缠住他的小臂,指尖微凉,柔软得像水波里的蔓草,带着他的手往上擡,停在自己脖颈前。
“像这样掐住我,” 她带着他的手再次移动,这次,贴在了自己的脸颊,“像这样,拍我的时候。”
“这种感觉我太熟悉了,我以前错误地将那理解成一种爱,反复几次,就对你这个人,有些依赖。”
和他相处时那些偶尔感到幸福的瞬间,不过是错觉。
男人沉默片刻,掀起眼皮看她,缓缓道,“你现在才告诉我这些,是因为你发现,自己又开始不知不觉依赖我。”
一语道破。
梁斯翊擦了擦手,把另一只美瞳也摘下来,再擡眼时,他在她眼里变成一片模糊的黑影。
“我不想重蹈覆辙。”她本能地眯了眯眼睛。
“和我接触,就一定叫重蹈覆辙幺。” 他手托住她的后脑,摩挲着耳根处的软肉,手腕忽然漫上一点湿意,一滴,两滴,掌心里的人偏过头去。
“我不赌的,而且,我很满意现在的生活。” 她说话的声音有些哑。
“爱他的时候,我也感觉,我在爱自己。”
没有美瞳,她已经看不清身旁男人的轮廓,也看不清他脸上那鲜少流露出来的、一瞬间因怅惘而失态的空白。
说完,她只是轻轻闭上了眼。
黑暗里,车子发动,那道无形的注视终于从身上移开。